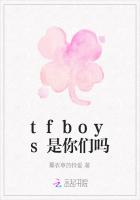1937年,川军各部编为第二路预备军出川抗战,邓锡侯率第22集团军开赴山西战场。当时,山西战场战况紧急,部队到了以后甚至都来不及集结,就急匆匆地开赴前线,仅仅九天,整个集团军就牺牲了一万多人。
时任第22集团军124师文书的何宏钧随部队赶到山西时,已经是11月了,但大部分战士仍然穿着草鞋单衣,邓锡侯几次请求补给,都没有回应。原因很简单:在许多人眼里,川军是杂牌军中的杂牌军。[国民党所谓的正规军就是蒋介石当黄埔军校校长期间的学生,就是黄埔系,还有就是外国军校留学回来的。杂牌军将领一般是地方军阀和各讲武堂毕业的学员。]
何宏钧清楚地记得,太原失守后,邓锡侯率领部队撤退。行进途中,他们遇到一个无人看守的军械库,战士们都说:“其送给敌,还不如自己用。”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旧枪换成了新枪。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这个消息后,十分恼火,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立即请统帅部调走他们。
蒋介石想把川军调给一战区,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却说什么也不肯接收这支部队,就这样,原本誓师出川抗战的川军,竟然找不到一片抗日的战场。
后来白崇禧给李宗仁打电话,想让他接收这支部队,李宗仁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第22集团军转战到第五战区。
1938年2月,第22集团军奉命增援滕县,3月14日,滕县保卫战打响。
对于当时的战斗情形,何宏钧仍清晰地记得,他说:“敌人在城外攻击,用飞机、大炮、坦克在前面开路,而我们就是老办法:先尽量筑工事,飞机来了我们就到工事里面去藏着,等坦克后面的步兵上来后,我们就冲上去拼命。远距离打靠枪,近距离就靠手榴弹,还有就是用刺刀杀。”由于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连续进攻三天都没能攻下藤县。
3月16日黎明,日军集中炮兵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射击。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驻守滕县的122师师长王铭章心中十分清楚,滕县已岌岌可危,但他对士兵们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
16日晚,王铭章决定留下部分士兵死守县城,然后把主力撤到城外。何宏钧回忆说:“其实这个方案应该是对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不同意,要死守。”最终,王铭章决定死守滕县。于是,他们几个城门全都封闭,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出,并且他还告知全城将士,他决心和战士们一起抵抗到底,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这天晚上,除了西关以外,滕城已经完全被敌人包围。17日下午,鬼子炸开南门进入南城,东门随即也被攻破。当晚,日军攻入城中,王铭章亲率自己的警卫连向日军进攻。战斗中,王铭章不幸腹部中弹,他高喊:死守滕县!随后饮弹殉国。何宏钧说:“王铭章下去以后发现敌人就打,但是你是手枪,人家是机关枪、步枪,怎么打得过,最后全部被打死。”
王铭章的尸体被连夜拉到利国驿,到那以后,他的夫人来认尸。何宏钧说:“夫人一看他那个袖口上的梭子花边,就认出来了,老夫人就开始痛哭,我们都痛哭。”说到这里,何宏钧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流出了眼泪。
王铭章为国捐躯后,国民政府明令予以国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17日傍晚,还有三百多名伤官伤兵滞留在西门一带,因为没办法逃出城,所以每个伤员都准备了一个手榴弹。战斗结束后,日军挨家挨户地清查,发现这些伤兵后,让他们投降,伤兵却陆陆续续走到一起,不约而同地拉响了手榴弹。
三百多人就这样以身殉国。
3月18日,滕县宣告失守,至此,122师师长王铭章以及全师两千余人全部殉城。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父手谕。
——一位川军父亲写给儿子的白布旗。
滕县保卫战打了三昼夜,阻滞了南犯徐州的大量日军,为鲁南各部队赢得了部署时间,仅凭这一仗,装备落后的川军就打出了声威。滕县城破后,何宏钧和124师的部分战士成功突围,狂妄的日军矶谷师团约四万兵力自滕县大举南下,直扑徐州东北的门户——台儿庄。
台儿庄
1938年3月末,本该是部队发饷的日子,但第2集团军27师的鲍鸿海却没能领到军饷。他说:“那时候发几块钱,都高兴得很,不到月底就盼着,结果没有发饷就开上去了。”鲍鸿海所在部队接到的命令是:火速增援台儿庄。
部队还没有到达台儿庄,震天的喊杀声就已经传来。经过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台儿庄已经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从3月23日开始,台儿庄就被包裹在一片硝烟之中。争夺台儿庄的战斗首先就在北城门打响,日本对北门狂轰滥炸,北城墙被炸塌,小北门亦被毁,经过三个昼夜的猛攻,日军终于攻破城防,守卫小北门的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的惨象至今仍印刻在鲍鸿海老人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死尸谁也不知道是谁,到处都是血,到处都是死人,天拂晓的时候看不很清楚,等到天亮了以后,哎呀,看得人害怕得很。”
4月3日,台儿庄三分之二的部分已被日军占据,守军在台儿庄南关死拼不退,总司令孙连仲直接给李宗仁电话说:“第2集团军伤亡十分之七,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2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的回答是: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鲍鸿海清楚地记得,孙连仲当时给各师下达的命令是:死守台儿庄,台儿庄在你在,台儿庄不在你不在!“那时候用人,后勤部队都用上了,连送饭的、炊事班的、通讯班的这些人都用上了。”
该日黄昏,猛攻数日的日军也已经筋疲力尽,暂时停止进攻,休整部队。被炮火声淹没了数日的台儿庄终于安静下来了。午夜时分,日军阵地突然传来一阵阵喊杀声。五百个敢死队队员背着大刀,每人配备了两个手榴弹,连枪都没带就冲进敌营,经过激烈的拼杀,他们最终将东门桥夺了回来。“逐街逐屋的拉锯战,胶着状态了,他的大炮不能打,飞机不能炸,坦克车也用不上,这时候他优越的威力用不上了,可是我们大刀片可派上用场了,一声喊杀,劲儿可大了,都砍头啊。”回忆到这,鲍鸿海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些驰骋疆场的峥嵘岁月。
仓皇应战的日军乱作一团,原本被日军占领大半的台儿庄,又被中国军队夺回。与此同时,汤恩伯率领的第20军团已向台儿庄以北逼近。凌晨时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带了几个随员亲赴台儿庄指挥作战。
当时,27师79旅和30师把日军桥外边的后援切断了,后续部队攻不进来,在台儿庄的日军就乱了阵脚,经过激烈的战斗,到4月7日早晨4时左右,台儿庄内的日军基本被消灭干净。
从3月24日开始,到4月7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历时十四天,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全歼矶谷师团主力约一万多人。然而,胜利代价是如此之大,中国军队损失将近两万人。李宗仁望着重叠仆倒在地的中国守军尸体,跪倒在地满面泪涌,随同的将士也一起跪了下去放声号哭。
“台儿庄是红血洗过的战场,
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
他们的尸身是金石般的雕浮。
台儿庄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用血铸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在残破的北关城墙插上了国旗。”
这是著名诗人臧克家为了纪念台儿庄战役所写的一首诗,回忆起往事,鲍鸿海老人显得有些激动:“仇报了,给中国人出口气了!都知道把咱的士气鼓励起来了,谁也不愿当亡国奴。”
台儿庄捷报传出后,南京、上海沦陷后笼罩在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台儿庄血战,几乎成了民族复兴的新象征。
1938年4月,在台儿庄遭受惨败的日军又反扑临沂,此时的李宗岱正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在攻打日军阵地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穿。“打鬼子丢了一只眼睛,不要紧,我还有一只眼睛可以看,所以无所谓。那阵儿我的腿还没受伤,只是眼睛看不到没关系,手脚都还可以动。”
受伤之后,李宗岱被送到徐州兵站医院,七天的抢救把他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但他的右眼却永久性失明。国民政府奖励给他两万四千块大洋,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八百多两黄金。他把奖金连同自己的金戒指、金镯子一起捐给了抗日救亡中国会。伤好后他又回到了部队,他和所有战士们想的一样:只要鬼子还在,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
对于台儿庄战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提到“我军以区区十余万疲惫之师,在津浦路上两面受敌。来犯的敌人,南北两路都是敌军的精锐,乘南北两战场扫荡我军主力百余万人的余威,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孰知竟一阻于明光,再挫于临沂,三阻于滕县,最后至台儿庄决战,竟一败涂地,宁非怪事??”。然后从敌我双方4个方面充分分析,认为台儿庄一战并非侥幸。”
台儿庄一役,不特是我国抗战以来一个空前的胜利,可能也是日本新式陆军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惨败。足使日本侵略者对我军另眼相看。——李宗仁
台儿庄的战斗则更像是一群军人为这个民族的赎罪之战!
臧克家在一首诗里这样感叹:台儿庄,红血洗过的战场,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
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这实在是一场血战,我几度沉浸在战场上的热血豪情之中,不管是哪一仗,我都相信,士兵们无不杀气腾腾,拼死一战。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载:抗战八年,仅四川就提供3,000,000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出川将士阵亡364,000人,负伤356,000人,失踪26,000人,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
这里讲的川军,原指民国时期军阀派系之一。不过,与其它的地方派系不一样的是,川军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早期的有刘存厚、熊克武,晚期的有刘湘。刘湘在抗战中战死后,川军形成邓锡侯、杨森、潘文华、刘文辉、王陵基五个上将争雄的局面,外人称之为川军“金木水火土五行”。表面上,川军内部派系繁杂,防区制盛行,完全没有国家的概念,各自为战。
长期以来,让人们对川军存有比较坏的印象是1963年拍摄的电影《抓壮丁》。这部电影主要剧情是:抗战中,1942年前后,四川军阀天天在抓壮丁。地主李老栓一家人和王保长、县上管兵役的卢队长之间,相互“狗咬狗”——卢队长勒索王保长,王保长诈骗李老栓、调戏三嫂子……该剧一些经典台词是:“出征军人是打中国人的,”“出征军人看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个”。让人啼笑皆非之余,又对所谓的“川耗子”充满了鄙夷。总之,这部电影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抗战中四川军阀及川军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大发国难财,利用国难壮大自己。严肃地说,《抓壮丁》是极左年代的产物,虽然以抗日战争为时代大背景,里面却丝毫看不到四川人民与川军参与抗战的任何爱国行动,这是非常偏颇的艺术宣传。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死守临沂的庞炳勋带领部队死战不退;内战中的仇敌张自忠不计前嫌,星夜驰援;藤县拒敌的王铭章对此更深有体会,“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之罪愆了!”藤县一战,王铭章高喊“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杀身成仁。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说,这一仗应该是惨败,因为三千人的牺牲换来的是日军仅百余人的伤亡。可川军赢得了尊重,正是川军的巨大牺牲才换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将军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
这里有兄弟情深、有报答知遇、有同仇敌忾、有血战至死……所有的情愫交织起来,第五战区完成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打鬼子的战斗,而是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一场精神洗礼,它如此完美的诠释了这场民族战争的内涵——只要鬼子还在,他们就要继续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