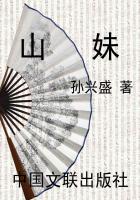后来,他就卷着袖子,攥紧拳头,笨拙地恶狠狠地扑过来。我和廖森闭了眼睛,站着不动,准备接受他的惩罚。轰的一声,拳头落在了身旁的墙壁上,屋顶的灰尘扑簌簌掉了下来,有一只叫不上名目的虫子也被震醒,在屋梁上翻山越岭地乱爬,我觉得它会钻进我的耳朵去,浑身痒酥酥的。
那一天,他直骂得天昏地暗,并勒令我俩写出深刻检查。
第二天早上,我就写了一份检查,廖森也签上名,派我送去。
闵老师刚起床,办公桌上放着一碗稀饭,热气腾腾的样子,他正从一口锅里提出一大片荞面烙饼,油油的、软软的,散发着香味。他把它卷起来,然后咬一口,经过漫长一段时间的咀嚼,就伸长脖子咽了下去。后来,他就端起碗,美美地喝了一口稀饭,往下咽时,紧紧地抿着双唇,脖子往前一伸,从牙缝里挤出一些汁液,由于压力大又从双唇间涌出来,白白的一条线嵌在两片有些干裂的嘴唇间……他似乎是在延长着进食的幸福感。
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饥饿,早晨在学生灶吃的酸菜、黄米饭这时使胃隐隐作痛,手心里出了汗,唾液分泌满嘴。如果让我吃,我会把饼子撕成碎片泡在稀饭里,用筷子一块一块捞上来吃,而不是一手端着碗,一手捏着饼子,吃一块喝一口,喝一口吃一块。我砸吧了嘴,咽下一口唾沫在心里想。
他终于把目光投向我,但比昨天柔和了许多。“昨儿我太过分了,不介意吧?”“您收拾得对!”我赶紧说。
这时,他就从自己的手里撕下一块饼子递给我,笑着说:“吃点吧!”“不吃的,吃过了!”但手却微微前倾了一下。他把饼子塞到我手里,我就站在他面前吃完了那块饼子,只觉得那是平生吃过的最香甜最令人陶醉的东西。
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愉快地跳了两个蹦子。
秋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初二的学生了。
开学不久,学校的机井坏了,断了水源,几天内又修不好,所以须放假。早晨,闵老师来到教室里说明了情况。但他又说,他请示了学校领导,他也愿意牺牲放假时间留下来为我们补课。他说离校五里路有个村子,到那里可以取上水。然后,他就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动情地说:“同学们,现在的社会不看重知识,这是很令人悲哀的。我相信总有一天这种情况会改变。大家还是跟着我,好好学一点实实存在的知识吧,将来总会有用处的……”这时教室里就有一些的响动。有少数同学显然是从他的话里获得了共鸣,嘴唇有些激动地歙动着。但绝大多数同学都表现出一种麻木和冷漠,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知识其实是不值钱的。既然老师已决定留下来补课,他们还能够说什么呢。
那天在课堂上讲话的时候,早晨的阳光从窗户上斜照进来,在他的脸上涂了一层淡淡的黄晕,他双手扶着课桌,形象显得凝重、肃穆,令人产生面对父亲时的感觉。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情景对我后来的想象力产生了那样深远的影响。
下午,就去取水。我们从周围的生产队借来两辆胶轮车,装上小水罐。闵老师把男生分成两组。一辆由他掌辕,一辆由廖森掌辕。
我们迎着午后有些疲倦的太阳,踩着软软的衰草,行走着。有时一只肥大的黄鼠从脚下惊走,有时一群山鸡从草丛里扑棱棱飞远。成熟了的粮食的暗香混合着泥土的香味,直撩得人心痒个,一种对生命的新鲜的热烈的情感也就涨满了全身。
我们很快赶到了那个村子,装满了水。但这时大家望着来时的路都有些胆怯,饥饿的肚子也开始咕咕作响。
回家的路上,车子陷进了一个沙窝。
闵老师眨巴着眼睛,双手紧握着车辕,勾着头,弯着腰,套绳勒进了他的肩胛,阳光和风勾勒出身体变形的力度,额头上粒粒虚汗在脚下炸响。他喊“一、二”,我们也喊“一、二”。大家都使出了所有的劲,但车轮在沙窝里越陷越深。他火了,回头朝我们吼:“吃干饭的,使劲!”
我低下头去,重新调整了姿势,把两只已经酸疼的手支在后车沿上。这时,从车底望过去,我看见了他的两条腿,卷起的裤腿,有一只已经掉下来了,另一只青筋暴凸,肤色如血。不知是汗珠还是水滴浸湿了腿上的毛,使它们倒伏着,如四野的衰草。我突然担心他会摔倒,这个世界会塌陷。
在他最后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声中,小车轮子终于从沙窝里拔了出来。我们来到一个比较平坦的场地,他放下车辕,说:“休息一会儿吧!”
我们刚接到这医生许可,就都软软地瘫倒在地,被汗水浸湿的睫毛,好吃力地张开,整个世界都像在喘气。
闵老师坐定以后,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一卷我们的作业纸,撕下一绺,卷成一个圆筒,用唾液粘住了纸角,然后从口袋里拈出一撮旱烟灌进筒里,捏一捏,拧紧封口,用火柴点燃。他用袖口擦一把汗,运足气,意味深长地吸一口,在嘴里品咂、酝酿,一缕淡淡的蓝烟从嘴角、鼻孔袅袅地溢出。这时,他就闭上眼睛,挤了一鼻子褶皱,“哈咝——哈咝——”这声音把那旱烟的辛辣与刺激强调得淋漓尽致。
后来,他才注意到了东倒西歪的我们。“同学们饿吧?”他说。
他停下抽烟,用手在四只口袋里吃力地摩挲着。终于,一张五元钱的钞票被他从上衣袋里用拇指和食指轻轻牵了出来。他把钞票在秋风里抖一抖,一甩胳膊,一个优美的弧线:“村子里有代销店,饼干什么的总有吧,谁去跑一趟?”
没人吭声。廖森说:“哪好意思让您破费!”“没啥,没啥,金钱乃身外之物,我一向不怎么看重。快说,谁去?”
廖森只好说:“那我去吧!”他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就走了。
半小时后,廖森买回来了面包和饼干。闵老师看着我们风卷残云般吃东西的情景,表情就有点意味深长,仿佛是陷入了回忆。他问:“低标准时候的事情,你们谁还记得?”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是1963年以后出生的,只有廖森说,那时候他跟着母亲要饭吃。
闵老师就说:“我今年40岁了,细想平生所为,大都问心无愧。只是那年夏天,做了一件使我终生感到内疚的事。事情的起因也是饥饿。那天我在村子里的小学上完课,饿得走不动了,太阳在头顶散发着黄晕肮脏的光,地球也开始旋转了。我强撑着身体,回到家里胡乱翻寻,希望能找到一点吃的东西。后来,我就拉开了我家堆放杂物的土屋的门。这时,有一只母鸡呱嗒嗒地从我的胳肢窝里蹿出去。站定后,我发现木屑堆上有几个鸡蛋:莹洁、浑圆,散发着诱人的光。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极其认真地数了一遍,是八个,比七个多,比九个少。我转过身去,朝那母鸡飞去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八个鸡蛋救了我的命。可是傍晚当睡在炕上将要进入梦境的时候,隔壁家的吵闹声清晰地传入了我的耳鼓。”主妇正追打着一只鸡,拖着哭腔骂它:“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那只鸡在院子里呱嗒嗒地乱飞。”
“我明白了一切是咋回事,心里涌起一种难言的感情,想给邻居解释一下,又没有勇气……”
他说着就泪眼迷离了,扔了抽剩的半截旱烟,低头坐着。
好一会沉默。廖森就换一个话题说:“闵老师,您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老婆和三个孩子,都挺好。小女儿已经五岁了,认了不少字,还能背几首古诗。”说着他就模仿女儿奶声奶气的童音,念了一遍“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把大家逗乐了,笑得前仰后合。最后他说,他已决定把老婆和孩子接来,让孩子在镇上读书。他说出这个打算的时候,我就觉得生活确实充满了许多新鲜的内容。
时隔不久,师娘就带着三个孩子从乡下来到这所学校。廖森最先向大家发布了这个消息。“师娘很年轻,看上去比闵老师小许多,长得很不错,嗯,很不错!”他说。
下午吃过饭,廖森拉我:“走,看看闵老师老婆去!”我们当然是借故去的。喊了“报告”,就进去了。闵老师正捅炉子准备做饭,师娘坐在炕头上纳一个鞋帮,三个孩子头凑在一起看一本小人书,一种淡淡的生活的温馨已经笼罩了这个单身宿舍。
她给我们让了座,沏了茶,就开始聊家乡琐事。她说话声音大,很健谈,有时把唾沫星溅在我们脸上,廖森的嘴唇就轻轻动了一下。那天她留我们吃了荞面搅团。
后来的星期天,我和廖森常去帮她干点活,关系就很融洽了。师娘说,她有一个心愿,就是把三个孩子的户口转成城镇户,将来好在城里找个工作。“你们闵老师啥都不管,就知道教书!教书!”声音里有娇嗔也有失望。
廖森说,他爸是公安局长,他可以帮忙。
师娘听了这话,目光立刻明亮了许多,认真地看看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一趟!”
“星期天吧!”他答。
闵老师听了这话,就在一旁摇摇头:“这合适吗?这合适吗?”
一个星期天,师娘就挎着一篮子鸡蛋,和廖森登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两天后,他们回来了。班车停在学校门口。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他们下车的情景:车门开了,廖森先走下来,然后是师娘,当她一只脚已经跨到地面的时候,廖森轻轻搀了一下,师娘抬头朝他看一眼,一个媚笑。那时候,阳光极柔、极灿,师娘的脸色极润泽、极鲜嫩,在她抬头的一瞬间,真是鲜明极了。我觉得阳光有幸,师娘有幸,我也有幸。
之后,在闵老师外出听课的某个晚上,就发生了那件事。
我去找廖森,去闵老师房子找。屋子里灯光朦胧,门关得很紧,一阵阵累极了的喘息声从门缝里传出来,叫人有缺氧的感觉。“当当——”我下意识地敲门,里面传来的声响,有些急促。
“当当——”又敲。一会儿,门开了。廖森伸出头朝左右看看,额头上是浓重的汗迹,声音却有些干燥,“啊,是你!”他侧转身把我让进去。师娘低头侧坐在炕头,头发有些散乱,脸膛上罩着一层火红的霞晕,在夜晚里有些烫人。白皙的脖颈越发显得修长,外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三个孩子早已熟睡了,均匀的鼾声衬托着夜的宁静。我说我该走了,廖森就朝我含义丰富地笑一笑,关上了门。
那天晚上,我在漆黑的校园里徘徊了许久许久。我有点不忍心再看见闵老师那笨拙的一撇一撇的身影。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闵老师的孩子仍然是农村户。那时候,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给师娘和孩子承包了二十亩土地。闵老师为了养家糊口,就带着全家回到了村上,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书,余暇种田。
临走的那天早上,我和一些同学去送他。一辆毛驴车装上了他的全家。闵老师牵着缰绳,迟缓地转过身来看着我们,有一线笑意从唇纹处诞生,迅速地掠过脸际、眉梢,在许多皱纹的额头上一闪就消失了。
师娘坐在车子上,一动不动,只是用有些凄然的目光打量着来人。我感到她的目光颤颤抖抖地徘徊在我脸上,突然,她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声音凄厉得如同破空而来的哀乐。
闵老师骂她:“哭啥,尿多!”而他自己也湿了眼圈。
然后,他就一撇一撇地牵着毛驴走了,把一串串冷涩刺耳的驴车声留给我们。
那时候,廖森早已进城招干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