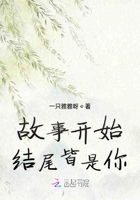凤四一腔怒血如同被泼一盆冷水,“朕不信,邵修城你信口开河,一派胡言,不过是为你卑鄙行径开脱!”
邵修城眸光冷冷,依然自顾自地道,“建元十三年,邵祁第二次战争的第二年,彼时,顾晓枫十七岁,尚未与你相遇,顾卫邦被朕生擒,顾晓枫为救父乔装闯入朕的军营,她救走了顾卫邦,却被朕的龙卫生擒,也就是那时,顾晓枫与朕结下不解之缘。”邵修城心里微微的疼痛,也就是那时,他悄然喜爱上这个敢爱敢恨英姿飒爽的女子,心里种下了一丝不为人知的情愫。可惜,彼时顾虑太多,他终是把爱压在心底,放走了她,生生错过了第一次相遇的缘份。他从未曾料到,因他的一丝顾念,那女子后来的命运竟如此不堪。
若论相遇,他比祁封越更早遇见她!
邵修城目光如井水寒澈见底,紧逼一步,冷斥,“你登基半年后,清肃废太子祁封元一党,顾家三族被抄,令顾晓枫一夕之间失去全部亲人。虽然你念顾晓枫与你的情义,没有废后,但失了母族的僻护,她在皇宫内的日子并不好过。好在,那两年你对她情义不薄。可惜,建元十六年,邵祁第三次战争,顾晓枫随行伴驾,在混元山脉途中,她被流寇所劫,被朕龙卫所救,朕派人护送她至你军中,你却听信乔震之女,随军医侍乔语嫣的挑拨,认为朕和顾晓枫有私情,恰巧,顾晓枫第二次身孕,乔语嫣故意将胎儿月份说迟一个月,你疑心甚重,怀疑顾晓枫与朕有私,最后你逼她落子。顾晓枫伤心欲绝,几次离宫,却被你掳回。你为了把她强留在身边,以她的皇子要挟,自此后,顾晓枫将自已锁于鸾凤宫,再不曾踏出半步,也不肯再见你。顾晓枫是如何死的,你想知道么?她是自 焚而亡!凤四,你还想听么?”
邵修城闻讯顾晓枫自 焚,他派龙卫寻到了她遗下来的一封血书。血书只留几余字“来生我们不必相遇!”。
他凭着那些遗留的血,种下情牵。因此他们在中国的二十一世纪再次相遇,在若璃车祸身亡后,他将她送回那时空,欲改变她的命运,却因为朴修元札记的缺失,他始终无法冲破元神,无法恢复所有的记忆,于是前世的自已再一次地错过了她,无知无觉中,竟做出了一样的决定,驾崩前在她身上种下情牵,意图在下一世中找到她。兜兜转转,他的心,至始至终全然是在她的身上。
在帝陵朴修元结界中,邵景弘恢复了他三世记忆,原来,他的她的缘份早就已定三生。也是他自已生生地错过,幸好,一切还来得及挽救。
“一派胡言!”凤四怒极,眸光诡谲阴沉,蓄足十成内力的手已经悄无声息地化为掌,猛地向邵修城的脑门攻击。
邵修城身形一晃,避开,凤眸如历芒,“凤四,你始终不敢面对真相,你在守护心爱之人时,你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你太轻信他人。这一世,你明知乔语嫣心怀不轨,你还是将她留在身边,以致让她有机会伤害衣儿。凤四,朕将真相告诉你,就是要你放弃纠缠,希望你与她的缘份就此结束!”
“你以为你凭空捏造,朕就信你一派胡言?”一掌落空,如影追随,紧接一掌,疼痛和错乱从裂开的胸口处传来,空气里弥漫沉沉的血腥,他死死盯着邵修城,眸光里全然是绝望与烈焰般愤恨。
邵修城并不还手,身如行云流水地踩着虚位避开,“那朕问你,你据实回答,彼时,你娶宁红衣之际,你是否也是怀疑衣儿与朕有染?”
凤四足下一滞,想起那时候,他确实恨她,甚至怨她的背叛,他将她掳至祁皇宫的当夜,就对好极尽羞辱。
邵修城眸讽然一笑,紧逼一句,“你不否认!那朕再问你,若衣儿彼时不仅与朕有染,而且腹中已有朕的骨肉,你又会如何做?”
“什么?”凤四显然不明这话中之意,掌力一收,挑眉怒道,“你不要污辱衣儿!”
“你会原谅她,你会依然视她为你一生最爱。这一点,朕对你从不曾怀疑。”邵修城摇摇首,冷冷而笑,“可是,你决不会容得下她腹中孩子,朕可曾说错?凤四,你爱一个人爱得太疯狂,爱得太固执,你眼里容不下一丝的瑕疵,就象是在青河岩洞中,你见衣儿与朕在一起时,你可以用那样的言辞去伤害她,你的爱是两面刃,你伤了你自已,也将衣儿伤得体无完肤,凤四,你的性情注定了你不可以给衣儿幸福。”
“难道你能做到,你忍受得了你的妻子与别人诞下孩子?”凤四微微翘起唇角,嗤之以鼻。
“朕可以,只要那是衣儿的孩子,只要她幸福,只要她过得好,朕怎样都可以。”邵修城淡淡地回了一句。
凤四挑眉,再一次嘲弄地弯起嘴角,“邵修城,你说的话,朕一个字也不信,如今,朕已经兵临城下,到时天下都是我凤某人一个人的,你邵家人又有何立足之地?”失了皇权的邵氏后人,就算不生不生不灭又当如何?
“容玉会败,是因为他年轻,根基不足,驾驭不了姚凤两家,单论两国实力,祁国国力远不足以和邵国抗衡,如今黑蛟沼泽既已通行,祁王卫队能够穿过,朕的暗卫自然也能,你真有把握与朕打这持久战?”邵修城不以为意地笑,“不论持久,就单论目前,你带着祁王卫队孤军深入,朕已命姚家的人切断你的后援粮草,你这战能打多久?”
凤四不语,若与邵容玉交手,他有必胜的把握,但对邵修城,他确实相信他有起死回生之术,将残局逆转。
“凤四,你做这么多,无非是想逼我出世,如今你也见到她,你该死心了,她把过往一切全忘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
是啊,这才是他心结所在,她已把一切过往全然忘记,他与她的爱全成了一场空!凤四易过容的脸上除了疲惫之色,还有浓浓的嘲讽,“你字字珠玑攻击朕,可你扪心自问,换成你当如何?你若放得下,你会逆天死而复生?”
“朕死而复生并非是因为放不下,确实来说,当日朕早已放开她,只求续一份来生的缘份,朕会回来,是因为再一次看到她的不幸,朕不想再见她三世离殇,这样的爱对她来说是一场场的悲剧,凤四,你放开她。“
“朕偏就不信这个邪,难道是生是死全由你邵家人说了算不成?”
“由不得你不信!”邵景弘突然而至,他的怀中竟抱着一个婴儿。
凤四退开一步,眸光在两人中巡视,频频发出冷笑之声,“是你?邵景弘,虽然你曾救过朕,但是朕并不感激。你今日插手,是不是也想封住朕对衣儿的记忆?”难怪宁红衣会失忆,这世间还有什么是邵家人做不出来?
邵景弘淡漠一笑,并不理会他的冷嘲热讽,“祁封越,朕怀中是你和宁红衣的孩子,现在交还于你!”他将孩子抱到凤四身前。
“朕的孩子?与衣儿?”婴儿似乎在沉睡中,这让他有一瞬间的恍惚,这会不会又是幻觉……
“当日,屠央把宁红衣带回时,她腹中已有骨肉。祁封越,无论你愿不愿意,你与宁红衣的缘份已尽,因为,三年前朕从你身边带回的一个魂消香断,一个是毒发身亡。既使宁红衣记忆恢复,你与她之间也已成死局,此生此世,你与那女娃儿已无缘可续。”
是......这就是他无法堂堂正正地站在她的前面,告诉她,他才是她的爱人!
凤四茫茫然接过孩子,流着泪看着明黄缎被下那个初生婴儿粉嫩的脸,此时的他,觉得自已比怀中的婴儿更脆弱不堪,孩子,衣儿和他的孩子,为什么幸福就在咫尺,却一次次擦身而过。
衣儿,衣儿......我知道了你的委屈,他日......你又可知我的委屈?
手指抚摸上那幼嫩的眼,小小的鼻尖,留在了那粉粉嫩嫩的婴儿小唇上,俯下身,印下细腻的亲吻,“朕的孩子......”突然凤四脸色疾变,怒喝,“为什么会这般小?论年纪,朕与衣儿的孩子已有三岁?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这孩子一出生就养在结界中,若非如此,当时的情况他也活不成。如今这孩子总算是完壁归赵,祁封越,你退兵吧,祁邵最终会在这孩子手上统一,但目前邵国气数未尽,何苦徒然让百姓流离失所。”
邵修城淡淡一笑,如今他也知道在建元四十四年,他带着宁红衣离去后,邵容齐继位,不出三年,就被年仅二十四岁的祁国新帝所灭,祁邵最终统一。
邵景弘上前一步,“你口口声声怀疑城儿的话,现在朕就恢复你所有记忆。包括城儿未介入前,你和顾晓枫的前世和来生。”
虽然此前宁红衣早已有思想准备,但见到邵容玉的那一刹那,极力压抑的呜咽之声还是从喉中流溢了出来。
她对他的记忆尚停留在他十三岁的那年,在京郊狞猎中,她抱着他纵马飞驰,在寒潭中,她抱着他一起驱去身上的寒意。
那个曾经最象邵修城的孩子——有着冰雪般的气质,墨色琉璃般的凤眸。
如今的他明显长开。就算是靠在床榻上,她也看出眼前的少年的身量早已不是记忆的模样。
“过来。”邵容玉脸上并没有多大的悲伤,反而在看到她的一刹那,脸上飘过极致的欣慰,他费力地对她扬了扬手,象久别朋友见了面一般,极平常地拍拍床沿,“衣儿,坐这里......”
宁红衣吞咽下所有的情绪,缓缓靠近他,依言坐下,展颜一笑,“都长这么大了。”
“笑得好难看,别笑了!”邵容玉撇了一下嘴,眸光带着戏谑,却又溢着笑意,“想哭就哭,又不是没见过你哭!”说完,他轻轻地咳了几声,看他的表情,明显是压抑着。
“很难受?”她看他歪着身子摇摇欲坠,忙倾身上前扶住他。邵容玉将头靠在她的肩上,他伸出双手搂住了她的腰,那样的姿势象极了彼时在寒潭中相依相偎取暖时的模样,他唇角满意地扯开,缓缓闭上眼,”衣儿......别动,就这样......让我靠一会。”
从受伤以来,伤口一直反复疼痛,低烧不断,除了伤口疼,浑身的每一块骨头都象被拆卸开一般疼,太医诊断更可笑,说是外伤并不是致命,而是他身体的内腑早有隐疾潜伏着,是因为早年中的慢性之毒终于发作了。
“衣儿,我疼......”他低低地呻吟,他最疼的是心脏,自从他知道她的死讯以后,那一次从未曾正常跳跃过。
宁红衣闭了闭眼,泪终是忍不了,行行清泪惭惭落下,“我揉揉,揉一揉就不疼了......”她伸出手轻轻揉着他的腹部右上方,掌心处,明显感到那一处鼓了起来,她知道,那是肝脏的地方。
“衣儿,你怪我么?”他突然间如呓语般,颤着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你恼我同意了联姻,害你受了那么多苦了,如果,我早点去寻你,你就不必受那些苦了,是不是?所以,你明明好了,也不愿来见我,是么?”他一直懊悔,听了那些老臣子的话,没有及时去接她回来,结果,等来了她的死讯。
“什么?”宁红衣愣了半响,看他如此虚弱的模样,眼底上翻涌而来的泪意有一半灌进了鼻中,连着说话也变得吃力,“容玉,你说什么......我听不大懂,我把很多事情忘了。”
“哦......“邵容玉苦苦一笑,他也觉得自己是烧糊涂,竟然又徒生幻觉,以为回到了梦境中,”是......呀,父皇说你把很多事忘了,还提醒我,不要说太多过去的,怕你伤心。我又忘了。瞧,我现在的记忆......”
“容玉,”她紧紧地,紧紧地把那他带着反常热度的身体抱进怀中,“我都愿意听,我也不知我忘了什么,你问我怪不怪你,我现在就回答你,无论你做过什么,我都不会怪你!容玉,我只想你快快好起来,我带你骑马,好不好?你快点好起来!”
他勉强地仰起头,看着她,“谢谢你,衣儿,能在这时候再见到你,我死了也是眠目,我很高兴......”他的声音很虚弱,苍白的脸努力地挤出半丝笑容,“这几天,我不是梦到你,就梦到我母妃。我梦到你时,你总是对着我在哭......梦到我母妃,她却是在笑着对我扬手。想来,这梦全是反的......”声音渐渐地小了,邵容玉又昏迷了过去。
“睡吧......睡了就不疼了......”宁红衣心疼地将他抱在怀中,不时地亲吻着他的额际。
水灵儿进来时,看到这一幕,眼圈一热,咬了咬唇忍了下来。
她倒了杯水,将怀里的药丸放进水中化开,走到榻边,轻声道,“可以叫醒他么?这药可以止痛,让他少受些苦。”
“他睡过去了,睡着了,就不会疼。等他醒时,再喂他服下。”宁红衣轻轻搂着他,眼里是难以隐藏的担忧和心疼。
两日后,祁王卫队突然退兵,帝都危机化解。同时,新帝驾崩,与此同时,在流坡河上南下的一行舟上,一个嘹亮的婴儿啼哭声直划过天际。
同月底,邵修城于帝都登基,恢复年号为建元。
宁府门前再次恢复车水马龙的光景,不过,来往的不再是以往帝都士豪新贵,而是名门贵妇和仕家女子。
宁红衣接到的递贴拜访,都是铭书求见华清公主。宁红衣也知道自已的身份奇特,但她不想隐姓埋名换一个身份进宫伴驾,只是暂缓和邵修城大婚的日子,当然不是为身份所尴尬,而是刚经历了两年战乱,百废待兴,实不宜操办立后大典。
这几日,宁红衣的三个姐姐相继带着各自夫君回到宁府。
王氏自宁钟元去逝后,在元宝寺念了几年的佛经,性情倒超脱了几分,不象以往在宁家战战兢兢的模样,在王嬷嬷的相助下,倒把宁府打得得井井有条。
宁红衣陪着母亲说了一个多时辰的话后,侍候母亲歇了下来,王嬷嬷提着灯笼送她回房。
“嬷嬷,今天几个姐姐是不是在母亲跟前说了些什么,我看母亲晚上心思很重。”穿过几个长廊,因为几年宁府无人长住,除了看管门户的宁府管家外,多数的奴才已被谴散,除了草鸢飞长无人料理外,宁红衣还看到很多地方也现破败和残旧。
“还不是想着老爷留下的那些田产,寻思着分了。老爷留下的那些个田产,都是小姐在宫里那几年皇上赏下的,当初小姐还年幼,就全落在了老爷的名下,其实老奴也知道,那是皇上赏你的。光京郊外的那几千亩良田就够吃几辈子,也难怪她们姐几个眼馋。只是碍于如今小姐的身份,一时不便提。”王嬷嬷愤愤不平,那些年皇帝赐下时,她当时侍候在宁红衣身边,自然一清二楚。
“身份?”宁红衣哑然失笑,邵修城一登甚至,急于安抚各方灾情,根本无法腾出时间理清两人的事,所以,朝堂内外,并没有人多少人知道如今她和邵修城的关系。
“你说,在她们眼里,我是什么身份?”回来前,邵修城有隐隐跟她透露,祁国上下的人皆知,她曾被祁国所掳,而后,才引起两国争端,邵修城将她救了出来。她想,那时她肯定吃了不少苦头,方会失忆,如今既然回到他的身边,过往的事也不必想得太多。
“老奴估摸着她们也闹不清,按说,小姐是皇上亲封的华清公主,而后远嫁祁国当了皇后,如今突来回来,以未嫁的身份回宁府。朝庭上没个说法,那边个祁国也没见个动静。她们打听不出什么,所以也不敢太撕破脸。”
“嬷嬷,那些地我不会给她们,我自已有用。但凡数于爹留下的东西,我一概不要,他们要,我全给她们。”邵国刚刚经历战乱,她想把那些地的收成分给那些灾民。再添些银两办些手工作坊,安置灾民。
“只怕她们不死心,老爷能留多少东西,不外乎就是这个宅子,靠那几十亩地的收成的钱多数给老爷添了些古籍罢了。至于这宅子,夫人还活得好好的,谁敢提出来分,闹出来,不给人笑死才怪。”
“嗯,嬷嬷说的有理,母亲向来喜欢听你的,你明日跟母亲提个醒,要是她们再问起,就一口回绝,要是她们有意见,直接来找我便是。省得她们借口回家天天烦着母亲。夜了,嬷嬷回去吧,最近秋凉了,多注意母亲的身子。“
回来后,每日光应酬那些名门贵妇就有些烦了,尤其这些人都带着试探的口气。自家人还不得清静。想起在流坡水城与邵修城隐居的日子,每闲时看花开花落,钓鱼,品茶多懈意。
进了寝房,一片黑暗,心里暗奇丫鬟去哪了,身后却一阵暖意,被人拥进了怀中,熟悉的香荚兰之味扑入鼻息——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