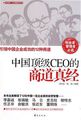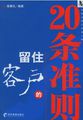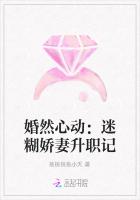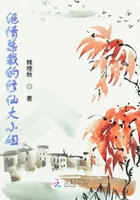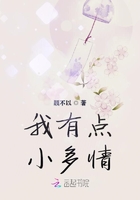读者在本书中,或者其他地方或许经常看见“收购法”和“反收购法”的字眼,但实际上,在美国法律中并没有名为“收购法”和“反收购法”的法律。只是在各州的公司法中都有关于公司间收购和合并的条款和判例,我们把这些条款和判例统称为“收购法”;其中的一些条款和判例又是具有反收购性质的,它们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公司间的收购,所以我们也相应地称这些条款和判例为“反收购法”。
为什么会有收购法的产生呢?
谈起美国收购法的产生,我总是会想起从前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所接触的一位教授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这位教授的研究领域并不是法律,但他的课是向法学院学生开放的。据说他的课讲得十分入味,且此人极富幽默细胞,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此我慕名前去聆听。一听之下,甚觉名不虚传。而这位教授在一堂课上的开场白对于我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影响颇深,至今仍难以磨灭。他说,20年来,每次开这堂金融法课【Financial Symposium】他都会引用一篇文章作为开场白,《金融法规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因为他十分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许多法规从形式上看来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实际上都是各个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
这为我们探索美国收购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线索。
收购法的联邦立法
直到1960年以前,恶意收购最主要的方式还是股东投票代理权的争夺。那以后,恶意收购者们发现直接购买目标公司的股票可以规避联邦法规关于投票代理权所作规定的风险并且可以省去因此产生的费用。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关于投票代理权规定未有覆盖的空白地带被现金要约收购所利用了,因为这种收购既不涉及证券发行也不涉及投票代理权的收集。恶意收购者将这种方式当做夺取并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的手段之一。为了对抗恶意要约收购,各个公司发展出了五花八门的反收购策略。而同时,美国国会及各州也相继立法来规范要约收购的全过程。其中国会通过的法律就有1968年的《威廉姆斯法》【Williams Act】。
威廉姆斯法的立法意图是避免法律的天平向目标公司管理层或者收购者中的任何一方倾斜。威廉姆斯法要求收购者公开收购交易过程中的细节,这个规定可以防止欺诈行为,从而明确地保护了目标公司的股东利益。同时,由于威廉姆斯法是由国会通过的联邦法律,因此,此后出现的各州所通过的相关领域的法律,都以威廉姆斯法为基准,如果被证明违反了威廉姆斯法,那么州法律就是无效的。
收购法的州立法
美国为数众多的州都拥有各自独立的立法权,而各州根据当地的经济状况、公司交易活动以及市场等因素来制定各自的公司法,其中当然包括收购方面的法规。由于并不是统一的行动,各州立法的脚步有先有后,对同一个问题看法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介绍收购和反收购法的时候,我们将同时期、具有同样特征的各州立法放到一起,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美国在收购和反收购的州立法的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代反收购法。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会自动将法院对每个案件的判决定义为立法,因此这三代反收购法也分别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标志。通过这三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判决州立法是否有效时,焦点都是判断它是否违反了我们前面所讲的联邦立法和威廉姆斯法及其立法精神,也就是在收购和反收购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不偏袒任何一方。
悲惨的第一代反收购法
游戏规则定胜负
1979年,MITE公司对芝加哥铆钉公司的收购战使后者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的收购法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也使这个案例成为第一代反收购法的代表。法院对它的判决决定了第一代收购法的命运。
争议点
《伊利诺伊州收购法》【1979】是否违反了联邦宪法的“最高条款”【Supremacy Clause】和“商业条款”【Commerce Clause】?
1979年1月19日,MITE公司发起了对在伊利诺伊州注册成立的上市公司芝加哥铆钉及机械公司所有流通股的现金要约收购。MITE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MITE股份有限公司是在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的,公司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
按照威廉姆斯法案的要求,MITE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14D—1表,表明MITE愿以每股28美元的价格收购芝加哥铆钉的全部流通股,这一价格比当时的市场价格高出近4美元。
而依据当时的伊利诺伊州收购法【1979】,任何意图收购该州目标公司股份的要约收购还必须在州务卿处登记注册。一项针对伊利诺伊州目标公司的收购在向州务卿提交申请后须经过一个为期20天的等待期,如果期间没有被要求举行听证,20天后视作登记成功。在这20天中的任何时候,如果州务卿认为有必要保护目标公司的股东,他可以下令举行听证会以裁定该项收购是否公平。而且,如果目标公司多数的外部董事或其在伊利诺伊州拥有涉及收购的有价证券10%的股东提出要求,也必须就收购举行听证。一旦听证得以举行,州务卿如果发现收购者并没有向受要约人完全和公正地公开与收购要约有关的实质性信息,或者要约收购是不公平的或是具有欺诈性质,他就有权依照伊利诺伊州收购法【1979】驳回要约收购的登记申请,即不批准该项要约收购。
然而,MITE公司并没有按照伊利诺伊州收购法的要求向该州州务卿报批,并且在宣布要约收购的同一天向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的美国地区法院提起了对伊利诺伊州收购法的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伊利诺伊州收购法违反了在先的威廉姆斯法和联邦宪法的“商业条款”。此外,MITE公司还申请一个暂时的禁止令和一个永久的禁令,以禁止伊利诺伊州州务卿执行伊利诺伊州收购法。
1979年2月1日,州务卿通知MITE,他将发布一个命令,要求MITE停止收购芝加哥铆钉。2月2日,芝加哥铆钉书面告知MITE:它将会向伊利诺伊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其计划中的要约收购。而MITE公司则向地区法院重申了禁令的请求。同日,地区法院颁布了临时禁止令,禁止伊利诺伊州州务卿对MITE公司执行《伊利诺伊州收购法》【1979】来终止其对芝加哥铆钉的收购。第七巡回区的美国上诉法院也支持地区法院的观点:伊利诺伊州收购法的若干条款因违反了威廉姆斯法而无效,它同时违反了联邦宪法的“商业条款”,妨碍了州际贸易。
“最高条款”不容侵犯
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伊利诺伊州收购法》【1979】是否违反了“最高条款”?美国联邦宪法的“最高条款”规定,美国联邦宪法、法规、条约优于与之发生抵触的州宪法、法规。也就是说,如果伊利诺伊州收购法违反了联邦的威廉姆斯法,也就违反了“最高条款”。
美国国会并没有明确禁止各州通过立法来规制公司的收购行为,而是由法院来决定州立法律是否与威廉姆斯法相冲突。当然,州立法律一旦在事实上与有效的联邦立法相冲突就是无效的。
因此,在这个案例中,争议点就是伊利诺伊州收购法是否以某种实质性的方式阻挠了威廉姆斯法目的的实现。
1968年通过的《威廉姆斯法》对公司收购中逐渐增多的现金要约收购做出了规定,该法律规定了几点要求:第一,在宣布要约收购之初,收购者要向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登记,公布或送交目标公司的股东,并向目标公司提供关于该要约的详细信息。收购者必须公开其背景和身份信息、收购的资金来源、收购的目的,包括任何进行公司清算或对公司组织结构做出重大变动的计划,以及收购方在目标公司持股的最大额度;第二,在要约收购的前七天,出让股份的股东可以撤销出让,如果收购方在要约收购发出后60天后仍未购买他们的股份,出让股份的股东随时可以撤销出让;第三,必须以同等价格购买所有被收购的股份,如果收购价格上涨,那些股份已被收购的股东应获得上涨的差额。
如威廉姆斯议员所解释的:“我们竭力保持公平的原则,既不偏向【目标】公司管理人员也不偏袒收购方。”“公平”代表了一种信念:在投资者面前,竞争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被给予额外的优势。投资者如果掌握了充分的信息,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国会不仅通过提供足够的信息来保护投资者,也会通过限制管理层或收购方的优势以使其不能够阻碍投资者做出基于充分信息的选择。
然而《伊利诺伊州收购法》中的三条规定打破了国会竭力维持的平衡,妨碍了国会对投资者的保护。
第一条,伊利诺伊州收购法要求要约收购人在要约生效前的20个工作日,将其进行要约收购的意图及要约的具体条款告知州务卿和目标公司。在这20个工作日内,要约收购人不能将要约条款送达股东。同时,目标公司则可以向其股东传播即将发生的要约收购的信息。此规定与威廉姆斯法的矛盾显而易见。依据威廉姆斯法,没有收购开始前的通知要求,而且关键的日期是要约收购“第一次公开或送达证券持有人”的日期。而提前将收购意图告知目标公司就是刻意为目标公司管理层制造机会来抵制要约收购,这严重违反了国会制定法律时的“公平”原则。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威廉姆斯法的立法过程中,国会曾经几次否决了设置一个事前告知的要求。
第二条,伊利诺伊州收购法关于听证的规定也是不符合国会立法原则的,因为这一规定人为的延迟了要约收购过程。州务卿可以在要约开始之前随时要求听证,且没有完成听证的最后期限。虽然州务卿要在听证结束后15天内做出决定,但听证的时间可能无限期地延长。不仅州务卿有权无限期地延迟一个要约收购,而且目标公司的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该规定延迟要约收购。如果其他的一些有相关利益的人提出要求,州务卿也要召集听证会。因为目标公司管理人员在很多情况下都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目标公司的股份,于是他们便可以通过坚持要求举行听证会来延迟要约收购的开始。那么,此类规定实际上成了目标公司反收购的利器。在制定威廉姆斯法时,国会就已经认识到这种延迟会严重地阻碍要约收购,因此竭力避免此类规定。因此,最高法院同意上诉法院的观点,这些有关听证的条款违反了《威廉姆斯法》。
第三条,伊利诺伊州收购法允许该州州务卿裁定要约收购的实质公平。但是,威廉姆斯法及其立法过程表明国会希望投资者可以自由做出决定。参众两院的报告都表明该法律是用来保证相关信息公开,以便股东拥有公平的机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关于这一条,最高法院也同意上诉法院的观点,即此条款违反了威廉姆斯法。
“商业条款”也神圣
接下来的问题是,伊利诺伊州的收购法是否违反了联邦宪法的“商业条款”?
联邦宪法的“商业条款”规定“国会有权规制各州之间的贸易”。然而商业条款仅允许联邦间接规制跨州的贸易而非直接规制。伊利诺伊州收购法有两点违反了这些原则:首先,它会对跨州要约收购进行直接规制和阻挠;其次,该法律过于倾向地方利益,而对州际贸易增加了阻力。
各州历来有规制州内证券交易的惯例,各州制定的“蓝天法”【blue-sky laws】也有一定的权力对抗“商业条款”。
伊利诺伊州收购法在实质上不同于州的“蓝天法”,因为它直接规制了跨州交易,甚至可能是完全发生在伊利诺伊州之外的贸易。对一个上市公司证券的要约收购通常都是通过邮件或其他跨州交易的方法来同国内和国外的股东沟通的。证券收购和交易成交都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在本案中,作为收购方的MITE公司,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但在特拉华州注册;芝加哥铆钉是伊利诺伊州的上市公司,其股东遍布全国,其中有27%在伊利诺伊州。MITE向芝加哥铆钉的股东,包括在伊利诺伊州的股东提出要约,在传送过程中必然利用了州际交易方式。而一旦要约被股东接受,就会发生跨越州交易。这些交易本身就是州际贸易。然而伊利诺伊州收购法,不仅会阻止MITE与位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铆钉股东履行要约和进行跨州交易,而且会阻止其与非伊利诺伊州股东的交易。事实上,从这个法律的条文来说,即使芝加哥铆钉的股东当中没有一个是伊利诺伊州的居民,只要一项要约收购的目标公司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两个,伊利诺伊州收购法就要被适用: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或在伊利诺伊州注册成立;或至少在该州有10%的法定资本和超过股票面值的已付余额。这样一来,这个法律连那种一个伊利诺伊州股东都不会涉及的要约收购都可以管了。
因此,可???明显看出因为伊利诺伊州收购法意图直接规制和阻挠州际贸易,甚至包括完全属于该州以外的贸易。此外,如果伊利诺伊州强制进行这样的规制,其他州未必不会效仿。如此一来,要约收购产生的证券交易中的跨州交易将会被完全抑制。
伊利诺伊州收购法明显过于偏袒地方利益,不必要的妨碍了州际贸易。该法律的内容实际上是允许伊利诺伊州州务卿对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收购横加干预。股东被剥夺了溢价卖出其股份的权利。这阻碍了经济资源价值利用最大化的重新分配这样一个可以促进效率和竞争的过程。要约收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刺激目标公司管理人员认真履行其职责和义务,以维持公司的股票价值,从而实现股东的利益。但是对要约收购的过度抑制和对目标公司的过度保护却削弱了这种激励。
该法完全豁免了对自己股份的公司收购。但芝加哥铆钉可以用自己的股份进行竞争要约收购,而无需遵守伊利诺伊州收购法。这使得芝加哥铆钉的股东只能依靠联邦证券法的规定来保护自己,这又与该州宣称的保护投资者的立法原则相矛盾了。
最高法院同意上诉法院的观点,伊利诺伊州收购法对州际贸易强加了一个很大的负担,而州际贸易是比该法所谓的地方利益要重要的。因此根据“商业条款”,该法无效。最高法院维持上诉法院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