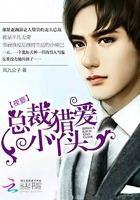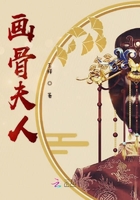曾几何时,我在想是不是葬天歌幼年时期遭遇了什么可怕,甚至近乎毁灭人性的事情,所以才会这样的阴晴不定,性子古怪?为了解了这个疑惑,我拿着两瓶酒准备去问葬天歌身边的小跟班北莫冷,但一想北莫冷还未落冠,葬天歌是禁止他喝酒的,于是就改拿了两盒他最爱的甜食——糯米糕,软软腻腻的,这点倒是挺符合他可爱的形象的。
最后结果是一无所获,不仅没得到一点消息,还被他佯装冷着一张脸讽刺了一顿,厚脸皮的抢了我的那两盒糯米糕,独自在那里露出虎牙的开心去了。
灰溜溜的从暗影阁出来,突然意识到他北莫冷虽然是个孩子,但也是葬天歌教导出来训练有素的杀手,这样的套近乎他自然是不买账的,也绝对不会向我透露一丁点我所需要的有用讯息。
一拍脑袋,于是这个疑问就成了至今未解的难题。
到底葬天歌童年遭遇了什么?
手捧着阿花的尸体,我又问了自己一遍:是什么让葬天歌变得如此古怪?他每次将我关进牢里,然后第二天就会放我出去,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连北莫冷也是这么认为的,有些人甚至会说我猫七看来是很得葬天歌的欢心的,即使冒犯了他,也只是关上一夜意思意思。其实,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夜是惊魂一夜。
遥记得上次他葬天歌是在草垛里放了一只五步蛇,当时幸好我留心的观察到了蛇拉下来的屎,觉得有所蹊跷,就没有贸然的躺进草垛里,而是小心翼翼的用长棍将草垛掀开,就看见一条五步蛇突然直起了身子,朝着我这里吐着信子。当时我是吓得一身的冷汗,暗想如果我不存点心眼的就这么坐下去,铁定是要被它咬的,第二天北莫冷再来开门送我出去时,见到的就只是一具尸体。
幸好我懂一点御蛇之术,以前在滁州也和一位捕蛇能手学了一点抓蛇的技巧,我就用棍子吸引蛇的视线,不停的拍打地面,将它逼退到墙角,再用棍子迅速的打向它的七寸,当蛇死透时,我才惊魂未定的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当第二天葬天歌见到活碰乱跳的我时,我从他的眼神里明显看见了惊讶的神色。
这次,他的做法却是在我上次就放在这里的柿饼里下毒。
上一次这个柿饼里是没有毒的,因为我本来带着五块,贪嘴吃了一块,那天晚上我是没事的,那么这毒就是我从地牢里出来以后放的。我想,当我出来时,葬天歌很不服气我为何没有被五步蛇咬死,就来到了这个牢里看见了五步蛇的尸体,也寻思着下一次我来到这里该用什么方式来害我,当他掀开草垛发现柿饼时,他突然来了灵感,就决定在柿饼里下了这毒。
嘴角爬上苦笑,看来我猫七福大命大啊!这次我又活蹦乱跳的从牢里出来了。只是不知道葬天歌下次会使出什么恶毒的招数。
我是不是该说,我很期待呢?
双手抱住双膝坐在地上,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些难过,尤其是这样夜深人静的时候,最让人莫名的去怀念过去。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万分后悔的,除了遇见葬天歌这件事。如果当初我没有一时心疼他,对他脸红心跳的喜欢上了,我也不可能会有这样悲惨的经历,如果我当初没去那个酒楼,我就不可能遇见他,如果当初……
现在是说什么都晚了。
我只求葬天歌哪天心情舒爽了,将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就这么放了,还我自由,让我继续在市井里做我不起眼的卖药女,从此永不相见,各安天命。
似乎是到了夜半时分,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本就单薄的衣物,因为从地牢高处窄小的窗横里吹来的风,更加的萧瑟寒冷。
就这样冻了一个晚上,当第二天北莫冷一脸不服气的为我开了地牢门时,他就见我脸颊有两陀诡异的红晕。
“哼,色猫七,这样红光满面,难不成你昨晚做了春*梦?”哆嗦着身子,抱着双臂从地牢里出来,幽幽的看他一眼,真是的,才是个十六七岁,毛都没长全的小屁孩思想居然这么不纯洁?说什么,做春*梦?你小子知道什么是春*梦了无痕吗?怎么可能这么明显的写在脸上?
“嗯,昨晚梦见了你..”幽幽的说一声,我昨晚梦见了你在和我抢糯米糕吃。
听闻,这小子果然立刻变了脸色,一脸愠怒的骂了一声:“流*氓!”显然他是想歪了。无奈的叹口气,拍他一下肩膀,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可以把人的话往这么邪恶的方向想呢?真是不纯洁!“我只是梦见你在和我抢糯米糕吃。你干嘛骂我流*氓?难不成你想歪了?想到那什么了?”
被我的话搪塞的抿住了唇,那张可爱的小脸上猛地泛起了两抹可疑的红晕。恼羞成怒的挥开我的手,立刻与我保持三步的距离,愠怒的脸配上那两抹红晕更像是这孩子因为被戳中了心事,在那里炸毛的狡辩,但说出来的话却不是那种意味:“色猫七,你果然很可恶!”细想想,这话是在表达他对我的厌恶之情,但换一个环境的话又有那种味道,比如我不小心戳中了他对我的心事,他有点生气我这人怎么可以这么直白的把他的心事公诸于世,于是他恼羞成怒的嗔我一句:“你果然很可恶!”其实这里面的成分多半是娇羞的意味。
呵呵,我好像确实蛮可恶的….
更有点……不要脸…..
“谢谢。”我由衷的感谢他的谬赞。
拖着有些惹了风寒的身子来到葬天歌的寝宫——天歌阙,就看见他一脸慵懒的侧卧在贵妃塌上笑看着我。他的身边居然站着一个面容陌生的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