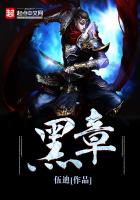“我对爱这个字的定义,很不幸,是最严酷的那一种。如果我爱一个人,就是为了他可以完全不顾自己,不要说付出生命,我可以为了他的幸福而离开他,只要他开心就好。”
欧阳昕躺回他的一侧,对我说:“我不会离开你,爱你就要跟你在一起。”
我不再说话,我们的爱情观似乎并不一致。那么,我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
在这样一个孤独寂寞的异乡,萧索寒冷的节日,人的感情本来就脆弱,我没有怪自己,并且打算好好待他,尽管我们之间或许还没有完全和谐。
第二天一早起来,昨晚落在外头的食物散了一地,我叹口气一件件收拾。
我屋里藏的美少年起身帮我一起收拾好,然后让我带他出去玩。
今天大部分地方都关门,我决定带他去轧马路。
我开一辆小小的GM的Sunfire,标准Girls car,外形漂亮,其他一无是处。我心仪奥迪TT多年,可惜一直狠不下心买。有次跟自芳提起,自芳说:
“你省钱干什么?”我惨兮兮哀嚎:“省钱给未来男朋友买车啊,谁知道是嫁鸡还是嫁狗啊。”
如今这个男朋友倒是不用我替他存钱,可是,上路不到三英里,已经被他骂了三百句,一会儿“你是蜗牛啊”,一会儿“你这技术也敢飙车”,弄得人不知所从措。终于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在等左转的时候心烦气躁,看错了红绿灯,踩住油门就往外冲。欧阳昕及时拉起我的手闸,救我一命之后瞪着我说:“你怎么开车的?想谋杀亲夫也不用把自己搭上吧。”
我气得当即下车:“换位子!”
他毫不客气地坐进驾驶座,起步之后,第一句话说“你这车的加速可真弱”,第二句话说“操作性也很差”。这两句我都忍了。可是他第三句说的是“这车的脾气也跟你一样坏”,于是他的第四句就变成“哎呀,你别跟我打架,很危险”。
中午路过一家Friendly,发现居然开着。虽然明知食物很难吃,可是我们昨晚都没有吃东西,我没怎么动倒是还好,他是把我当个瓷器侍候着,不敢轻不敢重的,我都替他累了,肯定需要食物补充一下,所以我立刻做了一回难得的东道主。
饭后我照例要吃冰激凌,为了表示友好和大方,我拿一只小勺子分了他几口,喂一勺我就心痛一下,可是他的笑容却比我杯中的冰激凌还甜。
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想起过来看我的?”
他说:“下雪了,看见地上的脚印就想你想得不行。想起来去年你踩着雪离去时,我的心一下子就空了,当时的感觉就跟那天医生告诉我妈妈得了癌症一样。”
我看他有些不高兴,赶紧握住他手:“我也很想你。”又接着转移话题,“你是怎么办的签证?换护照也要很早就打算才行啊,难道你早就计划好了?”
欧阳昕靠在椅背上笑笑:“那倒没有,我是临时决定。至于护照,我以前有个女友特别喜欢到处跑,为了陪她……”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脸色已经沉了下来。以前听他讲他的那些女友,只是觉得有趣,今日却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他即时停住话头,拿过勺子往我嘴里塞了一大勺冰激凌,脸上的笑容却是更灿烂了。
在美国的宽阔马路上驰骋之后,我们回到自己的小家,一起做了晚饭。美食美酒安顿停当,我说:
“昕昕,你知道昨天我为什么肯跟你了吗?”
他兴冲冲听我下文,我说:
“就是为了今天这顿晚饭。”
这可不是纯粹虚言,美式中餐已经吃得我快吐了,我的手艺当然也不错,但比起他还有很大差距。他笑着揽住我:“既然这样,先付过账再吃吧。”我大力摇头:“美食当前,你除非杀了我,否则是不可能把我拖走的。”
我开始暴饮暴食,他不停在旁边劝说:“明天还有明天还有。”
吃得脑满肠肥之后,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消食。欧阳昕过来抱住我:“今天早点睡觉好不好?”
我狐疑地看他,他也不隐瞒,直言道:“我想好好调教调教你的身体。”
我摇头:“不行,晚饭已经吃过了,从此两不相欠。”
他不说话,开始吻我。可是我正撑得坐都坐不下,我推开他:“说了不行。”他箍住我臂膀,继续吻我。我有些生气,叫了一声“昕昕”,他松手,我说:“你跟我相处,一定要学会一点——永远不要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
唉,跟小孩子在一起就是这点麻烦,凡事都要教给他,包括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已是约定俗成的事。
他看我一眼:“我让你那么不舒服吗?”我想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昨天晚上。我想说没有,可他已经走进卧室不再理我。
一个人坐在客厅,我打开手提电脑,习惯性地先查e—m a il。自从欧阳昕过来,我的e—m a il明显少了。
今天,却收到傅辉的信。
他很少给我写信。一定是大家都从自芳那里得了消息,知道我的工作合约到期,一起来凑热闹。
我点开,他讲话一如既往的简洁有力:
倾倾,圣诞快乐。
去年冬天,你曾问我喜不喜欢你,我没有回答。
今年冬天,我想告诉你,我没有回答,只是因为我不但喜欢你,还深深地爱着你。
我一直在追求心灵的极度自由,不肯束缚自己,更怕给不了所爱的人她想要的生活。可是,爱情是掩藏不了的。我爱你,愿意为你束缚自己,安顿下来。
我不打算再继续表演,想回家工作,闲暇时与你填词唱曲,好不好?
我将这封信看了两遍,从一个与文字为伍的写作者角度来看,每一句都很诱人。只可惜,信发错了人。倾倾已为人妇,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虽然不是个迂腐的人,骨子里却还有点传统。
我再看一遍,长长叹口气:老天爷跟我开了这么一个玩笑。如果没有昨晚的事情,也许一切都有余地,毕竟他一直是我梦幻中的情人,我也觉得自己还是爱他更多一些。可是现在,我只能叹口气,然后删掉信,并且努力把我对他的九十五分的感情往下压。
欧阳昕的声音由卧室传过来:“倾倾,我生你气了,你快来安慰我。”我“啪”地合上手提电脑,去安慰我该安慰的人。
第三天我们继续轧马路,欧阳昕坚持让我开车,说正好可以教教我,免得以后我自己撞死在马路牙子上。
美国的铲雪车动作很快,只是因为最近过节清理没那么及时,路上还偶尔有些残雪凝成的冰。我们在一条单车道的小高速上奔驰,我按着限速加五英里的时速开,后面一辆摩托车追上来,不停闪灯要超过去。
路面狭窄,我的副驾驶交代:“你开在正中间,不要让他,这里让车太危险。”我老老实实听话,一边抱怨道:“美国第一代摩托驾照持有者全部阵亡疆场,这玩意儿太危险了,开汽车是铁包肉,他这是肉包铁。”欧阳昕忽然回了一句:“跟我说这些没用,跟傅辉去说。”
转眼到了一处开阔地带,他前后看看,对我说:
“蜗牛往右边靠靠,他要是想过就可以过了。”这其实是违反交规的,但我的副驾驶也是个爱开快车的人,所以很理解后面那人的心情。我放缓车速,轧着右面的分界线开,后面的摩托车果然一越而过,那人到了前面还跟我挥挥手,车后面一圈彩灯挨个儿闪了一下。我笑笑,喊一句:“You re w elcome!”忽然就想,傅辉是不是也会有这样有趣的小心思,甚至,前面的那人会不会是他?
我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开得快了些。那人却更快,飞驰而去,瞬间没了踪影。
谁知开过一个转弯,又看见他了,原来前面有一辆比我还慢的车,而且毫不相让,在大道正中慢慢爬行。那骑手为了超车,紧紧逼在大车后面,车距显然过近。欧阳昕立刻说:“减速,离他们远点。”不用他说我也知道,赶紧松了油门,轻踩刹车。
正在这时,阳光一闪,忽然看见前方路面有一块成片的薄冰,紧接着便看见那摩托车在薄冰上斜飞而起,连车带人撞在前面车的车尾,然后那人像风筝一般落在路边。
所有一切都在一眨眼的功夫发生。在封闭的车厢中,加上自己发动机的声音,我们甚至连声响都不大听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已经那样被抛起落下。前面的车即刻刹车,我惊得没了动作,一直盯着那个骑手。几丝金发飘在风中,不是傅辉。欧阳昕叫了一声:“刹车!”同时伸手去拉手闸。
我这才反应过来,幸好脚本来就是踩在刹车上的,一脚踩到底。前面那车显然也是踩到底的,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往那辆倒地的重型摩托和大车的车尾撞过去。
我本能地想要避开他们,想让自己离他们远一些,所以往左打方向盘;眼角余光却看到欧阳昕因拉手闸而正前倾的身体,电光火石间不容我细想,我咬一咬牙又将方向盘往右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