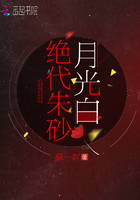过了五六天,她的伤势已好多了,韦从贤和令狐胜给她带了皇帝的一卷书信来。捧着信向长安所在的方向参拜后,再慢慢展开,那纸上半个字都没有,只简笔画了一群排成人字飞翔的大雁。分开来看,每只都定在不同动作,展翅欲飞,笔触甚美;合起来看就不太和谐,墨色也深一只、浅一只地凌乱无章法,不像是一气画成的,直看得她做声不得,呆立在地,脑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陛下……难不成是一天画一只?”但马上又狠狠捶自己一下:陛下会做这种奇怪无意义的事情吗?!
韦大人摸摸胡子轻咳两声:“这,小崔看得明白陛下是什么意思吗?”
她的声音低得像蚊子:“是,陛下是叫我回去。”任期未足就被召回,陛下这么不满我的表现?
韦大人看她表情就知道她想歪了,连忙解释:“陛下知道你中箭受伤,所以才让你回京的!”
崔捷望望他又望望令狐胜,你们的书信这么快就传了一个来回?
令狐胜说:“崔大人,本来我们想,这事还是由你来决定怎么禀奏陛下。不过,已经有人抢先一步地送信了。”
她疑惑不解:那是谁?
令狐胜笑笑,眼角似乎朝齐安平扫了扫,那呆头呆脑的小孩立刻局促不安地低头。
送走了两人,崔捷重新打量了一下齐安平,一脸憨厚,瘦瘦弱弱的,和那些高大健壮、虎背熊腰的龙武军士兵确实没法比。她正色问道:“小齐,你到底是什么人?”
“大人,我一向都在延英殿当差的呀。”齐安平冤屈地说,“只不过我的职务是保护陛下,每天都要藏着,所以你没见过我。这回陛下派我来保护你,可是我没做到。”
崔捷见他就快哭出来,连忙大度地说:“是我马快,你哪儿追得上。”
闭关了这许多天,她早已闷得发慌,而且不日就要离去,想法子遣走齐安平,自己偷偷溜了出来。经过几个小酒馆,在门口徘徊着探头望了望,因想起丁洛泉千叮万嘱要她戒酒,终究还是没有进去。
走了一会儿,忽然觉得有点不对,为何没有听到小孩子的读书声呢?退回到书塾去,里面静得鸦雀无声,院中两棵柳树间架起一根竹竿,一位老伯正往上面挂一串串熏肉,地上晒着许多腌鱼、菜干、药草之类的。进去打听,原来先生病了,暂时放假,那些东西都是学生父母送来的。
崔捷暗自点头,心里有个主意忽然明朗。
老伯听她说要找吃东西的地方,连忙举荐了本镇唯一出售“驴肉火烧”的小店。崔捷按他所说的寻过去,店面很小,稍嫌敝旧邋遢,人却多得要把桌子摆出路边了,从火旺炉子那边飘过来的炸酱香味更是令人食指大动。所谓“驴肉火烧”原来意指热烤饼夹热驴肉,崔捷心急,咬了一口,立刻烫得舌头打滚,又不好吐出来,只能闭眼用力咽下去,过后才猛然省起:丁大哥应该没有叫我戒驴肉吧?
大概因为这边热闹,有个卖唱的瞎眼琴师也在店旁占了位子,琴弦拨得叮叮咚咚的还算动听,就是咿咿呀呀口音太重,又和琴声和不到一处,听了好一会儿才辨出几句:“渺渺绿水,迢迢青山,楼台望尽,何日雁归来。”她心里顿时“咯噔”一声:原来他在唱《雁归来》!好端端一首曲子能唱歪到这种地步也真绝了。
再听一会儿,不知是否因为知道曲牌的关系,再加上那琴师颓唐褴褛的衣着,沧桑悲怆的神情,竟让人不经意间品出一丝缠绵幽怨、忧思离愁来。
若是陛下看见我一边吃烤驴肉一边听这曲子,不知道要怎么笑话我呢!但眼前又立即浮现临别那两天皇帝没有笑意的黑沉的脸。
她微微叹气,望望手中只剩一小块的渐凉的夹饼,又想:长安好像没有驴肉火烧,宫中会不会有呢?
走的时候,她向烤饼的厨子询问可有别的能带远路的小食,厨子推荐了一种棋子烧饼,她便挑了一些肉馅的送给琴师,一些素馅的包好带走。
这晚,书塾老先生程文通家中又有医馆大夫如约来访,只不过这位来头甚大,是京城仁安堂门下的洛大夫,派头也大,还有个清灵俊秀的药童跟着。
老先生不在授课,脸色亦放缓了,复原为慈详温和的老爷爷一个,只有两条入鬓长眉可隐约寻觅年轻时的英气。丁洛泉仔细为他把了脉,判断是“暑邪犯肺而致咳”,又问:“是否食蔗解咳?这可不对了,甘蔗对风寒所致的咳嗽比较有利,但先生不是啊。”
程文通边咳边应道:“大夫高明得很,昨日确实吃了甘蔗,老夫还奇怪这病怎么又忽然重了几分。”
丁洛泉对药童使个眼色,药童连忙走到旁边放着笔墨纸砚的桌子前,拿起松墨轻轻研磨。丁洛泉看他磨得差不多了,便说:“沙参、玉竹、麦冬各二两,桑叶、甘草……”
药童蘸好了笔想递给他,丁洛泉却笑着说:“不,你写。”然后便一股脑儿地继续报着药名分量。药童赶紧就着桌上的白纸快快地抄下。
写完了,丁洛泉也不怎么看便递给了老先生。程文通扫了一眼,大是纳罕,望着药童说:“京城里的人物果真如此不同,小小药童也练得一手好字?”
药童连忙逊谢,程文通说:“这字笔画圆净,收纵有度,又暗藏着秀骨奇峰。古人有云‘笔者心也,墨者意也,书者营也,力者通也’,非胸有沟壑者不能善书也。老夫实在不太相信……”他狐疑地上下打量着药童。丁洛泉只笑望着他,也不搭腔。
程文通眯着眼逐字再看一番:“确是好字,可惜有几个急回转笔、乍轻乍重的地方似乎力有滞挫,阁下莫非左肩有伤?”
丁洛泉和药童对望一眼,都叹服道:“老先生可真明察秋毫。”
药童重新施了一礼:“在下是宣抚副使崔捷,老先生往日都推辞不见官场中人,所以假扮了药童混进来。”
程文通回礼道:“大人垂临有何见教?”
崔捷也不兜圈,直接便问:“先生大概已听说了羊角山杀俘的事了吧?”
程文通背手踱了几步:“这事是薛涣昏聩了,杀了战俘又换不了烈士复生。这梁子是越结越大了。”
“不仅如此,听说战俘的尸首只草草安葬,而羊角山地势又比古亭和易州高,我有点担心谷中河水和这边的蘅渠相通……”
程文通醒悟,不禁用力捋了捋胡子:“这阵子我一直琢磨这件事,却漏了这一层,不能再慢慢想办法了。”
崔捷感觉他和自己的想法应该很接近,更加畅所欲言了:“老先生在本地很受敬重,门生广布,就连薛大人和县令大人都对你礼遇有加。我想,如果由你出面,说服大家,集合民间的力量把那些战俘好好埋葬了,也许最有效。但老先生可能要受不少非议和阻挠。”
程文通叹气:“我不怕受非议,只是说服和排除阻挠需要时间。”
崔捷从袖中取出一个装银子的小布袋放到桌上:“我几天后就要回京,不能出力,这些钱就请老先生买些松柏的树苗帮我种下,也当是我为这儿尽的最后一份心吧。”
程文通也不推搪,拱手说道:“大人想得周到,老夫必定竭尽所能。”
丁洛泉听说“回京”二字,有点错愕地望了望她。
程文通又问:“大人觉得沧州人会很快打过来报复吗?”
崔捷略沉吟了一下,答道:“之前的战事,田慈尘不是背部中了毒箭?老田手下有个迟大义,爱兵如子,民心所望,颇有将才,但也人如其名,义字当头,对老田忠心耿耿。要是老田死了,沧州必定以迟大义为首,那可就难对付了。最好老田一直缠绵病榻,死不了也好不了,那么迟大义不能上位,老田也没有心情过来袭扰……”
她脑中灵光一闪,忽然计上心来,眼睛也不由自主地瞟向丁洛泉,只见他微笑着颔首,似乎已猜到她心中所想,她却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程文通不知道他们已转了许多脑筋,呵呵笑着说:“崔大人分析得好。希望老天助我,让老田遇上个庸医。”
从程家出来,崔捷走了很长一段路都不言不语。丁洛泉便先打破沉默道:“你是不是想派我到沧州去当庸医?”
她眼中充满着忧虑:“太危险了,万一被他们发现,会把你当做奸细吊死。”
丁洛泉抬头望着天上半隐在云海中的弯月:“这确实是奸细的活儿啊!我能治病,又能下毒,又会易容,聪明敏捷,胆大心细,诡计多端,基本上是这一任务的最佳和唯一人选。”
崔捷很迟疑,对这玩笑话笑不出来。
“我只担心一件事,”他转头盯着她看,“你若还在古亭的话,我还能放得下心,但你却要回京了。”
“我,我伤口痊愈得不错,这是你说的。”
丁洛泉很轻地低语:“可我还担心些别的。”
崔捷低头:“我还没决定呢!”
丁洛泉笑了:“当然,我是朝廷派来的,有你下令我可以走得光明正大,可没你的命令我也照样能走。”
崔捷望了望他,继续低头向前走。
在医馆前告别,崔捷恳切地说:“丁大哥,这件事我们都再想想?”
“没时间了,老田痊愈了就不好玩了。”
崔捷心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劝不该劝,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丁洛泉轻轻推了她一下:“回去吧,别杵在这儿了。”
待她真的转身走了几步,他又一把牵住她的袖子。崔捷回头,他的大半张脸都隐在夜色中,看不清表情,声音也低得近于呢喃:“是皇帝把你召回去的?”
崔捷迟疑地答:“是啊。”
丁洛泉松了手,似乎“哦”了一声,片刻之后,崔捷见他没其他言语,只好再次道了告辞,转身回县衙去。
注:
[1]翰林院的风水问题来自于《阅微草堂笔记》:翰林院堂不启中门,云启则掌院不利。癸巳开四库全书馆,质郡王临视,司事者启之,俄而掌院刘文正公,觉罗奉公相继逝。又门前沙堤中,有土凝结成丸,倘或误碎必损翰林。癸未雨水冲激露其一,为儿童掷裂,吴云岩前辈旋殁……天高地远,鬼神茫昧,似与人无预,而有时其应如响,殚人之智力,不能与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