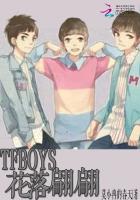到达纽约的那个下午,天上飘着点小雨,林晰的房子还是像几个月之前一样整洁。客厅里的窗帘没有拉,灰暗的日光照进来,窗玻璃上满是雨滴,外面是湿漉漉的街景,一副忧愁冰冷的样子。我走进去,打开暖气,把衣服从行李袋里拿出来扔在沙发上,鞋子放在门口,毛巾牙刷在浴室里就位。觉得自己就像是一阵捣乱的旋风,把房间弄得乱糟糟的,才有一点温暖的意味。在屋里转了一圈,我的偷窥癖又犯了,开始检视他的衣橱。事实证明,我对他的想象至少还有一部分是对的,他终究还是个爱漂亮的人,而且他的衣橱里果然是普拉达居多。喜欢意大利牌子的人和喜欢法国牌子的人总是截然不同,说不清是哪里不一样,不过如果你身边恰好两种人都有,你一定会有体会,他们就像爱唱歌的和爱跳舞的人一样不同。衣橱的下层都是鞋盒,此人鞋真多。每一双都刷得很干净,收在无纺布袋子里,装进黑色、白色,或者古铜色的鞋盒,码放得整整齐齐。最里面的角落里单独摆着一个亚银色马口铁的方盒子,也有装鞋的盒子那么大,不知道装的是什么,散发着一股秘密的味道。
我二话不说就拿出来,坐在地上,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照片,五寸到十寸的都有,还有一长条两寸的小照片。粗粗看了一遍,上面的人竟然全都是林晰自己。我吐吐舌头想,这家伙还真是自恋到家了。再仔细看看却又不像是自拍的,几乎都不是故意摆好姿势照的,有他睡着的样子,有读书的,有拿着照相机的,有的甚至就是远远一个侧面。其中有一张七寸照片,画面上是他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从一面茶色镜子前走过,镜子里映出一个女人的影子,一部黑色照相机挡住面孔,我认识那头发和打扮,是朱子悦。她那时一定非常喜欢他,我心里说。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她喜欢他到沉迷的地步。而他也在分手之后保留了这些照片,放在衣橱的角落里,是不是同时也在心中某个角落藏了些什么东西?我想地出了神,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妒嫉,反而被他们过往的爱情感染。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我尝试从一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林晰--朱子悦展现给我看的角度。我第一次撇开依赖,带着一点欲望,思念他。那天晚上,夜逐渐深沉,我关上灯,拉开窗帘。
外面雨早已经停了,但仍旧是个阴天,没有月光,只有一点惨淡的路灯的光线透进来。我躺在床上,怀抱着一件他的毛衣,寻找着依稀的熟悉的味道,慢慢睡去。接下去的几天都是在逛街血拼中度过的。洛拉和其他几个相熟的姑娘正忙着争取在时装周上露一小脸儿。我很少约得到人一起吃饭,约不到就一个人吃,然后独自在街上闲逛,给自己买衣服鞋子,为每个认识的人买新年礼物。给林晰买的是一瓶男用的“雅弦”香水,用深紫色的纸包起来,绑上白色缎带,看起来非常美。不过,说实话,那味道闻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他,更像是一部分的我,再加上一部分朦昧的回忆。每天夜里,我都抱着他的衣服睡觉,起来之后就套在睡裙外面,穿着它吃早饭,看电视,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这样一直到十二月三十号的早晨,天还没亮,床头的电话响了,我迷迷糊糊地接起来说了声哈罗。“你真的在啊,”林晰在电话那头说,“我就是打打看。”我觉得他这话说得傻傻的,却很讨喜,嘴上还是没好气地问他:“知道现在几点吗?”“七点多了吧。”他回答。“六点,笨蛋。”“那我挂了,你再睡会儿。
”“不要不要,都已经醒了。”我坐起来,靠在枕头上,“日本女人怎么样啊?迪克森大叔很羡慕啊,说你肯定天天在那里风流。”他笑起来:“你去跟他说,东方文华酒店三零一六房间彻夜回响‘呀咩代呀咩代’。”我不说话,觉得一点也不好笑。他也不笑了,问我:“笨蛋你在干吗?”“笨蛋抱着你那件老鼠灰的毛衣刚刚睡醒。”“为什么抱那个,要不要给你买个娃娃回来?”“因为想你了,笨蛋。”轮到他不说话了。“你见到朱子悦了?”我又问他。“见了。”“她怎么样?还是‘既丑又美’?”“对,还是‘既丑又美’。”“还是‘看不出年纪’?”“嗯,‘看不出年纪’。”“还是‘难以抗拒’?”“不那么‘难以抗拒’了。”“为什么?”“因为我爱上一个人,”他慢慢地回答,“而且她今天说她想我了,我特别高兴。”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只听得到微弱的电流声和呼吸的声音。最后,还是我先打破沉默,开口说:“笨蛋,你快点回来吧。”他说:“好,马上回来。”然后就挂断了电话。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马上”,真的是“马上”。
他在当地时间晚上九点钟到达机场,然后一整夜等待机票改签。不过,在他飞过一万四千公里回到我身边的时候,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上午,我照旧懒洋洋地在床上度过。吃过午饭,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也是在迪克森的摄影工作室里认识的,纽约一间时尚杂志社的实习生。他问我晚上有什么节目吗?我说就打算租个碟看电影然后睡觉。嘲笑了我一通之后,他告诉我,晚上在长岛一栋大房子里有个派对,如果我想去他可以带我进去,还夸张地补充:“所有人都会在那里,但是没人知道派对的主人是谁。”我笑着问他:“是不是盖滋比?”“盖滋比?谁?”很明显,他没听懂我的笑话,反过来又问我,“你到底去不去啊?”我想起前一天刚刚买下的一件宝蓝色小礼服,抹胸,细腰,下面是及膝的蓬松裙摆,非常好看,不穿一下实在可惜,于是就说:“好啊,我去。”下午又出去买了一双相配的鞋子。
到了晚上快出发的时候,我穿上裙子,却发觉怎么也绑不好后腰的蝴蝶结,只好照着镜子反手绑了一个歪歪的,外面罩了个斗篷式的黑色羊毛外套,然后开了差不多两小时的车去那所传说中的长岛海边大宅。到了地方发觉排场果然很大,虽然时间尚早,场面未暖,但是客厅、室内游泳池、温室里的人都已经不算少了。门廊和露台上也有暖气,有酒吧有乐队有舞池,据说午夜的时候还要放焰火。勾搭我来的那个人带我进了门就不见了踪影。我谁也不认识,于是就怀着单纯的混一顿吃喝的心态,检视了一下餐台。正要开吃,却发觉有人在拉我的裙子。回头一看是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三十五到四十岁的样子,个子很高,穿着无尾礼服却敞着衬衣领口没有打领结。他看看我,深蓝色的眼睛似曾相识,说:“无论如何,我都不相信你真的未成年。”我想起来他是谁了。“我认识你吗?”我装蒜。时过境迁,我再也不想跟其他人有什么瓜葛了。“不,你不认识我。”他回答得倒很干脆,“我可以肯定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一边说一边解开我背后的歪结,在我提出抗议之前又帮我打好了一个很正的蝴蝶结。“打得真好。
”我回头看一眼落地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又问他,“你怎么不给自己系个领结?”他微微笑了笑回答:“打结这种事情,男人女人互相做才有趣。”我正想着要怎么回答这句带着点调情意味的话,手机响了。接起来,是林晰的声音:“我到机场了,还要拿行李,大概还要一个多钟头到家。你在哪里?”我惊喜地几乎跳起来:“我在外面,我马上回家。”挂掉电话,就往外跑。那个男人伸手拉住我的手腕问我:“那个罗宾汉?”“我的情人。”我纠正他,朝他眨了下眼睛,甩开他的手满心欢喜地跑出去。因为心急,一路上我车开得很快。到了半路,因为超速被警察叔叔拦下来。我装可怜,深情地说:“我赶着回去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吻我的男朋友,求求你饶了我吧。”结果还真的开恩把我给放了。到了公寓楼下,抬头看到五楼那个房间的灯已经开了,那浅黄色的温暖的灯光,差一点让我落泪。我一路跑进去,电梯在六楼停了很久不下来,我等不及就爬楼梯了,气喘吁吁地到了门口,又有点怕怕的,不敢敲门。拿钥匙的时候,发出轻轻的金属碰撞的声音,他一定听到了。门开了,他一下把我拉进去,关上门,在我开口说话之前就深深地吻我。
我感到他的嘴唇和手在微微颤抖,小声问他:“你怎么了?”“我紧张。”他回答。“怎么会?”我不相信。“我也不知道。”他嗫嚅着说,“可能是因为认识太久了。”那天晚上,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在他的床上做爱。第一次他任由窗帘大开着,月光烂漫地照进来。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没错,他确实是个过来人,一个特别的“情人”。他的手和嘴唇温柔但坚定,月光一样轻抚过我身上每一寸皮肤,同时也像月光笼罩着整个房间一样摄住了我。他诱惑我,引导我,深情里带着点冶艳,在我颤抖退缩避让的时候,又让我无处可逃。
旧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两个都饿着肚子什么也没吃。所以新世纪的那个黎明,喝掉冰箱里最后一点牛奶之后,我们又跑出去觅食。外面冷得出奇,偶尔有辆黄色出租车载着几个狂欢之后的男女疾驰而过,一伙喝醉酒的人走过我们身边,其中的一个大声对我们说:“新千年快乐!”已经没有在营业的地方了,我们只能在街边一间二十四小时自助银行里的自动售货机上买了饼干和巧克力。也就是在那间满是涂鸦的玻璃房里,我们又一次拥抱在一起,吻得很忘情,榛仁巧克力和玉米糖浆的味道在两个人舌尖上交融,是种难以言喻的甜蜜和浓郁。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时不时地说起,如果可能,想找那间银行拷贝那段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