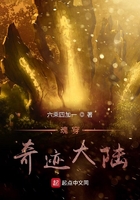从雩娄行到六安,三人只花了一天时间,就走了一半的路程,抵达小磨盘山。小磨盘山夹在决水(按:现史河)与湄水(按:现淠河)之间,等翻过山,度过湄水,便可到寿县,即属六安境。
李穆然本以为入了晋地,庾家便该派人来接庾渊,没想到一直拖到六安,还是不见半个人影。他直面问庾渊,庾渊仍以一句“一个人自在惯了”来推脱。他既然不愿如实相告,李穆然也就不再追问,想着明日到了六安,总算能把他撇开,也算去了一桩事情,便乐得少些心,登时甚觉轻松。
几人在山中安顿好后,临去各自马车上休息前,庾渊忽地开口道:“蛇公子也许就在附近。为防万一,两位兄弟还是把避毒的药先服下,以免夜里突然遭袭。”
那药冬儿早已辨过,的确是避毒圣药,听他提醒,两人也就依言吃了。冬儿见庾渊今日忽地一反常态,满脸紧张,以为他是在担忧过了六安,之后无人护卫。她心肠甚软,想着这些天来也多蒙他照顾,便对李穆然悄言道:“不如,我们把易容改装的方法教给他,他也能安全些。”
李穆然却断然拒绝,道:“那怎么行。你教会了他,他就要疑心你的身份了。更何况过了六安,离建康已经近得很,他总不能易容一辈子。建康是他的天下,晋国不是没有高手,还怕区区一个蛇公子么?”
冬儿看他态度坚决,知此事不能再提,便瘪着嘴瞪他一眼,自回马车去了。李穆然见她生了气,不觉暗暗苦笑。冬儿始终太过心善,又容易轻信,自己总要想个法子,让她改改才好。
三人奔波一整天,都很疲累,倒在车中合上眼,便都睡沉了过去。
午夜山中,一片静谧。偶有兽声在密林中响起,窸窸窣窣一阵过后,便又静了下来。
“扑棱棱”
猝然间,一道黑影划破长空,飞到马车的上空,盘旋一阵,又展翅飞离。
“不能落?”一只手抚摸着黑狐蝠的翅膀。那狐蝠觉得很舒服,眯起了一双细长如线的眼睛,喉间“咕噜咕噜”地叫着,以为主人是要喂食了,却觉头一阵剧痛。
看着被捏死的狐蝠,蛇公子脸色一沉:“没用的东西。”他取出手帕,擦干净右手拇指和食指上的猩血,随后,套上了鹿皮手套。
“看来是桃姬给的药没错那么,这一次是真的了。”蛇公子回头看着身后那个浑身上下抖作一团的鲜卑男子,极妖气地笑了笑,“放心,你的身份尊贵,我不会杀你。多谢你告诉我庾渊在哪儿。我拿了他的头,就来放你。”他拍了拍那人的脸。鹿皮手套划过面颊,那感觉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想着蛇公子浑身上下都是毒,那男子吓得双腿抖如筛糠,尿意袭来,登时喷薄而出。
“诶,真不乖。”蛇公子捏着自己的鼻子,笑看了那人一眼,又道,“你说,怎么杀他好呢?”
晚风猎猎,卷起他身上白如新雪般的大氅,让他的背后仿佛忽地长出了纯白的翅膀一般。他往山上缓缓走去,身影飘忽,如谪仙,却也如恶魔。他口中喃喃,那名被捆成一团的鲜卑男子在后却听得清清楚楚:“上次那个是淹死的,还有一个是活埋的,毒死他么?实在太无趣”
睡到半夜时,李穆然忽觉身上很热。
似乎是梦到了三伏时沙场练兵,太阳很大,晒得人口干舌燥,整个人都要被晒焦了。
可是鼻子好像真的闻到了焦味。李穆然迷迷糊糊的,忽然醒悟过来这不是梦,整个人一下子坐了起来。他揉了揉眼睛,几乎以为天亮了,可是看着车外的亮光忽明忽灭,他忽地大惊失色:“失火了!”
看看犹自沉睡的冬儿,他忙推醒了她,道:“你先在车里躲着,我出去看看!”言罢,他不及多嘱咐什么,一提无名剑,已纵出了车厢。
冬儿被他叫醒,初时还有些茫然,不知出了什么事,直到他一掀车帘,一股炽风迎面卷来,她才猛地惊醒。她还没说什么,李穆然已闪出车厢。旋即,就听李穆然怒喝了一声,似乎已经和什么人打在了一起。
冬儿满心担忧,忙钻出车厢往四下看去。给三人拉车的马早已经毙命,马的口鼻处流的都是黑血,应该是中毒而致。四周都是火,烧得仿佛一切都变了形,热浪滚滚中,李穆然和一个白衣男子打在一起,那人身法轻巧,但在李穆然狂风迅雷般的攻势下,占不了什么上风。
他们打的地方,隔在一排火墙之后,冬儿的轻功不如李穆然,无法一跃而过。她有些着急,想找皮毡蒙着自己冲过去,可是一回头,见庾渊的车在后边,车的尾部几乎都烧没了,整个车上都已经透出了红光。
“糟了,他人没有出来,难道不知道着火了么?”冬儿被吓得几乎惊叫起来。一想到庾渊可能已经被烧死,就觉甚是过意不去,她回头见李穆然仍是稳稳地占着对方上风,心中一定,忙飞身赶到庾渊的马车旁,手中长剑挑起车帘,向内看去。
她长剑一挑,一条火龙自车厢内扑面而来,若不是她闪避得快,几乎被火烧到脸。冬儿手一捂嘴,几乎落下眼泪:这般大的火,那位庾公子恐怕真的被烧死了。烈焰之中,大抵连全尸也留不下。想不到就差这么几天他就能回家了,却功亏一篑,惨死在这荒山之中。
想起他最后一句话还是在叮嘱自己和李穆然服下避毒药,冬儿更觉难过。只觉得是自己两人没有尽到职责,这一路上自己还对他颇多猜测
她正自难过,忽觉一人从身后拉住自己胳膊。她此时心中又悔又怕,惊惧交加,不及思索,左手一翻一推,右手顺势一剑斩去,正是一式“拨云见日”那人一矮身,脚下一错,用了一式“执干戚舞”勉强躲过,却被她一剑斩着发髻,头发登时散落了下来。这两式是平日里她与李穆然在谷中互相喂招练熟了的,若非对方对她的武功熟悉,断断不能躲得这般容易。
冬儿看清了面前人,轻吁口气,收回了剑。
李穆然满面被火熏得漆黑,面颊上粘的假胡子几乎全被烧光,身上的衣服更被树枝划得破破烂烂的,露出的胳膊上,满是划痕。冬儿瞧得甚觉心痛,不过看到他安然无恙,她心中也是大定,忙扑入他怀中,紧拥着他哭道:“那位庾公子被烧死了,我很害怕。”她这时再装不来平常的男子声音,回复了本声。四面噼噼啵啵的火烧声中,她的声音显得很柔弱,极是惹人怜惜。
李穆然一愣,而后回手搂紧了她,问道:“庾渊真的死了?”他的声音依旧是嘶哑的。
冬儿以为他是被火熏坏了嗓子,更增了几分心疼,便道:“你先别多说话。我我没来得及叫庾公子,来他车上看时,整个车都烧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他怕是尸骨无存了。”说到最后几字,她又落了几滴泪。
李穆然却显得无动于衷,他脸上表情依旧,声音极平淡:“别难过。林子里火这么大,我们先出去再说。蛇公子已经被我杀了,外边很安全。”语罢,他挽起冬儿,走到另一驾马车上,翻出了一大张毛毡,道:“披着,这应该够用。”
冬儿此刻早已六神无主,又习惯他说什么便是什么,就依言随他裹在一张毛毡之中。这时风刮得已经没有方才那般大,火势似乎也小了些,两人到了另一边的火墙缘,冬儿用手挡着脸,只觉面颊被烧得生疼。她见那火墙已经矮了半截,露出后边烧得焦黑的土壤,便一松毛毡,道:“我能跳过去了,不用毛毡了。”
岂料李穆然却摇头道:“不行。我我方才和蛇公子打斗的时候被他伤了腿,怕是纵不过去。”
“你被他伤了?”冬儿大惊,忙道,“怎么不早说我架着你走吧。”她把他的手放在肩头,却没想到李穆然微微一笑,道:“不用,你扶着我走就好。你那边也拉紧了毛毡子,小心别被烧到。”他一边说着,手一垂,又抱上了她的腰,手上似乎还用些力气掐了一把。
冬儿微微一愕,她和李穆然虽然有终身之约,但一路上都是以礼相待,就算同在车厢之中,他也不敢做这等举措,难不成这一场大火,烧糊涂了么?她脸上一烫,不过想到逃离火海最为要紧,便没说什么,将毛毡子兜头兜脸地一遮,轻喝道:“走!”便带着李穆然向火墙冲去。
短短几步路,两人却被烧得连呼吸也不敢。直到冲出了火墙,二人又连跑了上百步,才觉脚下不再滚烫,停了下来。毛毡子上还零星闪着火星,冬儿忙把它抛在地上,又在上边踩了几十遍,确信没有火了,方蹲坐在了地上,轻喘着气。
李穆然则仰面躺在一边树下,“呼呼”地喘着粗气,二人回头向山上望去,只见那大火还在继续烧着,山顶一片火红,离得这么远,还能觉出火势熊熊,热浪滔天。
李穆然叹了口气,道:“幸亏蛇公子还没疯到要把整座山都烧掉,咱们才能逃脱性命。”他哑着嗓子,说的是鲜卑语,冬儿听得直皱眉头。两人在冬水谷中,向来说的都是汉话,如今庾渊既然不在,他还说鲜卑语干什么,到了这时还怕泄露身份么?
她心中有着疑窦,转头看向李穆然,只见树荫遮挡着月光和火光,他的脸又被火烟熏得一片漆黑,在夜里实在瞧不清楚。隐约着,她觉得李穆然的手轻轻拂到自己的脸旁,他嘶哑的声音重又响起,却带着几分魅惑:“阿冬妹子,这些天你扮男装实在辛苦。我都快记不得你长什么样子了。”
他的手近在咫尺,他的人更是与冬儿呼吸可闻,可是在这一刹那间,冬儿却觉得他甚是陌生。
阿冬妹子?这是什么称呼?她的穆然从不会这么喊她。
这个穆然是假的!
冬儿大惊,可是还不及多想,遥遥的山林中,已传来了李穆然的声音:“兄弟,你在哪儿?”那个声音虽然仍是嘶哑的,说的也仍然是鲜卑语,但其中的担心和牵挂,却是别人怎么学也学不来的。
“你!”冬儿忙挥掌向前打去,可是对方的手就在她的脸侧,她只觉“太阳穴”被对方点中,继而整个人已是人事不省。
庾渊看着倒在地上的冬儿,不禁莞尔:“真没想到你竟是个女子,鲜于兄这些天来,真是艳福不浅。哎,这几****对我也算不错,如今可别怪我骗你。我还指着你逃命呢!”边说着,他边打横抱起了冬儿,方向山下迈了十来步,就听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不想死,就放了她!”
庾渊缓缓转过身去,看着身后那男子。他的样子比自己好不到哪去,同样是被火熏得满脸漆黑,同样是衣衫被划得千丝万缕。可是他虽然刚经过一场大战,又在山中跑上跑下,但他的呼吸依旧很平缓。他的手很稳,手中的剑也很稳,剑尖不颤,隐隐透着剑芒,直着自己的眉睫。
不过,两人之间,毕竟还隔着四五步的距离。
李穆然经过与蛇公子的一场恶战,实则已到了强弩之末,可是看冬儿被庾渊挟持,也不知哪里就凭空生出了许多力气,让他只想将眼前这人碎尸万段。
他不信蛇公子会来得这么巧。不知道姓庾的是用什么法子把他激来,更让他错认自己为庾渊,一言不发,一上来就用杀手。幸而自己本来武功便与蛇公子不相伯仲,之后这一年更是在快、准二字上苦下功夫,弃掉了原本武功之中花哨取巧之处,全凭以快打快,以狠斗险,方将蛇公子斩杀。此刻蛇公子恐怕早已被他自己放的那把火烧得一干二净。
他斗了上百招才取胜,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蛇公子在他后背上印了两掌,他掌力不大,却透着阴毒,此刻自己背上又麻又痒,若不是口中含着那颗避毒药,恐怕剧毒早已入体。
可以说,他是拼死才杀了蛇公子,这原不在他的计划之中。他恨庾渊利用自己,更恨斗心机输了他一筹,正想找他算账,没想到竟见他挟持了冬儿。
李穆然恨得牙痒,真想一剑劈过去,斩了庾渊,可是冬儿在他手中,他手上还拿着明晃晃一把匕首,架在她脖子上。
庾渊虽然力气不如李穆然,但毕竟也练过几年武术,兼且冬儿身子不重,故而一手抱着人,一手拿着刀子,还难不倒他。他微微向后撤着步子,脸上勉强保持着笑意:“鲜于兄,你别追得太紧。兄弟我脚下功夫不行,要是不幸跌倒了,手上的刀子可是不长眼睛的。”
“你怎么如此卑鄙!”李穆然怒骂道,“我们俩一路护送你至此,现如今还帮你杀了蛇公子,你你还是人么?”
庾渊笑道:“小声些。鲜于兄,难得见你也会骂人,这只能说明你到现在也已经无计可施了吧。兄弟既然是生意人,自然知道守诺的紧要。只要等到明天,兄弟能安安稳稳地离开湄水,尊夫人自当完璧归赵。”
“夫人?”李穆然一愕,但转念已明白庾渊多半已知道冬儿是女子,他瞧冬儿和自己同乘一车,在驿站也是同宿,自然有此联想。他勉强稳住心绪,道:“你现在就把她还我,我保你安全离开湄水,此后也不找你的麻烦。你若不信,我可以发毒誓。”
庾渊道:“鲜于兄,我是个守诺的人,但并不是个傻子。如今凡事都依我说的算,你还是省省心吧。毒誓什么的,我一天随口能发十来个,也没见过有当真的。”语罢,他忽然喝了一声:“止步!再往前我不客气了!”
李穆然被他这一喝,登时身子如同钉在了山上,再也不敢迈出半步。庾渊点头笑道:“看来鲜于兄对夫人的确是用情至深,如此我就更放心了。你今天就呆在这儿吧,一步也别往前挪了。等明天辰时,我们约在湄水的西淠渡口见。告辞!”语罢,他再也忍不住,不由朗声大笑起来。他拖着冬儿,一步一挪、踉踉跄跄地下了山,再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