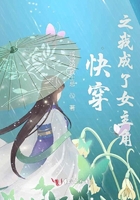然而李穆然马战这时可称得上罕逢敌手,郝贝和他擦身而过,他岂容她这么轻而易举地离去,猿臂一探,已将她拦腰抱住。青龙驹的力量远比郝贝坐骑大,二马错鞍,褐毛马登时再动不了步子,老老实实地立在了原地。
郝贝被他这一抱,满腔的委屈登时全都涌上心头,只觉鼻尖一酸,眼泪已滚滚而落。她还想再打他,可是想着他方才已受了一鞭,也不知还痛不痛,说什么也再下不去手了。
“冤家,你真是我这辈子的冤家了!”郝贝轻叹了口气,忽地伏在李穆然怀中大哭起来。哭到伤心处,她银牙一紧,在李穆然的左肩头狠狠咬了一口。
因为刚从驿站出来,除了白狐大氅外,李穆然并没有穿着平日的将军衣服,明光甲也留在了冬儿处,身上只穿了一件常服。虽因天寒地冻,常服很厚,可还是禁不住郝贝这用尽全身力气的一咬。
李穆然疼得身子一颤,却没有反抗,也没有放手,反而把郝贝抱得更紧了些,而后臂上用力,把她从褐毛马背上抱起,放到了青龙驹背上。
两人离得更近,郝贝这才觉得口中忽地有了血腥味,忙松口看去,却见月白色的衣衫上,已冒出了血来。
“哎呀。”她痛呼一声,扒着李穆然的领口往里看去,却见肩上有深深的两行齿印,此刻鲜血流出,赤红一片。
郝贝心中一急,眼泪又流了下来:“你是傻子么?怎么不躲,也不说话?”
李穆然微微一笑,柔声问道:“消气了没?”
郝贝听他这么问,心中又难过起来,狠狠地别过了头去,怒哼一声,道:“那几个小兵说将军怎么会有两位夫人,你倒是说说,那位夫人是谁?”
李穆然讪讪一笑,把马带着离城门远了些,方道:“是冬儿。”
郝贝小鹿般的眼睛猛地瞪大了起来,她怔了许久,忽地惨笑一声,道:“我还是争不过她。”话声未落,两行泪珠已如断线的珍珠般滑落面颊。
李穆然轻轻擦去她的眼泪,道:“阿贝,你不用争什么,你还是我妻子啊。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他欲要亲她脸颊,却被郝贝用力推开。
郝贝一擦眼泪,就要跳下马背,然而李穆然双臂都拦在她胁下,她左挣右挣,也离不开马背。倒是青龙驹不耐烦了起来,打了一声鼻息,前蹄猛地一抬,马身忽地立了起来。
李穆然忙拽紧了缰绳往前俯身,郝贝本就在他身前,此刻混无着力处,倒被他抱得更紧了些。她本就是急脾气,这时又不禁哭了起来,骂道:“你欺负我还不够,连这畜生也欺负我!”手中马鞭一扬,就要往青龙驹身上抽去。
李穆然忙一按她手,劝道:“这马刚驯服不久的,你这一抽,一会儿发起性来,咱俩都要被摔下去了!”
郝贝道:“摔下去就摔下去,就算我摔死了,你难道会难过么?”
李穆然笑道:“说什么傻话呢?”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稳住了马。只是这一番折腾后,肩膀上的伤口血流不止,衣服已经被血染红了一大片。
郝贝看着那片血,心中更是难过,倒也不敢再使性子,只问道:“我不明白。她不是嫁给庾渊了么?怎么又嫁给你了?你之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吗?”
提起庾渊来,李穆然又不由叹了一声,道:“此事说来话长了,就从咱俩金寨分开之后说起吧。”
青龙驹在月光下悠闲地踱着步子,李穆然柔声将往事跟郝贝娓娓道来。
郝贝这时心绪已平静许多,她毕竟从小在慕容山家中长大,见惯了男子三妻四妾,更何况数月前因为慕容垂属意将慕容月指给李穆然,慕容山夫妇也找她谈了许久,她早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时见李穆然和冬儿在一起,心中虽然一抽一抽地疼,但也自知木已成舟,自己是没什么法子拦着了。
她听李穆然说起金寨之后,荆州城救庾渊;又听他说大别山中慕容垂设计与青州军一起灭了镇军;还听他说淝水之畔以一万骑兵救援苻坚大军。
李穆然虽然不怎么爱说话,但口才也算是出众的,这些故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这时一一讲起,直让郝贝觉得身临其境,随他同悲同喜,也同惊同惧。
听他说到慕容烈之死,郝贝又难过了起来。她早知道慕容烈的死讯,可是当听到“玉花骢的尸体后,慕容烈头颅已无,手上仍握刀枪”时,仍心中一酸,潸然泪下。
而这之后,当听李穆然说道他为了夺回慕容烈的首级,被晋军追杀,虽见他安然无恙就在眼前,郝贝还是不由握紧了他的手,指节都发了白。
“后来多亏你哥哥率兵救了我。”李穆然微笑着看着郝贝。怕她多心,他特意没提慕容月的事,只提了一句万里追风驹跑伤了腿。
郝贝听到郝南的“壮举”,脸上才显出一丝笑意:“哥哥如今率军围着邯郸呢,你们过不久也能见面了。他很想念你呢!老是说没你在,打仗也没意思,都没人能比得过他!我说他是吹牛皮,他还不服!”
李穆然笑道:“那你呢,你想不想我?”
郝贝脸上一红,道:“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早点儿过来呢。垂王叔也真是的,干嘛叫你去长安!一听说你快打到晋城,我早早地就跑了过来。你个死没良心的,还这么问我?”她眼珠子一转,又道:“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正事上呢!你今天不说明白了,我才不饶你!”
李穆然神色一凛,接下来便说到苻坚属下的百人队攻到了宋家镇,庾渊为了救冬儿被乱箭射死,而他则阴差阳错之下,被冬儿误会,认成了凶手。
听李穆然讲起冬儿冤枉他,郝贝脑袋一热,不由怒道:“她你待她那么好,她还冤枉你!你谷中那些师父们也真是的,都不帮你说话么!”
见郝贝忽地义愤填膺起来,李穆然不由扑哧一笑,话锋一转,便转到了这之后如何带着抚军在长安城围打转,对右卫军布疑阵,与慕容泓攻下潼关,帮着慕容冲杀掉慕容泓夺得兵权,最终攻下长安。说这些的时候,自然隐去了慕容月不提,而郝贝也并没有起疑心。
听他不带喘气地说了这么一长串,郝贝的目光也变得柔和了许多,看着李穆然的眼神,又恢复了从前那般:爱慕骄傲,兼且有之。
而后,李穆然便讲到了冬儿为了不出卖他和谷中师父,被苻登严刑拷打,已至遍体鳞伤,甚至双脚脚筋都被挑断。
郝贝自幼习武,对于医术也学过一些,自然明白双脚脚筋都被挑断,对于一个习武之人意味着什么。她倒吸了一口寒气,心中对冬儿已起了一丝敬佩,以前一直以为那是个娇柔不胜的女子,没想到该坚强的时候,也能有此心性。
这之后,又听李穆然说道和慕容冲反目为仇,所幸拿到了药帮冬儿成功治好了脚伤,她才若有若无地轻吁了口气。
李穆然看她神色好了许多,便笑问道:“之前听说你在王上军中帮着练兵。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
听他提起这件事,郝贝得意起来,笑道:“不只练兵呢!如今我和嫂子还有我师父建了一支女军,我还是副统领呢!”随后,她像是想起了一件大事,忽地眼中一亮,又道,“你你那位冬儿她不是学过兵法么?之前我跟她比过武,看她武功也马马虎虎过得去。你叫她来帮我,怎么样?”
李穆然哑然失笑,摇了摇头:“等以后吧。冬儿她她如今身怀有孕。”他知道这是郝贝心中最重的伤,故而一直没说,但到这会儿却瞒不下去了。
“哦。”郝贝一个失神,随后强笑了两声,低声自嘲道,“你瞧,我倒忘了这件事了。也难怪就连王叔他们,也觉得你娶我娶错了呢。现在全军中都在说,说我和我师父一样,是下不了蛋的母鸡,什么用都没有。”
李穆然忙把她拥进怀中,道:“听这些浑话干什么?不是惹自己不高兴么?阿贝,答应我,别生冬儿的气,也别自怨自艾,好么?”
郝贝苦笑道:“我不生她的气,也不能生我自己的气,难道生你的气么?我我就是个没用的人,怎么样也恨不起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