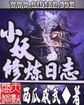饭罢,冬儿太过劳累,禁不住李穆然苦口劝解,便早早地在玉棠的小床上睡下。
李穆然却不休息。他在案后半卧半坐着,读着兵书。他想起在谷中时,常常也是如此,冬儿或采药、或嬉戏、或帮着师父们劳作,自己就在旁静静地看书。那时总觉那样的日子太过平淡,可如今有时忙中偷闲,却希望能重回过去,就那么天荒地老下去。然而这样的日子,今天恐怕是最后一次了。
他怃然默叹,只觉书上的字他都认得,可偏偏看不进去。他索然无味地读了一会儿书,就见仙莫问掀开帘,探进个头来。
李穆然起身走到帐门口,低声问道:“怎样?”
仙莫问道:“李财往后军去了。”
李穆然颔首:“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等仙莫问离去,李穆然也吹熄了烛火,自去休息。躺在床榻上,他暗暗想着仙莫问的话:李财往后军去难道大将军安排在军中那人是张昊?但怎么可能,张昊无才无德,让他当抚军将军,他弹压得住么?
不过也好,自己和张昊比起来,在大将军眼中,自然要重要得多了。李穆然心中一松,暗忖救庾渊的事情算是成了一多半了。
三日后劫法场,他放风声给大将军,实则是拿自己的性命为质,赌慕容垂不得不帮他。只是后日大军先要东行,总要找个人在军中暂代一时。
看来又要麻烦仙莫问了。李穆然无声地笑了笑,如今自己是越来越倚重这位同袍了。仙莫问论文论武都没什么过人之处,但与人打交道,察言观色的本事倒是出众的,更难得的是他遇事不慌,需要他出头的时候,总能独当一面,的确是亲兵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了。
三日后,荆州城刑场。
这一日要斩首示众的共有十余人,庾渊便在其中。人犯们被反绑着带到了木台之上,木台下三丈开外,是层层荆州守卫,再往外的,则是人山人海。
荆州城汉人居多,可这几日为了抓细作的事情,汉人们早就不敢出门,如今站在那木台外的,除了零星几个台上人的亲眷,便都是胡服穿着的人。不少人受了都贵蛊惑,当真以为台上的人都是晋国奸细,隔着三丈远,他们犹往台上扔石子或者烂菜叶。
庾渊被个臭鸡蛋当头砸中,不禁一阵苦笑。站在他身后的刽子手看他兀自好整以暇,狠狠在他膝弯踹了一脚,喝道:“死到临头,还敢嬉笑!”
庾渊腿一软,跪在了木台上。他低头看去,见眼前的木板早已变成了紫黑色,也不知浸染了多少鲜血。他暗自笑了笑,往两边看去,见其他同受斩刑的人早已抖如筛糠,心中不由叹道:“冬儿啊冬儿,你在哪儿呢?”
眼见午时已到,都贵坐在监斩台上,抛下令来,喝道:“斩!”
刽子手抽掉人犯身后的木板名牌,将诸人肩膀往前一按,拨开头发露出脖颈,便要挥刀斩落。
正在这时,刑场两旁的木制高楼内,各射出一支箭来。一箭射的是庾渊身后的刽子手,另一箭射的则是都贵!
射刽子手那箭穿心而过。刽子手大叫一声,钢刀脱手,正砸在了庾渊身边。庾渊忙往旁一闪,继而抬头往上看去,暗自骂道:“姓李的,你不拖到最后一刻就不动手!这不是故意吓我么?”
然而射都贵那箭,则没有射中他本人,只是射穿了他身前的木案。那箭势很烈,把都贵吓得往后一跳,看着箭羽不住晃动,许久才缓过了神来:“来人,抓刺客!”
李穆然和冬儿身处高楼,不由对视一眼。冬儿问道:“那边是谁射的箭?”李穆然摇了摇头,道:“救人要紧,一会儿再说别的。”语罢,已翻身出了高楼。他黑布蒙面,周身黑衣,这一翻出楼来,立时引起诸人瞩目。只是身在闹市,荆州守备苦于不能用弓箭对付他。李穆然几个腾身,便到了木台之上,继而一剑便挑开了庾渊手上的束缚。
庾渊等这一刻已等了好久,手上方得自由,回手便拎起了那刽子手的钢刀。钢刀沉重,他这几日身子没有恢复好,甫拿起刀来,整个人身子还晃了两晃。
李穆然连忙扶了他一把,同时一剑退了近前的几个刽子手。他与庾渊背对而立,随手几剑过去,又撇倒了两三个刽子手,一并解了几个汉人死囚的束缚。那些死囚有样学样,照着庾渊的样子,也抢了钢刀到手。
此时荆州守军已经齐拥而上,站在最前的十来个开始挥刀舞枪,往木台上爬。但是台上的死囚们被得狠了,哪里还管什么杀人不杀人的,一个个抽出钢刀来,便往眼前的人头上砍去。一时之间,尖叫四起,人声鼎沸,刑场之上鲜血四溅,如同地狱。
都贵见状还欲下令,却不料高楼之上箭矢如雨而至,嗖嗖嗖三箭几乎同时发来,一箭钉在他头顶一寸处,一箭射穿了他的左袖,一箭射穿了他的右袖。都贵被吓得魂飞魄散,但也知对方是在警告他莫要管刑场之事。他对手下用眼色,叫人继续往高楼上搜人,然而那手下方转过头去,又是一箭射至,此次那箭手没再留情,那一箭射穿了他手下喉咙,箭到人亡。
冬儿不知高楼上何人助力,但也无暇多想。她见围着木台的守兵太多,便也狠下心来,弯弓搭箭,射伤了几名守兵。她终究不肯多造杀孽,故而手下留情,伤的都是那些守兵的臂膀。
李穆然这时在台上只管护住了庾渊,他见死囚们已与荆州守兵混战一团,便一扯庾渊,问了一声:“你跑得动么?”
庾渊苦笑着摇了摇头。李穆然叹了声气,一低身,喝道:“上来!”庾渊老老实实趴在李穆然背上,问道:“哎,你跑得动么?”
李穆然没回他的话,只冷哼一声,道:“你要是掉下来,我可不再管了!”言罢,提了口气,纵身而去。
他纵然轻功高强,但这时背着个跟自己身形仿佛的男子,也觉得力有不忒,做不到像方才一样来去自如。他瞧准了台下守兵,脚下或踏或踩,点在那些人头上肩上,借力腾挪。
冬儿在高楼中看得好生焦急,只想也下去帮忙,可是高楼底下此刻也围了许多荆州守军,她自己脱身已是不易,哪里还有暇旁顾。
正在这时,忽地一骑快马从城南赶来。马上人还没赶到都贵面前,已高声喊道:“太守!晋军轻骑来袭,就在城南十里之外!”
“什么?”都贵猛地从利箭的恐吓中回过了神来,看着面前这个烂摊子不由连连跺脚。然而这时除了庾渊被李穆然救走外,木台上留下的那些汉人势单力薄,已被守兵杀死大半,其他也难成气候。他见庾渊被救走后,高楼中就安稳了许久,狠狠咬了咬牙,暗道:“算你能逃过这一次!”语罢,指挥五十人继续追着那“黑衣人”,其余人则统统前往城南守城。
高楼之下围势已解,冬儿翻出窗子,使出飞檐走壁的本事,径往城北而去。临走时,她瞧向对面高楼,却见那楼中竟无人出来,只是楼下冒出个伙计,从侧门离开。
这三人穿街过巷,不一时,便把那五十名追兵甩在了身后。三人在城北一个破旧的茅屋中会了面,他们都当过细作,对于易容改装极是熟悉,更不用提李穆然和冬儿更是个中好手。李穆然改装成仙莫问的样子,冬儿和庾渊则扮成了抚军亲兵模样,三人不敢多言,径往北城门而去。
到得城门口,荆州守兵早接到军命不肯放人出城。然而李穆然手持抚军将军令牌,口口声声说是替将军办事,现在南城军情紧急,要前往报信,那几个小小守兵自然不敢阻拦。三人堂而皇之地出了城门,城外早有备好的良驹,如此三骑绝尘,再过少顷,已将偌大荆州古城远远抛在了身后。
三人一直跑到了城北的一处密林中,才勒停了马。
庾渊率先翻身下马,对着李穆然纳身便拜。李穆然哪里肯受他的礼,忙一把扶起,道:“你和冬儿快些回谷。如今战事已起,外边始终不安全。我帮一不可再,下次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庾渊点头,又蹙眉道:“怎么这么巧,你救我的时候,偏偏南城就有晋军过来?”
李穆然道:“总有人在暗中安排。否则单以我之力,如何能救出你?”
冬儿这才醒悟过来:“那个高楼里的人,也是别人安排的?”
李穆然点了点头。他深深地看了冬儿一眼,暗忖她这一走,就和庾渊在一起,只觉心中难过,可看她这时眸中透着无限神采,整个人都开心许多,也觉为她高兴。他又看向了庾渊,看他瞧着冬儿一直在笑,笑得眼睛几乎都眯成了一条缝,只觉心中郁郁,便冷声道:“姓庾的,你回去把武功练好些。总要冬儿保护你,你也好意思?”
冬儿咯咯一笑,斜睨了庾渊一眼,道:“听到没有,现在总算有人站到我这边啦。”
庾渊笑笑,道:“一定一定。你放心,从今而后,终我庾渊这一生,只有保护冬儿的份,绝不会再让冬儿为我出手。”他静了静,又笑道:“话说回来,穆然,我和冬儿成亲之时,你来不来?不管怎样,你总算是她的亲友。”
李穆然心下一黯,看向冬儿。冬儿也目光灼灼地瞧着他,道:“你成亲的时候我没有去,我成亲的时候你若再不来,只怕师父们也要难过的。”
李穆然暗叹一声,强笑道:“我一定去,还要送份厚礼呢!只是我如今行军倥偬,哪里来的时间呢?”
庾渊道:“我观此战要打个半年左右。半年之后,你战事一了便飞鸽传书到谷中,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就订婚期,左右你回谷不会停留超过三日。反正成亲非小事,这之前我们也该准备准备。”
李穆然道:“好!”他不欲多言,上马欲行,冬儿却叫住了他,道:“穆然,你要记着要来观礼。这一仗一定要打胜,你要多多保重!”
李穆然莞尔一笑,道:“你也是,多多保重。早些回谷。”
他催马行远,方走两步,只听冬儿又在身后叫道:“记得吃药!”
李穆然在马上不由失笑,可是没笑两下,却觉满心酸涩,眼前渐渐一片模糊:“冬儿,等你成了亲,我也该履行和阿贝之约,你我二人永不相见了。”
李穆然驾马往东一路追赶抚军大军时,仙莫问正在头痛。他装扮成了李穆然的样子,勉强压着阵,一路东行,一直在默默念叨着将军快些回来。他一直盯着后军张顺,结果对方却全无动静,反倒是一早听见传闻说冠军慕容军侯率领十余轻骑,向西奔驰而归。
慕容烈与李穆然是胜似兄弟的,这件事仙莫问自然知道。他略略放下了心:看样子大将军是让慕容烈去救李穆然,这总比张昊去来得让人放心。可是前几日晚上,李财又为什么去找张昊呢?
仙莫问是跟着李穆然最久的细作,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李穆然的那些心思,他也学了一些。此刻他暗暗思索,忽地明白了过来:大将军是怕慕容烈犹然救不出李穆然,叫张昊在关键时候取而代之可是如此一来,自己这个假冒的将军身份就尴尬了
仙莫问猛地觉察到自己脖颈泛起了寒意,不由默默合十祷告:“阿弥陀佛,无量寿尊,别管什么了一定要让将军平安归来啊!”
而仙莫问在祈祷之时,荆州城中,慕容月已经换回了衣衫。她暗暗骂着自己今日竟没抓住绝佳机会,否则大可一箭射死李穆然,而后把他的死全都推到都贵身上就是。为什么当时在那木楼之中,她就没有打过这个念头呢?慕容月狠狠地捶着自己的头,重重地叹着气:难道自己已经下不去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