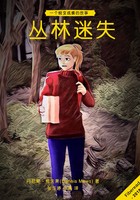随着牢门上的铁链子哗啦一声响过之后,一个约二十二三岁的男青年钻进了牢中。身材同老胖子极为相似,只是从里到外都过于“细嫩”了些,没有老胖子从里到外的那种“粗硬”。
老胖子的脚和老于的脚在一替一换落到这身材肥胖的男青年背上时,那如擂鼓般沉闷的嗵嗵声便比平常响了一倍。
“怎么这么一会儿就没动静了呢?我看进来这小子坨儿挺大,得往死干,要不早晚得‘鼓包’。”小旭在隔壁牢中喊道。
“咱这是和平号,从来不打人。”王冬来转头朝着小铁窗外回道。
“哈哈,谁不知道王哥啊,从来都不打‘死人’,就打‘活人’,哈哈。”小旭笑过之后又继续说道:“哎,王哥,咱这号今天来了一个怪胎,一进号,扑通往地上一跪就开始冒黑——各位老大,兄弟来迟一步,请各位老大恕罪,恕罪——哈哈。”
“哈哈。”邻近的几个牢中同时响起了笑声。
“你怎么招待的?”王冬来笑着问道。
“先‘按摩’,后‘桑拿’,现在还在坑里‘飞’着呢。”
“哈哈。”邻近的几牢中又同时响起了笑声。
“这小崽子,打过一锅儿罪儿,岁数不大,挺辣手。”王冬来从小铁窗上转回头,喃喃自语过后才冲在铺下像笨拙的企鹅一样“飞”着的男青年问道:“叫什么名?”
“金昊。”
“什么事儿进来的?”
“非法拘禁。”
“怎么拘禁的?”
“几个朋友带小姐出门,我跟着去了,小姐要回家,他们几个不让回……”
“这不是绑架吗?”老胖子立刻用重重的一脚纠正道。
“你们家管你不?”对是拘禁还是绑架好像并不感兴趣的王冬来冲老胖子摆了下手,然后对重新“飞”起来的金昊开始进行那不变的盘问。
……
金昊的腿实在是过于肥硕了些,坐到铺上时无论如何都难以盘上。同时那一身肥肉似乎勾起了老于某种难以遏制的欲望,于是在腰没有挺直、乱动了等种种借口下,一遍又一遍用拳脚在金昊那身肥肉上寻求起满足感。
“哎哟,我心脏病犯了。”金昊突然弯下身去,捂着胸口呻吟了起来。
“装相是不是?”老于刚欲起身,立刻被王冬来给拦住了。
“你是什么心脏病?”王冬来问道。
“心肌炎。”金昊呻吟道。
“把这个放嘴里含着。”王冬来从小瓷瓶中倒出几粒救心丹递给了金昊,然后自言自语道:“我也是心脏病,不过我这心脏病是扎粉儿扎的……”
“谢谢王哥。”金昊满脸痛苦地呻吟着把药含入口中。
“冬来,你们号新来的是不是叫金昊?”老中突然在走廊里面的牢中问道。
“是啊,有事吗,老中?”
“他有个同案分咱这号来了,咱这号有个‘上墙’的、叫白立伟,说跟金昊是邻居,给他买了两个菜,麻烦冬来给点儿光,照顾一下。”
“客气啥呀,老中,让他俩说句话。”王冬来从小铁窗上转回头,冲金昊说道:“去后廊边上跟你邻居说两句话,别什么都说,都能听到。”
……
“那个白立伟因为什么事儿进来的?”王冬来冲着坐回到原处的金昊问道。
“因为他对象,他对象和她一个厂的一个小子处上了,立伟一气之下用刀给那个小子捅死了……”
“现在这个社会,只有杀父之仇,哪还有夺妻之恨呢!”王冬来淡淡地说道。
“真是这样,现在这个社会,女人今天跟这个睡,明天跟那个睡,谁是谁的老婆呀!”
……
听到牢内人对夺妻之恨所发的感慨,白漠不禁忆起了几个女孩。
……小铃天生一副忧郁的脸,在自己到那家饭店做厨师后的不久,便因为筹办婚事辞了工。几天后,小铃在夜里回到了店中,当自己笑着抱住小铃嬉闹假吻时,没想到小铃竟真的回吻了自己。
也许是因为小铃的未婚夫,那个和自己一样是厨师的老张,自己躺在小铃身边总是感到不自在,在小铃的半推半就下草草地完了事儿。
“你就这么大本事呀?”小铃嗲声嗲气地娇嗔道。
既累又乏的自己像是没了兴致,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当自己在那椅子搭的床上一觉醒来时,却看到了堆在眼前餐桌上的粉色胸罩,自己情不自禁地把那胸罩握在手里揉搓了一会儿,欲火随之被点燃了,翻身又压到了小铃的身上。
“听你跟他们说,明天就要和老张举行婚礼了,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挺对不起老张。”
……
那是市内最大的一家室内音乐旱冰场,坐落在市中心的商厦顶层。也许不是节假日的原因,溜冰的人少得可怜,想来这时能到这儿来玩儿的人大多都是同自己一样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吧。其实自己对溜冰就像对其他娱乐一样并没有多大兴趣,况且五元一张的溜冰票钱对于自己这样一个既无所事事又生活拮据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之所以去那种地方实在是因为无处可去,更多的是寻觅——一种茫然的、带有某种臆想的寻觅。
昏暗的灯光与低沉的音乐汇成了一种无形的、令人感到压抑的灰调子,仿佛是从这灰调子的无形中走出来的有形,一个穿着灰色长裙的女子像一只飞倦的鸟似的,低着头没精打采地从另一端向自己这边滑过来,自己立刻心急火燎地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买了票换了鞋向那修长的灰色身影滑去。
“我带你滑好吗?”自己向那女子伸出了手。
那女子抬头瞥了自己一眼,莞尔一笑把手交到了自己手里。
自己牵着那女子的手不紧不慢地滑着,一种不知是自然而然生出的还是故作的骄矜使自己既不去细看她也不与她攀谈,更不去问她的名字,就算问了也是记不住的,因为自己是那种连自己生日都记不得的人,更不必说去记别人的什么了。自己的这种冷漠骄矜像一支柔软得无法栖息的枝条令她很快便有了欲落不能之感,同时自己那莫名其妙的天性又像是一股难以捉摸的邪风,令那本就柔软的枝条越发显得摇摆不定了。滑了几圈后,自己淡淡地对她说了声累了,便放开了她的手,一个人滑到护栏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当自己再把眼睛投向冰场里时立刻又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个衣裤郎当、容貌粗俗猥琐、皮肤晒得发黑并透着一股泥土肮脏的男青年龇着焦黄的牙,嬉皮笑脸地用两臂把那女子圈在冰场护栏的一角。那女子不但没有表现出厌烦,而且还低首垂目地同那男青年嬉笑攀谈起来。自己疾速滑过去,鄙夷不屑地从那男青年两臂的围圈中把那女子拉了出来,那男青年似乎连看自己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低着头讪讪地笑着滑开了。
自己牵着那女子的手又滑了几圈后停了下来,这次自己不但没有松开她的手,而且把另一只手也揽在了她那柔软的腰上,顿时,自己的手在无比惬意的凉凉滑滑中找到了一种归宿感。
“我们走吧。”自己提议到。
“去哪儿?”
“去我家。”
……
自己牵着那女子的手沿着河堤路悠闲地向家的方向走着。已是傍晚时分了,河堤路上到处都可见到漫步纳凉的人,可自己却感到了一种美妙的静,静得仿佛这生命的空间只剩下了两个人的呼吸。
自己时走时停,有意在河堤路上拖延着时间,为的是不让邻里看到自己又一次带陌生女孩回家。那女子想是饿了,从包里掏出了一袋烤鱼片吃起来,不时地撕下一条填入自己的口中,并跟上一吻,这湿润的、带着腥香味儿的热吻使那鱼片成了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美味。当自己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楼下已经没有了纳凉的人时才带她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