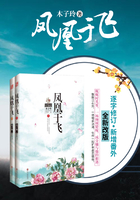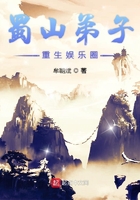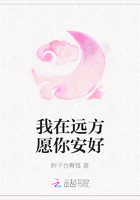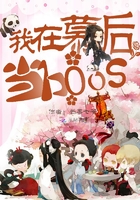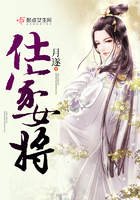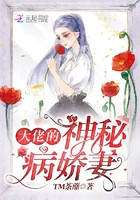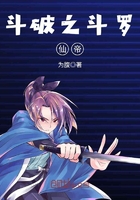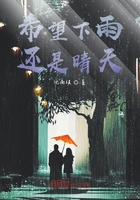关于外公童有源,我的外曾祖母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在她怀孕的时候,不知什么地方正在打仗。一会儿开炮、一会儿打枪的,整日都不得安宁。其实我们都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她的意思其实是说--那躲在娘肚子角落里蜷成一团的外公,他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创伤,结果才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话是由外婆转述的。所以真假难以分辨。但不管怎样,炮声隆隆中,外公出生于1905年的夏天。他是童姓家族的长子。他死的时候我四岁?十四岁?或者刚刚懵懂世事?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他的一生奇怪而又神秘,虽然我几乎从没见过他,却一直视他为至亲的亲人。我知道我的话无法解释。
我的外公出生在京杭大运河苏杭段的一艘木船上。在中国最美丽富裕地区的一个大雾之夜,外公哭叫着来到了这个漆黑一片、景色不明的世界上。多年以后,我乘坐夜航船穿越这一段并不漫长的航程。当熟悉的城市景致已经被清理归类变得毫无个性以后,我发现,夜航船上的午夜仍然漆黑一片。运河两岸的田野、村庄,散落在田野和村庄中间的草丛树木,即便在安静迟缓的月光下面,它们仍然显得面目不清、景色不明。仿佛正有一种难以辨明的危险和忧伤藏匿其中。
我一直觉得,外公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哭喊,其实正是因为他感到了这种危险。
“他生出来的时候,只是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声,就一声……然后,就再也不哭了。”
这依旧是外婆转述的一句话。现在,我仿佛又看到了外婆那张变形的脸。像几乎所有老年人那样,外婆有着一张比例失调的脸,有着被拉长与延伸的线条。但例外仍然存在。一般老年人的嘴形,都有着惊愕而茫然的神情。它们向前突出,微微张开,配上眼睛里浑浊与惊吓的眼光,仿佛对眼前这个再也难以理解的世界既好奇又提防。但外婆不是。她的嘴在轮廓上虽然失去了年轻时柔和的线条,但那苍老古板的嘴唇却是那样高傲的紧闭着。它们微微向下垂落,仿佛一个刚刚撕心裂肺大哭一场的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忍住了悲伤。外婆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那副强忍悲伤的脸。
“撕心裂肺”,这是一个可以同时用在外公和外婆身上的词。但与外公不同的是,我的外婆一辈子都在哭。她只是勉强挣扎着诉说了一次,然后就再也不说了。在心里哭。
我的外婆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她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历险,来自于如履薄冰怆然失重的片断……同样,也来自于这种粗鲁。
就在前几天的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打来的。
那是个终年奔波在蓝天白云以及铁轨公路之间的人。我不太了解他真正的职业和身份。因为他总是不断地变化着职业和身份。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做过演员经纪人,买卖过水暖设备,他因为贩运假酒失踪过一段时间,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带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去一片四面环山的草场看红豆杉林。
我记得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总是很匆忙。就像一只喷了过多香水的苍蝇。他随身经常带着很多叮当作响的药瓶药罐。身体状况好像确实不佳。据说他近年来常患的病大致计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痛风病,胆囊炎,胆结石、胰腺炎、胃肠功能失调……有一次,我和他在一处郊外的农家饭店吃野味时,他还一边啃着鸡腿,一边乐呵呵地告诉我说,最近医生怀疑他因为痔疮严重发作,体内充满了毒素。
那天中午我和他在一家西餐馆吃了午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窗外下起了一阵急雨。天空像是被一些巨大而浓密的眼睫毛盖住了。我和他面对面坐,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睫毛其实相当稀少,而且脸色看起来多少有些抑郁。
后来我们还为一个小细节争了几句--咖喱,那些金灿灿、香喷喷的咖喱,他竟然坚持说吃咖喱是可以减肥的,而我则坚持认为,那种粘乎乎、呛人的东西只会让人更加肥胖。
那顿饭正好延续了一场阵雨的时间。夏天的午后气压很低,仿佛有无数只淡绿色的蜻蜒低飞而过。我喝了几口酒,有点犯困。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他饭前吞下了两颗药丸,饭后甜点的时候又吞了几颗。一颗、两颗、三颗……那些银白色的药丸,就像蜻蜓的眼睛一样在她面前晃动着。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惊了一下。
我好像还叫了起来:“你在吃什么?!”
我一直怀疑他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要知道,这种病非常重要的症状之一就是暴饮暴食。喜欢吃肉,吃咖喱,有时又像食草动物一样无休无止的抱怨。当然,在私底下,我还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感觉:其实他完全有可能患有性病。
还有一个细节我同样印象深刻。在吃饭的过程中,他突然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他说现在他在一家公司里工作,那张照片是他们的合影。在照片里,他穿着略微有点包紧的深色长西装,站在一群比他高出一头的外国同事中间。也不知道是不是聚焦时出了点问题,我觉得照片里的他有点虚。整个人都是虚的,飘在空气里面。就像打靶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准心一样。
他死在我们分别的几小时以后。
我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在我们分别的几小时以后。当时我正在开车。前方是一段笔直的高速公路。在下午刺目的阳光下面,宽阔的路面像惨白的鱼肚一样微微凸浮了起来。大路向东,第一眼看不到拐弯,第二眼望不见尽头。我的两只耳朵里都塞着耳机。我心无旁鹜、专心致志地开车。
我突然想到了外婆头颈里那道绳子的勒印。童年的时候,当我低头看着外婆颈子里的那道勒印时,我也是淡漠的。对于已然而至的死亡,我从来都没有那种爆炸式的强烈感受。惊讶仅仅是为了某种迎合。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时日已长、浓情渐逝的缘故,还是因为对于死亡的某种默认。我并不害怕死亡。那个躺着的人与睡在大床上的那一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更为安静更加平和罢了。我甚至还有些喜欢那铁了心肠、毫无眷恋的人儿……很小的时候我就亲吻了外婆脖子上死亡的痕迹,就如同用我心里的粗鲁亲吻了她的粗鲁。
我经常会在雨天的时候想起亲爱的莉莉姨妈,我外公外婆的长女。她就站在青石板路那棵最老的梧桐树下,背对着我们,腰肢处有着细微柔软的弧度。我的莉莉姨妈直到真正的老年降临时还有着少女般的动作和姿态。她的少女和老年时代没有真正的界线。她内心有一种奇怪的东西,谈不上好坏,难以论雅俗。正是它们,最终打败了她的年龄以及她脸上垂褶累累的皱纹。
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阳光穿透梧桐树叶、照在莉莉姨妈那两排白牙上。她一直都有着异常整齐洁白的牙齿。再高明的外科整形技术,也很难把一个已经六十多岁女人的牙排列成那个样子。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老是习惯性的、完全不加掩饰地笑。而不管怎样,老是这样露出白牙的笑,在旁人看来,多少是有些装模作样、矫揉造作的。
有一年夏天我去看她,她刚洗完澡,正颇为费力地把自己有些过于丰满的身体塞进一件蓝色棉裙里。裙子软沓沓的,看上去没什么筋道。它从莉莉姨妈颇为可观的上半身那儿勉勉强强地掉落下来,收在她骨节突起的膝盖那儿。那是一件更类似于睡衣的裙子。当然,穿在莉莉姨妈身上的时候,它其实更像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
“太阳太大了,不出去了吧。”她懒散地靠在那张布面长沙发上,像少女一样用手托住了自己的腮帮。
我知道其实她更喜欢冬天。夏装的单薄暴露了她晚年已然发福的体态。而冬天出门的时候,她有几身比较好的行头。一顶白色绒线帽,围巾是黑白格晴纶棉的。她还有一双相当不错的棕色小羊皮靴。她喜欢听它敲击在地上的声音。那种相当不错的棕色小羊皮靴发出的声音。
然后,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只要出门,她都会给自己戴上两只硕大的珍珠耳环。它们很亮,很大,也很白。她看着它们的时候,又忍不住露出了那口好看的白牙。它们是假的,很多年前她在沧浪亭边的一个小地摊上买的。但现在,它们就像两轮无比灿烂的小月亮,盛开在她那布满皱纹、已然苍老的耳垂上。
“外公?你想了解你的外公?”
我记得莉莉姨妈仍然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她似乎对我刚才的提问大吃一惊。她猛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仿佛我说的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
今天的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莉莉姨妈那一刻的表情。震惊。愕然。惊惶无措。撕心裂肺……她重新回到了黑暗里……我懂得这个。对于黑暗我是个有着天生感知的孩子。我对美艳的罂粟没有欲望,但那种毒却早已在心里了。和亲爱的莉莉姨妈一样,和这个虚荣、做作的女人一样,我的深情和暴烈像毒一样埋在心里。毒液注满了我的身体,它们在里面奔涌、冲突、挣扎,它们是运河里掩埋千年早已腐烂的沉积淤泥。
我忘了说了,那条夜航船驶过的大河对于外公和莉莉姨妈的意义。他们都曾经疯狂地往返于河流之上。在夜航船破旧不堪、风雨零乱的航线上,他们经历着独自漫长而黑暗的旅程。他们擦肩而过,彼此憎恨,敌视。在这个落日般腐朽的家族里,有很长一段时间,彼此的怨恨与折磨完全掩盖了那深水般潜流的爱意。他们悲怆而倔强地独自挣扎。他们踽踽而行,完全看不到身边同样溺水的人。
所以--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莉莉姨妈是那种只有背影才能显出孤独的女人。
4、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起点的场景--
五十年前,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我看见十八岁的莉莉姨妈正独自一人走在去苏州中医院的路上。
--路的旁边是一条河。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经常被河、水、或者雨包围着。这是一个与水有关的城市。河的很远处则是水面开阔、潜流湍急的京杭大运河的一段。但是就这样看起来,那条大河单调沉闷地独自流淌着,完全看不到与这城市里任何暗流相汇合的可能。
那天莉莉姨妈穿着一件外面套了罩衫的薄棉袄,头发微微卷曲着。在春天暂时还没厚实起来的阳光下面,她显得眉清目秀,并且若有所思。
这位神情妩媚的姑娘得了慢性肾炎,拖拖拉拉有一年多了。每个月有那么一、两个下午,是她和医院约定的治疗时间。她不太想去,因为疗程过于漫长;但她又不得不去,因为医生已经明确表示,她必须耐心、耐心、再耐心……她是个病人,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远处传来几下零星的爆竹声。而两旁冬青树的树梢上,隐约可见淡蓝色硝烟缓缓飘过的痕迹。她深吸了一口气。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走在到处散落着小红纸屑的石板路上,这位名叫童莉莉的姑娘突然觉得,在这样一个欢欣鼓舞、人心振奋的春天,却得了绵延无期的肾病,同样也是可耻的。
就在前几天,单位里组织填写个人资料表格。在“家庭出身”那一栏,童莉莉犹豫了一下。
革命干部……无产阶级工人……资本家……工商业兼地主?都不对。在富春江老家,她父亲童有源倒确实是有几亩地。她隐约也知道些情况,十五亩土地以上,五头牛或者驴以上,根据富有程度可以划分为富农、地主。但问题在于,她父亲所拥有的土地和牲畜达到那个数目了吗?况且,在离开老家的时候,他已经变卖了几乎所有的财产。也就是说,在认识童莉莉的母亲王宝琴以前,在童莉莉降生人间以前,她这个名叫童有源的父亲就已经是个身份相当可疑的人。
不过,她父亲又确实在上海的一家洋行干过一阵子。有时,他还来往于老家、上海与苏州,兼带着做一些土产生意。有一年,他甚至跟着一位不明身份的传教士去了遥远的香格里拉。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闲散而容长身材的中年人。吹吹箫,叠几块怪石。还很喜欢女人和美食。
后来,在那张表格上,童莉莉迟疑地、颇有些痛苦地写下了两个字:“职员。”
这是一个中性的灰色地带。童莉莉很不喜欢。在某种意义上,她是一个把革命与浪漫联系在一起的理想主义者。她从没去过北京,但她向往北京。那个火红的、纯净的、轰轰烈烈的地方。然而,她又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喜欢在蓝天下看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却也喜欢在月圆之夜的梅树底下听父亲童有源吹箫。
因为她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都让她感觉兴奋、愉悦和明亮。私心里她甚至暗暗觉得,其实,它们应该是没有分别的。
而“职员”--这两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汉字,在年轻的童莉莉看来,它们是那样的无力与中庸,几乎就像是又一场拖拖拉拉、绵延不断的肾病。
5、
这一家都是病人。这便是童莉莉的故事的开场。她还没什么不好的。她还年轻。上个月单位拍的标准相里(她在一家小报馆的资料室工作),她看上去还是相当的秀气可人。唯一的遗憾只不过是她得了肾病,经常会觉得腰酸无力而已。得点病总是难免的。再说这是一种慢性病,也是急不得的。
她倒是常常会出神、发呆。别人看到也就看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纤弱单薄、看上去还多少有些虚弱的女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
她母亲王宝琴很有些抑郁狂躁症的症状。其实就是抑郁狂躁症了,到晚年的时候症状就非常明显了。只不过当时还看得不是那么分明,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法。其实就是那样了。不管王宝琴晚年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打开了管道煤气的开关,安静地躺到了床上;或者还是关掉所有的门和窗,打开煤气开关,然后把一根绳子挂在梁上,再用力打上一个结……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
其实这一切从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从王宝琴站在上海外滩的一个僻静之处时就已经开始了。在那里,王宝琴遇到了这个名叫童有源的男人。那时,她有个不错的典当行。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楼。那时她还很是有一些钱。她一定还是规整的。血液里的东西还在血管里规则和谐地流动。那时童莉莉的这个母亲还没有发疯。但也快要疯了。已经疯了。
童莉莉的那个父亲就更不用说了。
还在童莉莉六、七岁的时候,这个家里曾一度风传童有源得了重病。有几个不那么冷的下午,童莉莉陪着父亲去盘门附近的一家诊所看病。那是个上海过来的医生,手背上长着和童莉莉一样的酱紫色冻疮。他大半个身体埋在一件织得松松垮垮、并且同样是酱紫色的毛衣里面--
“最近睏觉好伐啦?”上海医生的声音从毛衣深处幽幽地传出来。
“还好的。”
“那么胃口呢,吃饭胃口好伐啦?”医生接着又问。
“也还好的。”
“近来开心伐,心情好伐啦?”医生不屈不挠地追问下去。
童有源迟疑了一下,没说话。
“家里有小人伐……几个小人啦?”上海医生从那件松松垮垮、然而却是小麻花大麻花、织法繁复纠缠不清的毛衣里抬起头来……意味相当深长地看着童有源。
童有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情。
“唉……你的这个毛病呵……”上海医生使劲地皱起眉头来。
“……”
“我对你讲,我老老实实对你讲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