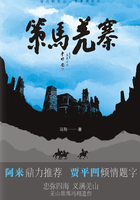哑巴在桃林里支起几十顶帐篷,以应外地赌徒午休之需。桃花彩选开彩后,赢的把酒庆贺、输的埋头裹腹,当地人或手舞足蹈或如丧考妣,回家养精蓄锐以待晚上时来运转;外地赌徒酒足饭饱后便穿过一线天,爬进帐篷睡大觉。午后,暑气渐渐降低,灼人的日头被挡在浓密的桃林外。一觉醒来的赌徒钻出帐篷,望着繁星一般密密挂在树梢、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哪能不喜笑颜开。水蜜桃的树冠开张、叶片宽大,树底下非常适合人的活动。他们选着个大的、成熟的,举手便摘。
这个季节的水蜜桃都成了满面红光的胖子,不仅非常丰满,而且多汁多肉。拭去果皮上一层薄薄的绒毛,那种润泽几乎要闪射出光来。托在手上,每一个果实都是一颗硕大的珠子。有多大肚皮放开吃,肚皮撑不下还可以带走一塑料袋。赢家心情愉快,视桃林为天堂;输家心情沮丧,猛吃一顿以解愁烦苦闷。当他们走出一线天,蓄山羊胡的老头就守在关口收钱了,一人十元,不论你睡帐篷没有、吃桃没有,一律十元。
如果说桃源是闽西的钱庄,陶氏祖祠就是钱庄老板的钱柜,抓一把空气都能拧出油来。
什么治理桃花会,什么面临严峻考验,我范某一个市委书记还不清楚桃花会是怎么回事?还要一个小女子来提醒?笑话。想到花季说的话,仰靠在蓝鸟驾驶副座上的三把火笑了。三把火喜欢坐驾驶副座,视野好、独立,后排留给秘书,要搭上一两个人,就跟秘书挤吧。民间标会在广东、浙江、江苏都有,周边的永安、连城还刚刚烂过会,岂止桃源市有桃花会?三把火发现,烂会的过程总是千篇一律:先是民间互助,然后以赢利为目的,然后抬会,然后全民参与,最后是烂会。这是一条铁律,报纸、简报、通报、内参都这么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在跑。三把火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有能力提前介入,更不要说制止,他们处理烂会的惟一方式就是严惩会首、清理债务。三把火注意到,只要自己不标会,地方官员使出雷霆手段惩办会首,不但能躲过金融风暴,还能落个治理有方的政绩。
三把火自以为聪明的诉求远不止这些,桃花会、桃花彩选给桃源带来了人脉,人脉就是钱脉,桃源要做的不是釜底抽薪,而是趁热打铁,乘着人来钱涌的狂潮,抓住机遇把桃花街形象工程、桃花坞别墅区搞上去。项目上去了还怕什么烂会,腾出手来弹压就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除了奋力一搏,三把火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
为官之道,有的事可以做不可以说,有的事可以说不可以做。比如计划生育拆房子,可以做不可以说;类似“要唯实,不要唯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之类的话,说一说而矣,谁要真这么做了,乌纱帽一天都保不住。今天,三把火就是要做一件只能做不能说的事:对付一个厦门客商。
桃源的水蜜桃不是泛滥成灾吗?这种状况几家欢喜几家愁,愁的是果农,喜的是商家。厦门金宝集团的老总叫罗宁,带了一个秘书姓喊,桃源之行的目的就是考察水蜜桃压榨易拉罐果汁的可行性。三把火就不信,低到形同白送的价格他们会不动心。
罗宁留平头,中等身材,特征是没有特征,与众不同的是漠然的脸上有一股狠劲儿,凝思的时候眼睛会像雄鹰一样阴冷而深邃,令人过目不忘。看他白净斯文的模样,假如不是那双邪邪的眼睛,猜断肠子你也看不出他是个大老板。相反,喊秘书则是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嗓门像他的姓氏一样粗犷。俩人往哪儿摆,人家都以为老喊是老板,罗宁是秘书。没有漂亮女秘书还叫大老板?搞笑。只是什么时候要带男秘书、什么时候要带女秘书,连这个也会弄错,那也不叫大老板了。
听三把火一吹,罗宁基本同意在桃源投资三千万,建设“金宝饮料厂”,等事业发展了,再考虑筹建配套的罐头厂,将桃果加工成果脯、果酱和蜜饯,甚至将桃仁、桃胶和桃根制成药材。饭桌上已经谈到土地转让费、工业用电价格、农民工待遇等具体问题。
水蜜桃果肉柔软多汁,容易消融,这是鲜桃不同于其他水果的地方,这种特性致使它不能保鲜,也不易包装、贮藏和运输。如果卖不掉,除了眼睁睁的看着它腐烂发臭,果农就只有抱头痛哭的份了。
对三把火“遍地鲜桃烂如泥”的说法,罗宁难以置信。百闻不如一见,罗宁要微服私访,了解水蜜桃的真实售价。
罗宁那辆加长的卡迪拉克是开不进武陵村的,俩人坐三轮人力车一路晃悠,武陵村给他们的感觉不是农村,而是一个巨大的水果仓库。街道两边的水蜜桃山丘似的延绵起伏,没有看守,没有标价,来去匆匆的路人正眼都不看那些桃子,空气中一股浓烈的水果腐烂的酸臭味。老喊走下车,拾一个桃子在手,一看就知道是正宗的桃源品种,属于玉露水蜜桃的佼佼者。
旁边有一家小百货店,老喊放一个桃子在秤盘里,指针正好是一百克。罗宁问店老板:
“这桃是谁的呀?”
老板是个暴牙妇女,忙着往货架上摆榨菜,“有多大肚皮就吃吧,你管它是谁的。”
罗宁又问,“怎么卖呢?”
“你们是收购桃子的?”由于吃惊,老板的大门牙飞了出来。尽管暴牙漏风,她还是把话说清楚了。“要买就买我们家的,价钱你们看着给,真的,我们家的桃子长相靓丽,口味也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家的桃子不吃不知道一吃吓一跳,保证你今天吃了明天还想吃。听口音你们是闽南人吧?闽南好啊。闽南佬闽南佬,夏天不戴斗笠,冬天不穿棉袄。”
罗宁笑了,“你们不卖桃子,人都干嘛去了?”
“赌博。”
罗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光知道澳门可以公开赌博,难道桃源是小澳门不成?老喊递一张名片给老板,她的暴牙又飞了,“世上还有姓喊的,看着都累。”
“我老家在武平,那里还有姓红的、姓绿的、姓蓝的,眼花缭乱吧。”老喊说,“你们是怎么赌的?”
“不叫赌,叫什么来着,对了,叫桃花彩选,跟香港的彩票一个意思。”
罗宁来了劲头,“能带我们去看看吗?”
“看看?有什么好看的,要就玩一把。”
“走啊。”
“要走可以,你们答应我,先买我们家的桃子。”
“没问题。”罗宁掏出皮夹,抽两张百元大钞给老板,“算是定金吧。”
老板收起钱,大暴牙飞向里屋扒酒糟的男人,“你顾着店,我带两个闽南佬去玩一把。”
三把火出行的队列一般是秘书开路、自己居中、司机断后,目的是方便秘书通报。还在村支书家门口,秘书就大声吆喝,“范书记来啦。”
支书的脸都白了,他正同山羊胡一块数钱,大小不一的钞票倒得满桌子都是,要收显然是来不及了。支书不愧是支书,事实证明,他的村支书不是白当的。他拎起桌布的四个角,将裹起的钱往山羊胡怀里一塞,“快,进房间。”
“哎呀呀,什么风把我们书记大人给吹来了。”支书满脸堆笑,大步流星冲三把火迎去,“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三把火心事重重,不愿跟他废话,“那两个厦门客商在哪儿?”
“什么客商?”支书揭开茶罐盖子,糊涂了,“不晓得啊。”
秘书帮腔道,“陶书记,你就别泡茶了,赶紧找到那两个客商。”
支书盖上茶罐,想想不对劲,重新打开搁在秘书面前,“麻烦你泡茶,我来找人。”
支书往文书家挂电话,几句话一对,文书就心中数了。“肯定在祖祠买桃花彩选,我刚才扒酒糟,听我老婆说要带两个闽南佬去玩一把。不是桃花彩选,还有什么好玩的?”
三把火拉支书上车,赶到陶氏祖祠,赶上一场好戏。
事情是这样的,老喊买了一千块钱筹码,填上“禄鼠门”和名字,将桃花封投进密柜。神铳一响,谢军头顶的彩筒散开,展现的花词果然是“谷雨三朝看牡丹”。取出桃花封,老喊悲喜交集,喜的是中彩,悲的是中彩却拿不到钱。老喊向哑巴出示名片,说自己是厦门客商,来桃源投资办厂的,不知道文化馆的门朝哪儿开,也没空去兑奖品,希望筹码能兑成现金。罗宁也发了一圈名片,证明老喊的话句句属实。
哑巴很为难,捏着名片跟张思发和谢军紧急磋商。为了吸引“游客”,张思发和谢军都穿上复古的土布长衫、剃光前额套上假辫子。张思发拿不准,说“破了例不好办。”谢军摘下假辫,抻出布袖子擦去头顶的汗珠,“一定要给,”他果断地说,“厦门人来桃源不是为了桃花彩选的,肯定另有来头。”
哑巴歪起脖子权衡一番,还是吩咐劫波点三万块给老喊。劫波数钱数到每个手指都缠上胶布,因为她已经会用五个指头数钱了,速度跟银行储蓄员差不多。意外之财到手,老喊兴高采烈准备离去,却被一个叫陶火旺的人堵在祖祠门口。陶火旺是谁?见过他染成红色尖刀式头发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今天的陶火旺更不好惹,他一千块钱的筹码也中了“禄鼠门”。陶火旺堵住老喊,伸长脖子冲哑巴喊话:
“我也要兑现金,不然,相骂没好口,相打没好手。”
哑巴拨开人丛走过来,斜嘴一笑说,“远方的客人特事特办,其他人一律去文化馆兑奖品。你不是在刁难我吧?”
陶火旺攥住老喊不放,“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全靠方立伟,谁敢刁难你啊。来的都是客,凭什么狗眼看人低?”
“你要这么说话,叫村支书来评评理。我就不信,你一只手能遮了武陵村的天。”
“村支书?村支书跟你还不是裤裆里的两个卵。要评理,我来找人。”陶火旺松开老喊,拔出手机就挂110,“喂,陶氏祖祠聚众赌博闹事,你们快来吧,出人命了。”
这么一挑拨,中彩的人鼓起了兑现金的勇气、赔钱的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层层围堵门里门外。哑巴像落入饥饿的鸭群,只见张开的大嘴和伸长的脖子,再也辨不清谁在要求、谁在痛斥、谁在指责。
这么一拖,就把110的人拖来了。一伙戴头盔的巡警跳下警车,光头老虎雄走在最前面,他什么也没说,凭眉宇间的阴鸷杀气就把围观的人逼开。人们鸦雀无声,只传来门口油锅煎炸的细响。
“谁赌博闹事?”
陶火旺看看哑巴,再看看谢军、张思发,一指老喊说,“就是他。”
老虎雄跳动头皮上下打量老喊,扑过去就搜身,拽出老喊裤兜里的三万块钱。意外之财刚得手又旁落,见多识广的老喊怎么会服气?
“这是非法搜查,我要投诉你们。”
老虎雄使劲一推,老喊于是面墙而立,老虎雄用手上的钱一抽他的后脑勺:
“赌博闹事还嘴硬?再嘴硬拘留十五天。”
罗宁看不下去了,“警官,我们是厦门来的客商,要在桃源投资办大厂的。”
老虎雄掏出手铐,“同伙吧?正好一起走一趟。”
罗宁背过手连连后退,“你不是开玩笑吧警官,我们生意人戴手铐不吉利的,手铐一铐,钱财溜掉。”
老喊转过身,严肃地面对老虎雄,“我们是范书记的朋友,真的得罪我们,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年轻人?”
老虎雄的头皮跳来跳去,停在愤怒的表情上,猛地铐上罗宁的右手。老喊企图缩进人群,两个巡警架住他,也铐住了右手。两人都被铐右手,就无法并肩而立,站在一起显得怪异。老虎雄满意地笑了:
“你们不是三把火的朋友吗,到巡警大队等他吧。”
“不用去了。”众人循声一望,正是三把火一行大踏步走来。围观者“噢”地齐声呐喊,为三把火让出地方,他们心中有数,好戏的高潮到了。三把火在两个客人面前立定,鞠了一躬,满脸诚恳:
“实在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我很负责任地对你们说,这真的是一场误会。”
三把火当众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等老虎雄的配合动作了。老虎雄岿然不动,头皮猛烈跳跃,脸色憋得紫红。场面僵持着,空气都凝固了,巡警们急促到呼吸困难,一个机灵的夺过老虎雄紧握的钥匙,打开手铐,并将三万块钱塞回老喊的裤兜。三把火扫视一遍巡警,矛头直指老虎雄:
“我不想给你们上法制课,也不想给你们讲大道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谁影响桃源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桃源的面子,我就摘谁的帽子;谁工作通不开路子,我就换谁的位子。”
老虎雄头顶布满了汗珠,右手提到腰间手枪的位置,那个机灵巡警觉察到气氛的异常,按住了队长的手背。
老喊掏出钱,甩到老虎雄脚下,“年轻人,我来这里是想碰碰运气,不是为赢钱。三万块钱算什么?塞牙缝都不够。既然运气不好,这钱我也不要了。不过我发誓,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会出现在桃源这个破地方。”
罗宁摸摸被铐痛的手腕,不冷不热地说,“平平安安回家,我就谢天谢地了。范书记,一个街上站大岗的也不把您放眼里,要警惕啊。”
客人愤懑地走了,带着满腔的投资热情、带着三把火的宏伟蓝图。三把火目送俩人的背影,蒙在原地,突然,一个灵感击中了他,又撒腿赶了出去。
所有在场的人都目击了桃源市难得的风景:两个匆匆赶路的闽南佬屁股后面,紧追着三把火;心急火燎的三把火屁股后面,紧追着秘书;左右为难的秘书屁股后面,紧追着蓝鸟车;若即若离的蓝鸟车屁股后面,紧追着长长的尘土。
老虎雄没走,他并不知道自己留下来该干什么,只知道自己不应该跟在三把火的屁股后面。等长长的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