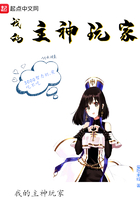年少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便是在知了没有蜕皮之前,将它们捉了来,放入罐头瓶子里,在夏日夜晚的灯下,大人们都睡熟的时候,悄无声息地看那个瓶中的小虫,怎样静静地趴伏在光滑的玻璃上,开始它一生中最重要的蜕变。
这样的蜕变,常常是从它们的脊背开始的。那条长长的缝隙,裂开的时候,我几乎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外壳与肌肉之间,撕扯般的疼痛。它们整个的肉身,在壳中剧烈地颤抖,挣扎,但却没有声息。我只听得见老式钟表在墙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蝉细细长长的腿,扒着光滑的瓶壁,努力地,却又无济于事地向上攀爬。那条脊背上的缝隙,越来越大,蝉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慢慢将新鲜柔嫩的肌肤,裸露在寂静的夜里。但我从来都等不及看它如何从透明的壳里,如一枚去了皮的动人柔软的荔枝,脱颖而出。我总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地睡去,及至醒来,那只蝉早已通身变成了黑色,且有了能够飞上天空的翼翅。
因此我只有想象那只蝉在微黄的灯下,是如何剥离青涩的壳,为了那个阳光下飞翔的梦想,奋力地挣扎,蠕动,撕扯。应该有分娩一样的阵痛,鲜明地牵引着每一根神经。我还怀疑它们会有眼泪,也会有惧怕和犹疑,不知道褪去这层壳,能否有想要的飞翔,是否会有明亮的歌声。我还曾经设想,如果某一只蝉,像年少的我一样,总是害怕大人会发现自己想要离家出走的秘密,因此惶恐不安地在刚刚走出家门,便自动返了身,那它是否会永远呆在漆黑的泥土里,一直到老?
但是这样的担忧,永远都不会成真。每一只蝉,都在地下历经10年的黑暗,爬出地面,攀至高大梧桐或者杨树上的第二天,为了不到3个月的飞翔之梦,便褪去旧衣衫一样,从容不迫地将束缚身体的外壳,弃置在树干之上。
这样振翅翱翔的代价,如果蝉有思想,它们应该明白,其实称得上昂贵。但是每年的夏日,它们依然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就像每一个不想长大的孩子,最终都会被时光催促着,从视线飘忽不定、局促慌乱,到神情淡定自如、从容不迫。而这样的成长,其中所遭遇的疼痛,留下的伤痕,外人永远都不能明白的苦楚,全都化作沙子,生生地嵌入贝壳的身体,而后经由岁月,化成璀璨的珍珠。
而今我90后的弟弟,历经着80后的我,曾历经的一切惶惑与迷茫。他在一所不入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学一门连授课的老师,都认为毕业后即会失业的技术。他从乡村进入城市,被周围穿着时尚的同学排斥,他的那些自己尚且找不到出路的80后老师,根本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他出门,被小偷尾随,抢去了手机,为了可以重新购买一个新的,他省吃俭用,从父母给的生活费里硬挤,却在一个月后,因过分节食而不幸病倒,只去医院就花去了几百。他在南方那个没有暖气的宿舍里,向我哭诉城市人的冷眼和没有朋友的孤单时,却未曾换来我的任何安慰,因为,我也正在为工作和论文而燥乱焦灼。
其实我一直认定,他在走出家门独自面对那些纷争、喧哗和吵嚷时,自有一种柔韧的力量,可以让他在外人的白眼、嘲讽与击打中,挣脱出来,就像一株柔弱的草,可以穿越冷硬的石块,甚至是坚不可摧的头骨。他或许为了获得一份真情,一碗粥饭,而抛弃昔日宝贵的颜面。或许这样之后,他依然一无所获。但是这样的代价,犹如蝉蜕,除非他一生都缩在黑暗的壳里,否则,必须要无情地遭遇。
我知道而今的他,依然不能够原谅我的冷淡与无情。他一次次希望能够从我这里,得到慰藉与帮助,可是我却置之不理,又假装对他的疼痛,一无所知,毫无感触。可是我也知道,当他从那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里毕业,在社会中几经碰壁,受尽冷遇,然后终于寻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的时候,他会明白我昔日的种种淡漠,不过是为了让他,在从校园到社会的这一程行走中,能够提前习惯这个俗世总是不能如意的温度。
这样的习惯,便是疼痛的蝉蜕。代价,永远都不能逃离。
那时我已经开始爱美,会在肥大校服的里面,穿碎花的衬衫,天热的时候,将校服的拉链,尽可能低地拉下去,露出那一蓬一蓬散漫开着的花朵。有男孩子看过来,会羞涩地低头,手指轻轻绞着校服的一角,似乎,想要从里面,绞出一丝炽烈的勇气来。
那时真是单纯任性的小女生,十五六岁吧,总抓住一切可以不穿校服的机会,放任自己妖娆地绽放。老师们在讲台上,看见谁故意地将校服穿得凌乱不堪,就会板起面孔,说一通女孩子要自尊自爱的话来。而我们,则于课下凑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讲这个老师的八卦和坏话,一直讲到心满意足,被批的那点小委屈,终于烟消云散,我们又回复到昔日嘻笑打闹、热爱臭美的一群。
是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将一盆茉莉,摆在桌子上,说让我们描摹。邻桌叫茉的女孩,却偷偷地将一朵花瓣柔软芬芳的茉莉,画在了自己校服的内侧。画完了她便伸过头来,欣喜地要与我分享。就在我刚刚瞥了一眼那朵呼之欲出的茉莉,还没有来得及惊讶茉的大胆笔法时,老师便一脸威严地走了过来,而后不容分说地,让我和茉站到讲台上去。
惶恐中与茉肩并肩地站到讲台上,等待老师的冷嘲热讽,和同学善意却刺目的同情。老师冷冷地让茉给大家“展示”一下她的艺术作品,知道这是故意的揶揄,但茉却骄傲地朝老师微微一笑,而后打开校服的一侧,又像鸟儿一样,铺展开另一侧。台下一片哗然,我小心地顺着老师愤怒的视线朝茉看过去,这才吃惊地发现,她右边的校服内侧,竟然开满了大朵大朵绚烂的山茶花。而当她背过身去,将衣领内侧也翻开来,竟是一条长长的绿色的青藤!
老师的脸,霎时像泼了一瓶油彩,红的绿的蓝的紫的,混在一起。而这些颜色被他僵硬的面部肌肉一抖,扑簌簌地,便全都脱落下来。台下开始有人高声地喊叫,唱歌,像一群被束缚太久的鸽子,呼啦啦地,便撞开了笼门,飞向那高远纯净的蓝天。
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场由茉引导的手绘的革命,它在我们那个保守封闭的小城,犹如一道雨后的虹彩,张扬炫目地,挂在天边,让每一个人,都渴望走近它,采摘一片,放入背后的行囊。
我们手绘自己喜欢的花草,飞鸟,童话,音乐,明星,格言。我们还自创抽象唯美又神秘莫测的图案,而其中蕴含的爱恨,除了那个校服的主人,无人可解。我曾经将对另一个男孩的暗恋,只用一片水中漂泊的绿叶,就含蓄完美地表达出来。而茉,则把对一次测验失利的懊恼,用一个龇牙咧嘴的小人儿,尽情地发泄。男生们呢,则在校服上绘满崇拜的球星、赛车手,或者一个女孩秀美的双眸,一行爱的英文字母的缩写。
老师们终于无力阻止这股手绘的潮流,任我们将画由内至外,涂满原本单调的校服的每一寸空间。昔日总强迫我们穿校服的体育老师,却是喜上眉梢,因为,我们终于不用他耳提面命地,才勉强穿起校服,绕操场跑步了。那些绘满青春符号的校服,像是猎猎彩旗,陪伴我们,激情地,迎风奔跑。
几年后我离开校园,来到北京,在一所中学的门口,看见那些出出进进的男孩女孩,与年少时的我一样,穿着肥大的校服,脸上挂着漫不经心的表情,而所有流行的物语,不必看报上网,只需瞥一眼他们校服的衣领,袖口,肩背,便能管中窥豹。
而我,站在北京的街头,看见那些青春的代码,在校服上熠熠闪光,犹如我已经远逝的年少时光,那样的鲜明,疼痛,又感伤无助。是到那一刻,我才看清了,自己一路行走奔波,却始终不肯,驻足回望那段岁月的原因。
读大学的时候,人渐渐失去中学时的单纯,不再小心翼翼地凡事都遵守规则,亦不再崇尚权威,对于许多事情,常常抱有逃掉的侥幸心理。而且在这一路奔逃里,觉得刺激,似乎,逃掉老师的呵斥,逃掉门卫的检查,是件物超所值的事情。尽管,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那头小学课本里傻笨的黑熊,捡了芝麻,却丢了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