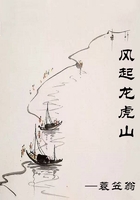4、
在隐隐的枪炮声和弥漫的硝烟中,人们迎来了新的一年,农历春节也快要来临了。贾先生的教桌上书柜上到处都堆满了红纸,那是乡亲们拜托贾先生写春联的红纸。教学已经暂停,贾先生从早到晚忙着书写好像永远写不完的红纸;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各自在自己的砚台里磨着墨,源源不断地供给先生。写完田明理家的对联,贾先生指着贴大门的一副宽大的对联对田明理说:“我年年都想给您家写这样一副对联,可是一直不能写,因为下联不实。今年终于给写上了!这是因为有了你。重任在肩啊!努力吧!”说罢,双目灼灼地盯住田明理的双眼。田明理看了一眼那副对联:“忠厚传家;诗书济世。”对这副门联的含义田明理不十分明了,但是从先生的话语和目光里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更感受到了先生的殷切期待和鼓励。
贾先生的对联写完了,也要过年了,凤梧书院在除夕前一天放年假了。
田明理回到家里,照例忙着给母亲背书。从上学那天起,似乎成了定例:明理放学回家当晚得给母亲背诵当天的课文,母亲则翻开课本,就着字数对照着儿子的背诵,一方面检查着儿子的背诵,同时也对照着学着认字。今天放假了,明理背完课文,把自己已经学完的课本摞在一起,推到母亲面前,认真地说道:“大娘,把这些书都卖了吧!俺都背熟了,您看书都还新着呢!”理娘听了感到诧异混合着生气,问道:“为什么要卖书?”“大娘,卖了钱买好面,咱就不吃杂面了。”明理认真地回答。理娘听了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子,鼻子一酸,一把把儿子揽在怀里,忍不住潸然泪下。农家一季夏粮多不足以维持全年的生计,到了秋粮归仓通常杂以秋粮掺合着,原来的好面(麦面)卷子变成了“花卷儿”、“驴打滚儿”。麦子吃完了的人家则全是“杂面”做成的“窝窝头儿”、“饸饼子”了。田明理生来“嘴瘸”,吃豆面头昏,吃秫秫面咽不下,宁可只喝稀饭、吃红芋、吃胡萝卜。忠老爷经常嚷着要理娘给明理单做好面馍,可是理娘一直默默地“抗命不遵”。其实理娘心里经历着艰难地煎熬——全家人都吃杂面,公公吃杂面,两个小叔子吃杂面,莲莲吃杂面,能给自己的儿子单吃好面吗?!她这个家庭主妇难呀!今天,幼小的儿子想到把属于自己的唯一能够奉献的——几本书奉献出来……母亲的泪水滴落到了儿子的脸上。田明理挣开母亲的怀抱,吃惊地看着母亲,以为是自己犯了错,让母亲伤心了,慌忙说道:“大娘,咱不卖书了!大娘,不卖书了!”一边使劲摇晃着母亲。理娘抬手抹干了眼泪,用力吞咽下混进口腔里的微咸的泪水,复又把儿子抱进怀里,温柔地安慰着:“等麦收就好了,全家就有好面吃了。再说,你那几本书也卖不到多少钱,买不到多少好面。要过年了,咱家也蒸了好面馍,明儿个起,咱家都吃好面馍。”明理听了放开了刚才的紧张不安,生起了过年吃好面的希冀。
理娘接着对儿子说:“理儿,咱念书不卖书,念过的书都好好收存着。大娘给你讲过的那些英雄,那些做大事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都念过很多很多书,书都装满了书箱、书柜、书房。”理儿认真地听着,不时点着头,脑子里不断闪过母亲讲过的一个个令自己崇拜的人物。理娘见儿子认真地听着,接着说道:“理儿也要念很多很多的书,也要装满书箱,装满书柜,还要有一间书房,装满很多很多书。理儿,听懂了吗?”“大娘,我懂了——咱不卖书,俺要念很多很多书!”明理认真地回答说。自此,田明理一直钟爱书籍,爱惜书籍,自己的课本,还有不断买来的书,连同自己的作业本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保管得完完整整。然而“卖书”,似乎一语成谶,十一年后,田明理的十多年的藏书真的全部被人卖掉了。
趁着战争的硝烟,土匪又猖獗起来。一个冬夜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十里八乡的平静。芦荻村东南五里的台庄的花先生家遭遇了土匪的抢劫,而且是明火执仗,还开了枪,好在没有伤到人,只是在花先生的背上用“洋犁子”(子弹头儿)“犁”了几道长长的伤口儿。花先生姓胡名杏林,南方人,迁居台庄行医已有多年,主要是给方圆十里八乡的孩子们种花儿(牛痘),所以人们惯称花先生,倒是几乎把其姓氏给忘了。花先生与田仁喜交往甚厚。田仁喜赶下桥子集听到消息,散集回家时专程绕道去看望了他。以往土匪作案的器械只是刀、小攮子之类,而今持有火器了,给善良本分的乡民增添了更大的恐惧,也让田仁喜平静的心又悬吊起来。
时隔不久,新年刚过,大槐树田家西邻闵家遭抢。一声清脆的枪声震撼了寂静的寒夜,也惊醒了大槐树田家。忠老爷父子四人迅速穿衣出房,集合到院子里,随后分头守护几段墙头。紧接着从闵家传来撕心裂肺的嚎叫声,那是西院男主人闵兴财受惨刑折磨时发出的令人战栗的绝望嚎叫……忠老爷转回东屋拿着白蜡棍,就要卸大门闩门杠。
“大!您不能出去!”田仁喜过来挡住了父亲的大手,阻止着父亲说。
“放开!你听!那帮畜生正在造孽!”忠老爷大声吼着,猛地拨开田仁喜的手,用力卸着闩门杠。
“大!不行!他们有枪!”田仁喜坚定地挡住大门。
忠老爷怔了一下,一双大手迟缓地收了回来,狠狠跺了一脚,“嗐”了一声,恨恨地离开大门,急促地在院子里来回走动着,宛如一只饿虎被关在铁笼之内。很快嚎叫声停歇了,接着,响起一声无力的关门声,最后一切归于寂静。
天亮了,一切归于光明。闵家人一夜没有睡。闵家在早做鞋帽烟酒糖等小买卖,后来改做色布生意。昨天闵兴财刚刚从鹏州进布回家,夜晚就遭了劫匪。劫匪个个都拉下套头帽子,整个头脸脖颈罩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贼眼。他们不满足于屋里堆放着货物,鸣枪逼着闵兴财交出家藏的黄、白、黑货,又用尖头儿子弹在其后背狠狠“犁”着,留下一道道血肉模糊地创口。见闵家实在拿不出金银烟土,匪徒们便将浮财货物洗劫一空,并押着闵兴财一路出村,到东南乱葬岗子将其两条小腿刺穿弃之而去。
劫后的闵家,一片破乱哀痛的凄惨景象。闵兴财浑身血污俯卧在床痛苦地呻唤着。罐儿娘哭红了眼睛伏在床头安慰着丈夫。闵东山老太爷、缸儿、罐儿束手无策地满屋转悠着。直到罐儿的舅舅领着孙小街子的医生孙天和赶来了,全家才得到了些安慰。孙天和忙着给闵兴财清理创口,床上不时爆出压抑住的呻吟声。罐儿娘里里外外忙活着。
乡邻们陆陆续续来到闵家看望,留下一些近乎相同的安慰话语后离去。理娘领着明理、莲莲来了,看到伤者的惨状,不由得呜咽起来:“这些天杀的土匪,真该天打五雷轰!”缸儿娘反倒转过来劝慰理娘,拉着理娘坐下来,自己也挨着坐下。因为屋里人来人往,不便对土匪猜测议论,罐儿娘又要忙里忙外的,理娘劝慰了一番离开回家。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