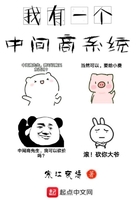11、
徐业慷慨激昂地讲话倒很有当年他当小队长时给战士们做战前动员的气势和鼓动劲儿,让村干和互助组长门听得热血沸腾,感觉跟着徐区长好像明天就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似的,一个个心潮澎湃。但是,当听到让踊跃发言时,一个个又彷徨四顾起来——眼下正值度荒期间,缺乏思想准备;再加之这几年灾荒频发,生产发展不好,感觉自己的互助组困难重重、步履艰难,还从来没有想过要转入合作社的事,一下子突然提出来感到茫然;还有,即使转为合作社,也是田大忠的“第一互助组”最有资格。所以会场一时冷清起来,他们都把眼睛望着田大忠。而此刻的田大忠估计会议是不需要自己发言的,所以正在想着那十几户救济粮接不上趟儿的解决办法呢,全然没有注意到会场上的情势。梁乡长贴着徐业的耳朵轻声问道:
“大家都在看着田大忠呢,是不是让田会长说说?”
徐业黑着脸没有回答。
会场难堪地冷着场。
“我来说两句!”忽然,从灯光照不到的墙角处传来田百怀的声音,打破了会场冷场的尴尬局面。田百怀是田百广互助组副组长,田百广很少过问互助组的事儿,所以通知他也来参加会议。徐业正自难堪着,忽然听见有人发言,救了场,不由得心中一喜,竟然产生一种被人救驾的感激之情,于是引颈张目,循着话音寻找着说话的人,想早点儿一睹其风采。可是,煤油灯如豆的灯火照不了太远,再加上满屋弥漫着烟草的烟雾,只能看到雾蒙蒙一片,未免有点儿失望。
“我来说两句,说得不对,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田百怀继续说道,“我听了徐区长的报告,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奔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接着他重复了农业合作化的意义,展望了合作化的美好前景,表达了自己成立合作社奔社会主义的迫切心情。最后宣誓似的大声说道:
“我田百怀,一名复员军人,一名回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荣誉军人,坚决响应徐区长的伟大号召,回去发动群众,带领我们互助组全体十一户人家,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走合作化路,尽快转为合作社,搞社会主义!”
徐业听完了田百怀的发言,不禁喜形于色,带头拍起巴掌来。回头悄声问梁乡长:“这个****的……噢,田百怀,个老子荣誉军人,是合作化的积极分子嘛,个老子骨干力量嘛!”梁乡长报以微笑。徐业对着会场说道:
“这个……田百怀个老子发言很好嘛!下面****接着发言!”
会场嗡嗡一阵又冷了场。戴指导员说道:
“刚才田百怀同志的发言很好,徐区长都表扬了。下面请大家继续踊跃发言!”过了一阵,仍没人发言,只好宣布散会。并且通知次日召开群众大会,由徐区长作合作化动员报告,田百怀作互助组代表发言。
经过半个月的宣传发动动员以及管干事的繁忙工作,赶在年底前芦荻村一下子成立了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田百怀为社长的胜利社,东头儿的永久社和西南场的灯塔社。对于这三个社的名字,相互之间还有过戏谑的调侃攻讦:永久社说灯塔社是“一蹬就塌了!”灯塔社说永久社是“原地踏步,永不前进”。
芦荻村三个合作社的成立,田大忠心里处于复杂状态:既高兴看到它们的成立,又替它们将面临的巨大困难前途未卜而担忧。他默默地祝愿三个合作社的乡亲们好运,真希望哪天清早起来徐区长能带领着拖拉机队、机械化队轰隆轰隆开进芦荻村。同时,他又为自己作为芦荻村的带头人而没能走在农业合作化的前列心底感到隐隐的歉疚和不安。
这年冬天特别冷,雪下得特别大,遍地积雪一尺多深,许多果树冻死了,南李家田明理嫏家南屋门右旁那棵生长多年的石榴树也冻死了,大槐树田家门口儿的大槐树也被厚厚的积雪压断了好几根枝丫。
田仁喜顺利讨完了账,提前缴纳了罚款310万的“下欠10万元”的欠款,感受到了无债一身轻的轻松,也感受到了“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其乐”的幸福,更感受到了生意顷刻化为乌有的创痛与悲哀,感受到了失去生意而又囊橐无余的彷徨于无奈。于是自我解嘲似地苦笑道:
“人说‘无官一身轻’,咱平民百姓没经受过那种变故,可是而今却感受到了‘无钱一身轻’了。如今穷光蛋一个,不担心土匪抢劫了,不担心丢了折了,开着门睡觉也不用防贼了,哪里累哪里歇,哪里困哪里卧,跟要饭的一样,心无牵挂,真是一身轻松呢!还有,生意丢了,不用起早贪黑赶集了,不愁着下雨刮风了,不愁着进货了,不愁着……哎,轻松之处可多了去了呢!像这大雪天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安享清闲了!”说着想着,不由得心底猛地涌出一股酸楚,双眼一下子模糊了……于是赶忙咬紧牙关,用力张大双眼,使劲眨动了几下,又把泪水强行收敛了回去。
这天清早,田仁喜放下饭碗,望着围在案板周围五个大小有序的可爱的小儿女,脸上绽放着笑容。理娘望着丈夫,不解地问道:
“您笑什么?”
“俺看咱这孩子真像一窝小燕子呢!”理娘很清楚,丈夫的回答是真实的,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幸福的流露。然而很快发现,丈夫微笑着的眼底渐渐涌现出无限的凄楚与无奈。理娘连忙把自己的目光从丈夫的脸上移开。田仁喜也连忙转身出了锅屋,回到南屋,以免把泪水洒在孩子面前。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田仁喜仰卧在里间大床上,任凭泪水恣意涌流。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就指靠这几亩地吗?指靠地,丰年尚可维持。那一家老小穿衣呢?孩子上学呢?遇到贱年呢?今年,秋季就颗粒无收啊……自家快要沦落到吃救济粮、逃荒要饭的地步了!想我昂藏七尺男儿,奔波半生,而今落了个两手空空!父亲已经年迈,孩子渐次长大……自己上无力赡养老父,中无力抚慰妻子,下无力抚养儿女……我,我愧为人子,愧为人夫,愧为人父……我田仁喜何以为人啊!苍天啊,俺该咋办?俺又能咋办呀?!田仁喜躺在床上,流了一阵子泪,伤了一阵子心,装着满腹的疑问,喊了一阵子苍天,终于慢慢冷静下来。他连忙坐了起来——不能躺下,那样又会惹起妻子的伤心和担忧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