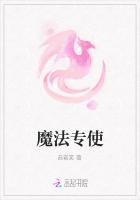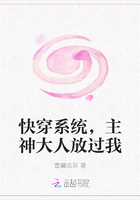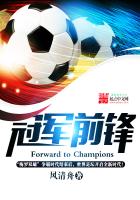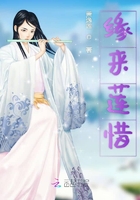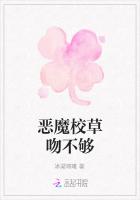偶婚制,或称对偶家庭,是指一男一女在长或短的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偶居生活的婚姻形式。它是群婚制向一夫一妻的个体婚制转变的过渡形态或中间环节,它产生于原始社会蒙昧时期和野蛮时期的交替阶段。对偶婚盛行于野蛮时代,即原始社会晚期。
妇女统治的基础
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
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18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
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
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新娘的同氏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赎金。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在夫妇不和时,双方的同氏族亲属便出面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而且,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
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18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庭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甚至不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或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妇女在克兰(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种妇女统治的发现,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妇女都担负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lady),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对偶家庭
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头脑中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看做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群婚看做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类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
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情况更加向前发展了。这样,我们就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数百种。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他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即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所谓婚姻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女子婚前自由
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却是一种通例。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说成是对违反古代神戒的赎罪,即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利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古时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莉塔庙里献身给男子;其他前亚细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许她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可遇到。为赎身而做出的赎罪牺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愈来愈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杂婚制,现在是姑娘的杂婚制;从前是在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区别地献身于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一定的人了。”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各民族、太平洋地区的岛民,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只要到过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曾经谈到一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绍同这一家的女儿认识时,他问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圭战争的军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她没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混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毫无愧悔地谈到她们的非婚生子女;这完全不是例外,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们……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却是一种通例。
初夜权
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存在于阿拉斯加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及其他民族中……
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只有个别地方是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一夫一妻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
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