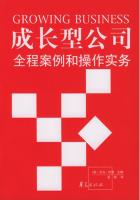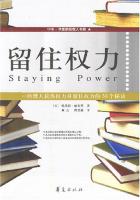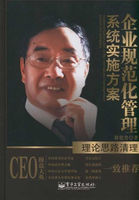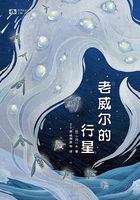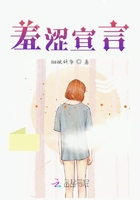年过二十,不为少矣,若再扶墙摩壁,役役于考卷截搭小题之中,将来时过而业仍不精,必有悔恨于失计者,不可不早图也。余当日实见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尝入泮,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腼颜也哉!此中误人终身多矣。温甫以世家之子弟,负过人之姿质,即使终不入泮,尚不至于饥饿,奈何亦以考卷误终身也?
他认为科举考试是误身害己的事情,一个人要是过了二十岁还在扶墙摩壁、汲汲于功名,从事于吊渡映带,那就会百业荒废,贻误终身。为了避免这种贻误终身的悲惨事件发生,曾国藩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读书目的。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做明理之君子,是曾国藩对子弟读书的要求,是他的读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是读书的根本所在,终极目标所在。那么他所说的明理,又是什么样的理呢?他指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明德、亲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读书必须做到《大学》所倡导的: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到这三个方面,才算是明理。只有做到这三方面,读书才有用,否则就是一个只知道识字的“牧猪奴”。朝廷用这样的人当官,也是用“牧猪奴”做官。读书不以考取功名为目的,而以追求学业上的修为、追求人格道德的修养、追求自立自强为目标。所以他要求子弟有正确的追求。他说: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弟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又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明理之外,读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修业。修业的目的是“卫身”。他说:
卫身莫大于谋食。农工商劳力以求食者也,士劳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禄于朝,教授于乡,或为传食之客,或为入幕之宾,皆须计其所业,足以得食而无愧。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食之得不得,穷通由天作主。予夺由人作主;业之精不精则由我做主。然吾未见业果精而终不得食者也。农果力耕,虽有饥馑,必有丰年;商果积货,虽有壅滞,必有通时;士果能精其业,安见其终不得科名哉?即终不得科名,又岂无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则特患业之不精耳。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与农工商是一样的,当官与教书是一样的,做传食之客与担任幕宾是一样的,方式是自立,目的是“求食”。“求食”,不是一般的获取食物,也不是不择手段的获取食物,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正当的职业、工作去获得养身、养家的资财。求食,强调的是自食其力,自立自强,不论是劳心还是劳力,不论是读书还是从事工农商,不论是做官还是教书,分工不同,目的一致,都是自立自强,自食其力。读书人以知识谋食。科名,则是获得食物的一个阶梯。只要努力,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终会有顺畅之时,即使最后得不到科名,也没有关系,还有其他的工作可以自食其力。这种对科名的理解,在当时来说,恐怕也只有曾国藩这样的卓越人物才有的。
当然,曾国藩并不否认科名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科名的意义除了求食之外,就是一种孝顺的手段。他说:“科名之所以可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子孙后代博得一个科名,目的就是让父母高兴而已。
修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艰苦的努力与付出,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法。曾国藩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值得研究与学习,一个是 “三有”学习法,一个是专注化学习法。“三有”就是有志、有识、有恒,他说:
故予从前限功课教诸弟,近来写信寄弟,从不另开课程,但教诸弟有恒而已。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炉,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一个人真正要学有所成,学有所得,必须要有志、识、恒。离开这三者,将会一事无成。志是志向、理想。一个读书人、一个领导者没有远大的理想与志向,就会“甘为下流”,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识就是学识、知识、才华。一个人要是满足于已知,那就会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坐井观天,河伯自大。恒,就是恒心,就是坚持。做一件,不做成不松手。做一下,停一下;浅尝辄止,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曾国藩虽然是在教育诸弟学习,其实也在教育他们怎样成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以前自己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教育弟弟们时,开了不少的功课单子;在北京结识了一批朋友,才学到了这一招。教给几个弟弟,和他们共勉。
与“三有”相匹配的一个学习方法,是专的问题。一个人学的专业不一定要很多,所谓“艺多不养身”,学多了学不精,不如专心专一学一样,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效果。
曾国藩教育诸弟,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敢于自我批评。这和他一贯的自我反省精神是一致的。领导者要使下级打心眼里信服,使下级主动、积极追随他,跟着他,不离不弃,就是要敢于自我批评。一个只批评下级的领导者,最后的结局往往不理想。哥哥教育弟弟,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老大自居,代替父母行使教育权,动辄打骂、责怪弟弟们,而对自己的教学方法,是否尽心尽力则不去反思。错误是弟弟们的,功劳是自己的。加之弟弟妹妹们对哥哥的缺点、缺陷看得比外人更加清楚,因此很难心服哥哥的教育。这样就容易出现弟弟们顶撞哥哥的事情来。这个问题,曾国藩是处理得相当好的。其显著的做法就是敢于自我批评。弟弟们对他有看法,有怨恨,他敢于承认、敢于批评自己;弟弟们有缺点、有错误、有不是,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指出。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当然能够得到弟弟们的理解与支持。
有一段时间,几个弟弟不想在家塾读书。他们认为在家不好读书,读不进书,就此与父亲发生冲突。他们想到衡阳、长沙等地去求学,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曾麟书开始不同意;国华、国葆曾经想到北京去,后来只有曾国荃去了,他们也有想法。种种原因,使他们心里不快,“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对此,曾国藩反省自己,批评自己有“五怨”,将责任扛到自己肩膀上。
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威克厥爱,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尝教弟一字,可怨二矣;临进京不肯带六弟,可怨三矣;不为弟另择外传,仅延丹阁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两弟不愿家居,而屡次信回,劝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难免内怀隐衷。
有心读书,在哪里都可以读;无心读书,在哪里都读不好书。曾国藩在北京,几个弟弟在家中,相隔何止千里,他们在家不听教训,读书不用功,根本原因主要还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些弟弟们看到自己的哥哥成了翰林,自豪感油然而生,骄傲心理也随之出现,读书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刻苦,对学习环境的要求也就更高了一些。我想这是曾国藩知道的,但是他没有说,而是反省自己,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对几个弟弟来说,应该是一种比面斥更加有效的教育方法。为了不打击、不压抑弟弟们的读书积极性,曾国藩一方面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祈求父亲允许他们外出求学;另一方面,积极筹措读书经费,帮助选择学校与老师,以满足弟弟们的要求。其用意之深,非一般人能够做得到。
教育弟弟,曾国藩既有耐心,又有原则。有耐心,就是经得起磨。1841年,曾国荃在北京跟着曾国藩读书。这位比哥哥小16岁的弟弟当时只有15岁,到北京去读书,想必是怀揣着好奇的心理去看看大世界的。读书只怕是个幌子。到北京之后,开始还好,几个月后,热情过了,读书毫无兴趣,只想回家,不看书,也不去客厅吃饭,问他什么原因,也不回答。“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弟弟的表现让曾国藩很担心。他不停地检讨自己:哪里有不友好的地方?哪里有不对的做法?又给他写诗,又给父母写信,让他一人回家,又不放心路上。这样磨了几个月,到第二年八月,用尽了一切办法,最后不得不安排他回家。有原则,就是不袒护弟弟的过错。开诚布公、坦坦荡荡是对领导者的基本要求,兄弟之间更应该如此。“凡兄弟有不是处,必须明言,万不可蓄疑于心。如我有不是,弟当明争婉讽。”对于弟弟曾国荃的过错,曾国藩中肯指出:“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弟有最坏之处,在于不知艰苦。”读书不用功,做事没有恒心,不知道生活的艰难。这些批评,对曾国荃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荃科场没有功名,最后官至两江总督,与曾国藩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教育弟弟成才上,曾国藩还主张弟弟们结交一批好的朋友。他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在乡下是很难有什么好的朋友的,他特别将自己知道的一些人介绍给弟弟们。省城中有一个姓丁的,曾国藩的朋友们都称赞他,所以曾国藩将他推荐给弟弟们。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在长沙读书的时候确实也结交了一批好朋友,像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罗罗山、杨岳斌、彭雪琴等。这些人对他们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