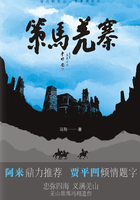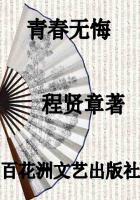这遍地是坟的园子,胆小的人不敢随意进入。耿就买来了上千只鸡,放养在林地里,不想那些鸡在他死去了的祖先们的照管下,食虫饮露,个个昂首挺胸,长得精神而壮硕。刚开始,他挑着它们四处卖,后来日子长了,那些吃惯了他的鸡的城里人,换了别人养的鸡吃,身上总长麻疹。这事经地方电视台报道后,都说那些鸡有药物残留,而耿的是绿色环保的,于是常有人开车到他家登门购买,几年下来,耿的家道殷实起来。
他请了几个帮工,都是些老头,有年轻的女孩子想到他那找事做,都被拒绝了,渐渐地人们都说他不喜欢女人。耿的业余爱好,就是在田野和山林中不停地游走,如果天气好,他甚至可以不知疲惫地游荡上一整天。谁也不理解他为何一再拒绝那些主动的被动的向他示好的女人们的追求和爱意,一直苦苦守着单身。而每在夜深人静时,总有一个女人顽固地占据着他的梦境,那就是叶儿!那个和他一同长大,一同上中学,然后让他真正做了男人的女人。当那些喜欢他的女人一个接着一个成了别人的妻,他也怀疑过,是不是自己的心理不正常,才一而再地拒绝了那么多的女人,因为那个女人仿佛就没真实地在这尘世存在过。
叶儿,他一次次在他们一起上学的道路上呼唤她。
叶儿,他或清醒或醉意熏熏地徘徊在田野山林,寻找他们坐过或躺过的草堆。
可年复一年,总不知她的消息,就连她的父母也不知她去了哪里。
耿有时也揣了很多的钱,想到附近的州城里碰运气,总想找到那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女人,每次总是徒劳无功。
有一次他满怀怨恨地在饭馆里将自己灌醉,再回车站的路上,他看到路边的小巷里亮着成排的粉红色的灯,站着些衣着暴露性感妖艳的女人,就多看了几眼。那些女人看到了目光呆滞的耿,就连推带拖地将他弄进了屋子里。耿只觉鼻子里塞满了浓郁的廉价香水味,眼前晃动着那些单薄的衣衫,半遮半掩欲藏还露的胸脯大腿,只觉得血脉贲张,心里像着了火,生命最原始的欲望被撩拨得近乎沸腾。可就在那女人将自己脱光,躺在他身下时,他想起了那个秋天午后的叶儿,想起那金黄色的散发着稻子香味的草堆,想起叶儿雪白的身子如瀑的黑发,它们都变成了一根根锥子,尖锐地刺痛了他的心,他飞快地穿上衣服,扔下了一叠钱,在那群女人的浪笑中,飞也似逃了出来。
4
当那一株老槐又一次挂满花儿的又一个夏天,衣着光鲜入时的叶儿悄然出现在她家的院子里。她四下打量,发现家里没人,就撬开自己家的房门,屋子里陈设如初,墙壁上挂着她小学中学的照片,没有因为她的离去而有所改变。她来不及慨叹,就爬上自己的床沉沉睡去,她从一个遥远的连她也忘记了名字的城市回来,汽车火车的颠簸,已经足足有一个星期没有睡了。
当田地里劳作了一天的父亲,扛着一大捆的柴草回家,看到洞开的房门和放在门边的行李箱,就扔下柴草冲上了楼,却看到床上躺着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穿着城里女人的衣服,抱着头的双手留着长长的指甲,上面画满了妖艳的花朵。他屏息站在那儿看了半晌,纳闷她怎么就躺在自己女儿的床上,直到那女人翻了个身,将脸对向他,他才看清是自己的叶儿。老人怏怏地下了楼,取下挂在墙上的旱烟杆,坐在门边吧嗒吧嗒地吸了半晌,才步履蹒跚地向田野走去,他是去告诉老伴,他们的女儿回来了!
“刘氏妹,刘氏妹……”
当他看到那叶儿的母亲从地里抬起头,不知为什么,他哭了。
那老女人好不容易听懂了他说的话,就扔下他,飞也似的冲回了家,只留他一个人在田野中生闷气,不知为什么,他心里隐隐觉得,那叶儿不回来也很好,因为凭直觉,他感到她已经不是他们的叶儿了。他觉得肺里塞塞的,就拼命地咳了起来,直到吐出了一团浓浓的东西,带着咸腥味,他在草地上用鞋将它摊开,是黑色的血。
那晚,他没等女儿醒来,就饭也不吃上床睡了去。
他听到叶儿的母亲上了女儿的楼房就没下来,接下来,还隐约传来了她们压抑着的抽泣。夜枭在暗处围着他的房子飞,翅膀扇动得空气呼呼作响。他感到心里发慌,身体极度虚弱,夜半时分,他发起了高烧,临近天明,她们将他送到了镇上的医院。
他在那儿连续打了几瓶点滴,才控制住了病情。
他每天昏沉沉的大睡,脑子里全是叶儿的身影:
她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她在襁褓中转动着眼睛,她牙牙学语,她扶着墙根走出的第一步,她穿着碎花衬衣乖巧的样儿,她的小学,她的中学……还有她那双总在眼前舞动着的生长着娇艳花朵的长指甲,它们像极了传说中的鬼魅妖魔,居住在老林洞穴深处,淫冶而邪恶,他真的不理解他们的女儿,为何变成了那个模样!
都是城市,他憎恨那个地方。
它们像白蚁窝那样堵塞而拥挤,到处是游动的车流和人群,它们传播病菌,到处以文明的名义播种欲望的种子,颠覆人们与生俱来的是非善恶标准,那个该死的物欲横流的地方!他将所有的怨恨转移到了城市的身上,在昏沉沉中日复一日地诅咒它,直到有人翻动着他的身子,并大声地叫他,他微微睁开眼,是女儿和她的母亲,她们的脸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下面,哀伤的眼神让他空荡荡的心里再次慢慢地填满了柔情,他将手伸向她们,她们是他的亲人!
5
耿这一段时间有事无事的总往叶儿家里跑,可叶儿有意无意地躲着他。
每次叶儿的父亲见了耿,就讪讪地一低头,自顾扛了把锄,下地干农活去。而母亲刘氏妹的脸上却溢满了近乎谄媚般的微笑,她指着那老头的背影说,别管他,他病还没好呢!她热情地为耿抬来凳子,安排他坐了,并拿出些地里产的新鲜果子拼命往耿手里塞。耿拗不过,只好有一句无一句地和她拉家常,一边用心倾听着屋子里的动静。通常,那个他想找的人,总是安静地坐在她的楼阁上,矜持如大家闺秀,不肯轻易露面。
好几次,耿好不容易从叶儿母亲身边得以抽身,就兴冲冲地去敲叶儿的门,那叶儿只将门打开一条缝,并不让他进去。他盯着那个穿着睡衣,浑身散发着慵懒魅惑香味的女人,心里涌起那个秋天相互缠绵的柔情,浑身如同猫抓般,却又无从接近。
“叶儿,叶儿,我是来和你商量婚礼的!”“我并没同意说要嫁给你!”那只手执拗地拉住门框。“全村子都知道了,你母亲都请先生来看了日子的!”他使劲扳她的手。“哼,那是你在死缠烂打!”那只手丝毫没有退步的迹象。
“你放开……”
“决不!”
他于是压低嗓子的央求,无效,就转而使劲掐她把门的手,那姑娘疼得泪眼婆娑,可还是不让他进门。母亲听到了楼上的争斗,就干咳着叫着叶儿的名字,提醒他们别忘了她的存在,耿只得悻悻地撤退。
“叶儿,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已经为你建了一个王国,你还要等什么啊?”
“耿,你别逼我……”
6
叶儿最近总是做梦,并且多与死亡有关。
有一晚她又梦到自己死去,这次不是坠落,而是被人用刀砍了,随意丢弃在一个陌生城市的街巷里,就伴随那些不断倾倒的腐烂菜叶,还有成堆的死猫死狗。从腐臭的垃圾堆中,蠕动着钻出来成群的蝇蛆,慢慢爬满了她的全身。她还看到自己丰盈的臀,被随风起舞的纸片拍打着,不知羞耻地裸露在阳光下,白晃晃地那么刺眼,招来了成群的男人驻足和围观……
她觉得那些死亡的梦已经变成了她的影子,追逐着她的身体和灵魂,从城市到乡村,从她知道和不知道的地方,直到她真正的死去。
曾几何时,她欣喜于自己的善于忘却。三年前,当她不声不响地从这个村庄出发,飘摇在不同的城市里,她很快就将那个穿着碎花布衬衣,说话轻声轻气的女孩忘掉,她忘掉了她的初恋,她的父母,忘掉了她的村庄,甚至她的名字。她也曾努力地想了很久,但大脑中总是一片茫然的空白,没办法就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冬香,男人叫的开心,她听着也觉得有趣。
“冬香,你长得真好看……”
他们的手和目光像毛虫般在她身上游走,一开始她脸红,恶心,浑身长鸡皮疙瘩。渐渐地,当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事发生,她不再挣扎,只狠狠地在那些手上掐上一个深深的指甲印,然后嫣然一笑:
“骗人,鬼话!”
有时为了度过那些难熬的夜晚,她甚至接受男人的邀请,到歌厅舞厅包房中去疯,她年轻,除了需要生存,还需要唱歌,需要红酒或白酒,需要异性的爱,需要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中发泄生存的压抑……
而每当那种近乎疯狂的放纵结束,浑身疲软的她,将那具曲线玲珑的身子,横陈在幽暗角落里的沙发上,泛着象牙白的面庞反射着红灯绿灯,目光散淡迷蒙,似乎身边的一切都变成了虚无。那已经是朵散发着魅惑气息的暗夜之花,在幽幽的音乐声中不知不觉地挥发着毒素,肆无忌惮地冲击矜持和道德组成的堤坝,直到它们分崩离析。
直到有一天早上,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过来,发现一束明亮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暖暖地照在自己的裸露的双乳上,它们温润鲜艳像两粒晶莹的玛瑙,这让她想起那个秋天金黄的稻草堆,想起了另一个叫耿的男人,还有那个让她窒息的村庄,她不如意的高考,以及无边无际没有目标和方向的逃遁,她甚至想起来自己就是那个喜欢穿碎花衬衣说话温婉的叶儿,而不是这个神情恍惚举止癫狂的冬香。
7
对于叶儿的变化,耿并不是不在意。他是这片高原上闭塞的山村长出来的芽儿啊,那些祖辈承袭的观念,早已经积淀成遍及脚下的每一寸黑土黄土,扎根在这样土地上的人们,关于饿死和失节的轻重,不用探究早已盖棺定论。尤其是女人的不贞,更常被视为家门的奇耻大辱。有时他脑海中也闪过叶儿父亲闪过的念头,那就是叶儿不回来也好,就让这个村庄用它惯有的方式去怀念那个穿碎花衬衣的女孩吧,怀念她温婉的笑,略带迷茫的顾盼,花儿一样的羞怯。对于耿而言,还有那个属于她和耿的秋天。
在叶儿逃遁的日子里,耿有时也会回到镇上他们上学的校园,他发现当年教他们的老师大多调走了,操场边他们在某一个劳动日栽下的法国梧桐,已经长成枝干繁茂的大树。他沿着环形跑道像当年一样慢跑,不时有叶儿般的女孩抱着书本迎面向他走来,这让他心里泛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就如同时光在和他开玩笑。
那个处处与书本为伴的叶儿,一点也不像他,她一直学业优异,理应有一个和她的祖辈们不一样的人生。而耿,早早地就明白命中注定是属于这块土地的,他要做的是除了学会识字,更重要的还要有一副强壮的身体。这种差距拉大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却拉近了叶儿和另一个叫做超的男孩的距离。
超出身镇上一个政府部门小干部家庭,他长得白净聪颖,充足的营养,严格的家教,让他一开始就和他七拼八凑的同学们,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这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田径场上,耿都是服气的。所以,除了周六回家和周日返校,他认为他理应保护这个邻家女孩外,其余的时间,他也认为她和超多待在那个空旷的教室里是有好处的。他这样想,也还隐藏着另一层难以启齿的秘密,那就是叶儿和超家境的悬殊,他们,也注定走不到一起的!
但让耿苦恼的是,他还是一天天从叶儿和超的眼神里,发现了他们隐藏于心底的好感,他们总是借口忘了一本书,或是为解一道复杂的几何题,毫不避讳地待在一起。带着那个季节特有的青涩,耿除了自惭形秽的退缩和避让之外,只有将对这个女孩的关注,深深埋在心底。一直到那个无法规避的七月过后,耿和叶儿怀着不一样的心境回到了他们共同的村庄。当耿开始忙碌地准备他的新家选址规划时,超却赶来向叶儿道别。听人说他考上了喜欢的大学选了他喜欢的专业,叶儿强作欢颜地为他祝福,却从此接连几天卧床不起。
那天,耿在他后来的新家的林地上转悠,他剥开了蒙在他祖先们石碑上的苔藓,发现那些斑驳的文字,最老的只能上溯到大明洪武三年,他正想把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告诉别人,却发现叶儿悄悄出现在他眼前。她步履蹒跚,带着长期失眠有着青黑的眼圈,明显地消瘦了许多。他忙心痛地将她带到一个稻草堆上坐下,然后默默地听她诉说她的烦恼,她想要的生活,还有她的无助和孤单。到了后来,叶儿终于停止了说话,她斜斜地躺卧在稻草堆上,眯着眼看了好一阵对面的远山,回头看耿,淡淡地对他说:
“哎,你在听我说话吗?”
耿忙点点头。
“你死人般就像我爸,他还会抽着烟,而你只会愣着!”
“那你要我怎么样呵?”
叶儿拉过他的手,将整个身子偎着他。
温软的触碰混合了稻草香,让耿大脑一片空白,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做点什么,但从内心升起无尽的悲悯,让他泪流满面。他可能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叫叶儿的女孩,最后将自己剥得一丝不挂,像举行宗教仪式般,将自己交给了那个喜欢她的男人,接着就梦幻般从他的世界里消失,却让他用一生的代价去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