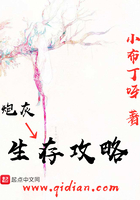“这大晚上的,你看个什么早梅,在说了这冬月的,天不过是那下午申时就开始擦黑了。”她一而再在而三的反驳自己的话,方太太不禁又道。
然夜文宇这心里气着的是,那夜瑶进来是一日不如一日,而且又是叫上官家给休了的,这水依然跟着她出去,莫不是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当下看了床上仍旧昏迷不醒的夜子轩,自觉地自己当初答应大哥二哥这件婚事,简直就是把子轩给害着了,心里此刻满是愧疚,好在如今还有些补救,这水依然竟然犯了女戒的这么多条,随便的一条,便能把她给休了。
不过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她,且不说她在子轩的病重期间不管不闻,自己出去逍遥,就单是跟她论这把家法棍子扔在地上的事情,所以当即便朝方太太吩咐道:“这样的女人,怎么还能待着我们永平公府里,先把她拉到院子里去,重则二十大棍,明日天一亮就将她送回七贤伯的家的别馆里去。”
方太太闻言,不禁高兴道:“我这就去办,老爷不必担心子轩的身体了。”这些可好,原先自己不能把这水依然赶出去,所以想委屈自己的那侄女来做子轩的妾室,眼下老爷发了话,自己的那侄女不就能名正言顺的做正室了么?而且还能正正规规的嫁娶,这样的话,自己也算是为娘家做了一件事情。
水依然有些诧异的看着夜文宇,就因为这个,他要打自己,而且听他的那口气,似乎要把让子轩把自己给休了,这怎么能行了,当下不由得道:“你们凭什么打我,我从来长得这么大,我父亲母亲还都没有碰过我呢,你们算是那门子的长辈,有什么资格来打我,而且这要休也不是你们说了的算,我是子轩的妻子,自然是他做主决定的道理,哪里是任由你们来说的。”
“凭什么?就凭你目无尊长,竟然说我们是哪门子的长辈,我告诉你,你嫁了子轩,那子轩是我的儿子,你就是媳妇,一个晚辈竟然这么跟着长辈的顶撞,还敢说凭什么?何况向来这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当娶贤德,如今你这个媳妇不闲不良不德,我们做长辈的,自然是有资格把你给休了,另给儿子求贤良。”夜文宇见她竟然连自己都顶撞了,当下也就不客气的回过她的话来。
“还有,你将我三房的家法棍子丢在地上,沾了地气,破坏我三房的运气,就冲这个,我也有权力把你给休了。”夜文宇又道。
水依然看那个红刺树棍子,一脸的不屑,“一根破棍子而已,你要是稀奇,我七贤伯府里多的是。”
破棍子?这还了得,当下方太太只喊着丫头道:“快来把这个泼妇给我押到外面的院子里去,将她的裙子给我撩起来,看我不打烂她。”
几个丫头一拥而上,便将水依然给捉住了,而她因先前就受了方太太的几棍子,现在身上还是一片片的火辣辣疼痛,突然被他们这么一围住,便一时间里找不到出路。在看着这些个丫头,大都是他们永平公府的家生丫头,当初自己嫁过来的时候,家里连个丫头都没有陪嫁过来的,现在自己虽然是收买了那身边的两三个丫头,可是她们现在见自己落了马,哪里来理会,各自都装作没有看见。
见几个丫头不过是将水依然围住,并没有去捉住她,便吼道:“你们都愣着做什么,赶紧去给我把她拉出去。”
丫头们闻言,也都不敢在冷着,抓的抓着水依然的手,捉的捉着她的腿,就这么把她给拖了出去。
水依然一面喊着,一面只骂道:“你们这些小蹄子,平日里我待你们那般的好,现在竟敢这样对待我,看你们还有没有一定的良心。”
只是她的喊叫无济于事,只觉得外面此刻正是西风阵阵的,吹得她一阵阵的颤抖着,突然被几个丫头强行的压倒在那院子里的玉石桌子上,只把她的胸给压得疼痛不已,而且脸也给那玉石桌子上的冷气冰得有些麻木起来。
不过这还才算是刚刚开始,只觉得下身一阵凉飕飕的,双腿忍不住并拢起来,厚厚的棉裙叫丫头们真的给掀了起来,那西北风像是刀一般的割着自己白嫩嫩的双腿。“哎呀!”的忍不住叫来声,冷得牙关打着冷颤。
那方太太见她的这身雪肤玉肌,还当真有些可惜,不过随之一想到她彻夜不归的,说不定都已经叫不少的男人给碰过了,现下只觉得一阵阵的肮脏,恶心不已,吩咐丫头道:“用那家法棍子打她的话,不免是把那棍子弄张了,你们去给我找根扁担来。”
那丫头闻言,心里一阵寒战,那扁担都是竹子做的,这么打下来,这水夫人还能有气么?不过还是不敢出声,便去找扁担来。
水依然挣扎着,扭头看着那根粗壮的扁担,不由得给下了一跳,只是这还没来得及喊一声,便觉得腚上一阵剧烈的疼痛感觉,身子抽搐来一下,便旧昏死了过去。
“太太,昏死过去了。”有个年纪小些的丫头见此,不由给吓得,生怕断了气。
可是那方太太却料定她是装的,只吩咐人去打来一桶冷水,浇在了她的身上。
水依然现在才感觉到什么叫做痛不欲生,不在心里,而在肉体上,身上全都给那凉水泼湿了,而腚上传来的疼痛不但没有一丝减少,反倒是越加的严重起来。想开口求饶,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而自己的身后,那方太太却为停止,一扁担一扁担的打下来,只庆幸这动手的是她,又老了又是个女人,力气终究不怎么大。
打到这最后,她也累了,打得也不重了,那水依然也叫她给打麻木了,又被这冷风吹着,早就已经失去了知觉,只觉得是木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