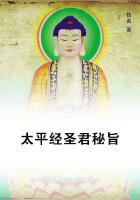60年代生人被称为“老帮菜”,80年代生人被称为“独一代”,而“幸运”的70年代生人,则被商家与媒体合谋冠以一大堆金光闪闪的头衔,“小资…‘BoBo…‘中产…‘新贵…‘雅皮”……新收到的杂志提供了如此犀利的浮世绘,我忍不住哑然失笑,试为自己归类——你算个“雅皮”吗?
在我身上,“雅皮”的外化符号似乎都具备:某男,28岁,工作于外企,有不错的薪水和看上去还不错的前途,喜欢优质生活,也有能力拥抱物质社会里曼妙的东东,例如,精品楼盘、15万以下的小轿车、名牌西服以及买昂贵的门票听音乐会的天籁。
可是,谁都说我不配担当这个美名。瞧,这人没出息地住在五环外的便宜小房子里,而没有听从楼书的召唤在CBD附近买下均价七八千一平方米的豪宅;骑车或坐公交车上下班,却不懂预支有车族的轻便快捷;更多时候在秀水、东单、动物园等服装市场买衣服,把15块钱一件的衬衫穿得津津有味儿。至于精神生活,也爱听音乐,不过不一定借助盛大的音乐厅,而是把cD的碟片当作管弦。
抠门儿、土老帽儿、未老先衰、消费高蹈时代的落伍者,面对“鄙夷”,我只是淡淡地一笑,对不起,所谓“时尚符号”再不能覆盖我的生活,我的心中,自有一根优柔的管弦在轻轻弹奏。
许多年前,我是个从小镇来的憨厚学子,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三,是唯一考上大学的人。爸爸送我来学校报到,从北京西站到西直门到西苑……一路倒车,城里人皱着眉头躲避我们的扁担与灰尘。四年期间,家里一共给了我一次学费,而我也只回了一趟家。学费咋办?
每个暑假,都有个瘦弱的孩子在学校的图书馆勤工俭学,倒腾那些厚重的图书。
我快乐地成长,想长成一棵顶天立地的男人树,这棵树的科目绝不叫“雅皮”,从根子里我就不属于“雅皮”。
然而,在北京一呆就是八年,谁能与“符号化”绝缘?刚毕业的我也曾迎着商家的预谋欣欣然前进。那时,对《第一次亲密接触》里的“轻舞飞扬”和“香水雨”念念不忘。于是,用第一个月工资5000大洋的五分之一,买了瓶法国香水。嗯,我要做个“优雅”男人,邂逅一个时尚女人。没事儿就在西四环附近转悠,把“观澜国际”、“郦城”、“世纪城”等楼盘一一看遍,房子的单价不得低于6500元,我对自己信誓旦旦,高价格等于好的人居环境。那时候我多想与大都市的同龄人合拍。想告诉“土著们”我有多么与众不同,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为自己打上各式各样醒目的物质标签。
环顾四周,同事美眉都如痴如醉抱着几米滋养性情,好,买,可在没人处说句真心话,我觉得这把年纪了还活在童话里,有点儿傻;看他们说微波炉的好处,好,买来热面包牛奶,后来我发现自己更热衷于跟在大爷大妈后面买豆浆油条;至于百货公司的活动更要支持了,买400多块的鞋返200多的券,回过头来想,羊毛出在羊身上,被涮了吧……轮流按照各个族群的行为模式复制生活,“小资”过后,然后是“雅皮”。
真的快乐?你确定吗?没人问我,包括我自己。
春节回家对时髦词汇向族群倒是绝口不提,拿些奖金给爸妈,他们露出意外的惊喜,聊起我熟悉的张叔叔,那个笑起来像弥勒佛的人。“多好的人啊,就这样没了。”爸爸摇头,天哪,张叔叔才四十出头而已。“得了癌症,单位垮了给不起医疗费,医院用担架把他抬出去,几个月人就没了。”“他的医保呢?难道他没有积蓄,没人管他救助他?”看着我惊诧的眼神,爸爸说:“傻儿子,穷人家这样的事情多了,有什么稀奇?”
那个春节并不平静,回京前一天,远房的一个老奶奶去世了,我们去送她。她的女儿、五十多岁的丽姨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啊,您临走前嘴里发出‘jiu jiu’的声,我以为喊的是孩子他舅,我糊涂啊,我不知道您喊的是‘救、救’。原谅我,不是我不肯救您啊,是家里实在没有钱,上不起医院……”远房的老奶奶,我只见过她一面而已,可那一天我哭了,因为被狠狠地撞击了,击中我的,是真实的残忍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落差!
当我在都市里为如何做“雅皮”、“雅皮应该用什么牌子的打火机、哪个厂家的笔记本电脑”而苦恼时,我轻易地忘掉了——我有两个哥哥,大哥在桥头卖米,米价的起伏让他忧心忡忡;二哥30岁才娶媳妇,现在犯愁出去打工还是在家喂鳝鱼。
小姨和姨父都下岗了,而他们的儿子,明年就要上大学,大学的费用有多高每个中国人都知道。
我妈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从来没有,她到了武汉都要晕车,大城市于她是新奇而又恐怖的地方……
做不做“雅皮”,如何做“雅皮”,至此还有什么关系呢?有闲散银子不是,自有更有意义的用途。再回到首都,我已得以穿越浮华的周遭,穿越写字楼的重重“枷锁”,看到更为广袤的深沉的北京,没有被广告、精美的包装、概念化的语汇覆盖的北京。那天,一家人的炒菜地点引起了我的好奇(同事们常常议论他们理想中的整体厨房,把预算制定在5000元到1万元不等),居然是在某个胡同的公共厕所门口。
女主人伸手去拿盐罐,旁边一个男人边系皮带边丢过来两个钢蹦儿,显然这家人靠看厕所过活。看,不做“雅皮”不做这个族那个族也能活,而且活得更自在、更朴素、更接近本心。
记得许多年前在火车站,分别时刻爸爸拍拍车窗说:“儿子,你要相信‘奋斗改变命运’是句真理。”我明白了,奋斗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命运、家族的命运,它指涉的外延,无限广大而苍茫。
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起喝咖啡
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
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非要到城市来?农村不很好吗?空气新鲜,又不像城市这么拥挤。”可是农村没有好的医疗条件,2003年,sARS好像让大家一夜之间发现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竟然如此落后,物质供应也不丰富,因为农民挣的钱少,贵一点儿的东西就买不起,所以商贩也不会进太多货。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中买得起等离子彩电的农民毕竟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农民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于是我要进城,要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你生下来就拥有的大城市户口。
考上大学是我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我要刻苦学习,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我在独木桥上奋勇搏杀,眼看着周围的同学一批批落马,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窄,我这个佼佼者心里不知是喜是忧。激烈的竞争让我不敢疏忽,除了学习功课,我无暇顾及业余爱好,学校也没有这些发展个人特长的课程。
进入高中的第一天,校长就告诉我们这三年只有一个目标——高考。
于是我披星戴月,早上5:30起床,晚上11:00睡觉,就连中秋节的晚上,我还在路灯下背政治题。
而你的升学压力要小得多,竞争不是那么激烈,功课也不是很沉重,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去读课外读物,去球场挥汗如雨,去野外享受蓝天白云。如果你不想那么辛苦去参加高考,只要成绩不是太差,你可以在高三时有机会获得保送名额,哪怕成绩忒差,也会被“扫”进一所本地三流大学,而那所三流大学我可能也要考到很高的分数才能进去,因为按地区分配的名额中留给上海本地的名额太多了。
我们的考卷一样我们的分数线却不一样,但是当我们都获得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所交的学费是一样的。每人每年6000元,4年下来光学费就要2.4万元,再加上住宿费每人每年1500元,还有书本教材费每年1000元、生活费每年4000元(只吃学校食堂),4年总共5万元。2003年上海某大学以“新建的松江校区环境优良”为由,将学费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这就意味着仅学费一项4年就要4万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总共6.6万元。6.6万元对于一个上海城市家庭来说也许算不上沉重的负担,可是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这简直是一辈子的积蓄。我的家乡在东部沿海开放省份,是一个农业大省,相比西部内陆省份应该说经济水平还算比较好,但一年辛苦劳作也剩不了几个钱。以供养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为例,除去各种日常必需开支,一个家庭每年最多积蓄3000元,那么6.6万元上大学的费用意味着22年的积蓄!前提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不能生大病,而且另一个孩子无论学习成绩多么优秀,都必须剥夺他上大学的权利,因为家里只能提供这么多钱。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东拼西凑加上助学贷款终于交齐了第一年的学费,看着那些握着录取通知书愁苦不堪、全家几近绝望的同学,我的心中真的不是滋味。教育产业化时代的大学招收的不仅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而且还要有富裕的家长。
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在大学校园里汲取知识的养分!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假期打工挣点生活费,我实在不忍心多拿父母一分钱,那每一分钱都是一滴汗珠掉在地上摔成八瓣挣来的血汗钱啊!
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我发现与我的同学相比我真是土得掉渣。
我不会作画,不会演奏乐器,不认识港台明星,没看过武侠小说,不认得MP3,不知道什么是walkman,为了弄明白营销管理课上讲的“仓储式超市”的概念,我在“麦德隆”好奇地看了一天,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丰富的商品。
我没摸过计算机,为此我花了半年时间泡在学校机房里学习你在中学里就学会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我的英语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我的发音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听不懂,这也不能怪我,我们家乡没有外教,老师自己都读不准,怎么可能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发音?基础没打好,我只能再花一年时间矫正我的发音。我真的很羡慕大城市的同学多才多艺,知识面那么广,而我只会读书,我的学生时代只有学习、考试、升学,因为只有考上大学,我才能来到你们中间,才能与你们一起学习,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
我可以忍受城市同学的嘲笑,可以几个星期不吃一份荤菜,可以周六周日全天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可以在周末自习回来的路上羡慕地看着校园舞厅里的成双成对,可以在寂寞无聊的深夜在操场上一圈圈地奔跑。我想有一天我毕业的时候,我能在这个大都市挣一份工资的时候,我会和你这个生长在都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做一个上海公民,而我的父母也会为我骄傲,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大上海工作!
终于毕业了,在上海工作难找,回到家乡更没有什么就业机会。
能幸运地在上海找到工作的应届本科生只有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水平,也许你认为这点钱应该够你零花的了,可是对我来说,我还要租房,还要交水电煤气电话费还要还助学贷款,还想给家里寄点钱让弟妹继续读书,剩下的钱只够我每顿吃盖浇饭,我还是不能与你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
如今的我在上海读完了硕士,现在有一份年薪七八万的工作。我奋斗了18年,现在终于可以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我已经融人到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中了,与周围的白领朋友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我无法忘记奋斗历程中那些艰苦的岁月,无法忘记那些曾经的同学和他们永远无法实现的夙愿。于是我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些是最典型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平民子弟奋斗历程的写照。每每看到正在同命运抗争的学子,我的心里总是会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怨天尤人,这个世界上公平是相对的,这并不可怕,但是对不公平视而不见是非常可怕的。我在上海读硕士的时候,曾经讨论过一个维达纸业的营销案例,我的一位当时曾有三年工作经验,现任一家中外合资公司人事行政经理的同学,提出一个方案:应该让维达纸业开发高档面巾纸产品推向9亿农民市场。我惊讶于她提出这个方案的勇气,当时我问她是否知道农民兄弟吃过饭后如何处理面部油腻,她疑惑地看着我,我用手背在两侧嘴角抹了两下,对如此不雅的动作她投以鄙夷神色。
在一次宏观经济学课上,我的另一同学大肆批判下岗工人和辍学务工务农的少年:“80%是由于他们自己不努力,年轻的时候不学会一门专长,所以现在下岗活该!那些学生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嘛,据说有很多学生一个暑假就能赚几千元,学费还用愁吗?”我的这位同学太不了解贫困地区农村了。
我是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我的同龄人正在逐渐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行为将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把这篇文章送给那些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和很久以前曾经吃过苦现在已经淡忘的人,关注社会下层,为了这个世界更公平些,我们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社会责任感驻留我们的头脑。
我花了18年时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