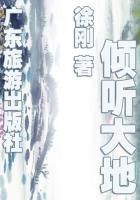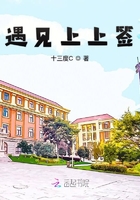浩然的《喜鹊登枝》在这一时间的发表,有刊物编辑选稿倾向稳妥的策略性机遇,即扶植工农兵新人,加之《喜鹊登枝》比较保险,不会导致编辑因用稿而犯政治错误,而且是别具风格的创作。万般磨炼写作意志后的浩然,在适当的时机里终于被伯乐发现。当然作为初学者,浩然这篇小说在艺术构思、语言文字,甚至语法方面都有缺陷,浩然在《巴人同志指导我学习创作》里深情地回忆巴人对他小说里的语法错误、错别字等进行细致修改。在浩然迈向文学之时,文坛已经出现了诸多描写农村新变革、新风貌的小说。值得一提的是,马烽的《一架弹花机》(1950年)、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1953年)、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1954年)、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年)、西戎的《麦收》(1956年)、骆宾基的《父女俩》(1956年)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小说的整体风格是关注发生在日常生活里的农村变化,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作家们并不执著于重大政治事件,而是倾心于用农间生活变化的琐事来表现农村新生活,选取的创作方法是将政治内容日常化。初来乍到闯入文学世界的浩然,凭着单纯、清新的作品增添了1956年百花齐放时刻的喜气。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百家争鸣的蓬勃景象迅猛跌入反"右"斗争中,政治形势的突然陡转,让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毫无思想准备,作家协会系统从"丁陈反党集团"开始,"右"派大帽子从天而降,冯雪峰、钟惦棐、艾青、萧军、秦兆阳、刘绍棠、丛维熙等等一大批作家接连被打成"右"派分子。祸从天降的劫后余生使很多作家变得小心翼翼,不再轻易抒发与政治条文不同的文学见解了。反"右"斗争之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的重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判断,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在剧烈的反"右"运动中,浩然这个初学者尚不可能受到波及。
在文坛惊惶自危的时候,他在《喜鹊登枝》之后一鼓作气地发了六个短篇,算是在文坛站住脚了。此时,浩然的文学生涯经历了一次重要"转机":已置身文学界的浩然凭着一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精神指导,不到两年时间便有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面对初步成果,浩然同时也陷入了模式化的创作中。以编辑身份希望帮助作者成长的萧也牧、巴人都针对浩然作品的"简单化"提出过建议。巴人在给浩然的回信里说道:"你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写出了人物的一些精神状态,但不够深刻。这里的关键在哪里?你总是以一些'外来的条件'使人物的'思想感情'突然转变。看不出他内心的斗争和变化的真实基础。......问题还在于对生活的理解还不够深入。" 萧也牧也指出,浩然纯歌颂式的写法会让他的创作路子越来越窄,要敢于深入生活复杂面。
假如是在平常年代,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契机,这些建议可以拓展作者的创作深度,使他在文学理解上迈入新境界。而反"右"阶级斗争的风暴,让浩然并没真的理解编辑的苦心。当然,在人人自危的时刻浩然也不敢冒险自毁"前途"。很快,萧也牧被打成右派,浩然也在惊恐中烧毁了以地富分子为主人公、尝试深入人性深度的《新春》手稿。事后,浩然心有余悸地自责犯糊涂,差点被一件脱离"正确路线"的作品毁了。浩然意识到唯有准确紧跟党的路线政策才是最稳妥的创作方向。这次事件,由于各种因素没能引导浩然反思自身创作的不足,反而促成浩然形成紧跟政治创作的路数。之后的六年里,浩然沿着最稳妥的路数,以稳健的创作方法紧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1962年前不断丰收短篇,有时一年内最多出版四本小说集。而反"右"运动后到1962年的文坛创作情况如何呢?
反"右"运动以后,随着1958年全国大跃进生产运动,文学界的激进倾向抬头。随后1960年初开始恢复生产,弥补大跃进带来的经济损失,文学界也相应在农村小说创作中开始反思"浮夸风"、"假大空"带来的弊端,提出写"中间人物"和深化"现实主义"。农村小说有了新的发展,细致入微、生动深入农民内心世界的优秀小说成果不断,像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等等,这些短长篇小说刻画了亘古未有的时代变化中各式农民的内心震撼。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提出目前文学创作写英雄,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人物",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亭面糊这样的人物给人印象深刻。
"写中间人物"对突破反"右"斗争造成的创作禁忌是一种调整,这时期农村小说创作中还出现了难得的"唱反调"、揭露现实真实的作品。李古北的《破案》和《奇迹》(1958年)正面披露大跃进中的"五风",讽刺、批评农村生产的浮夸风。欧阳山的《乡下奇人》(1960年)塑造了坚决抵制浮夸的生产小组长赵奇的形象。张庆田的《"老坚决"外转》(1962年)描写一个宁愿要粮食不要红旗、坚决抵制瞎指挥生产作风的农村基层干部甄仁。以上几篇小说在满天欢声叫好的年代不可多得。这种调整局面的时间维持不长。1963年底,政治形势又开始转向,之后掀起比反"右"更狂暴的阶级斗争风雨,成为1967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先声。就是在各个作家尽力发表真言,回避"大跃进"、"共产风"造成的写作压力的时候,浩然依然独自唱着单调的颂歌。六年的短篇小说经验积累,也使浩然在1962年之际有了新的想法,面对创作无法突破的苦闷和欲更上一层楼的创作追求,浩然迎来了文学生涯的第二次转机,出其不意地在这个阶段达到其创作的高峰。
(二)1962-1966年 (1)
前面提到,浩然初登文坛不久便意识到最稳妥的创作方法是准确贴合党的文艺政策走。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塑造积极向上的农民形象为浩然迎来文学第一阶段稳健的发展。如果照此下去,浩然最多成为混同一般农村作家之中、没有明显特点的普通作家,远没有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大家的名誉。是什么使他在1962年突然开启了创作的新阶段,创作出得到主流意识形态极力认可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艳阳天》?答案还是--准确贴合主流文艺政策的创作方法。
在浩然无力摆脱简单化写作苦恼的同时,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作品的着眼点都不在表达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与外界风雨大作的政治情况相比,作品反而为人们提供了精心绘制的一幅幅农村百态图,像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西戎的《赖大嫂》等。在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作家参与时代生活,表现火热的斗争场景;另一方面,大部分作品中的"斗争"和"农村"却是分离的,书写农村民间世俗生活的时候,作品生机勃勃,而写阶级斗争的时候则比较生硬,两部分不能做到有机融合。这是因为阶级斗争观念还没有完全成为作家们认识生活的角度。阶级斗争与日常生活怎么在小说内部有机融合起来,而不只是外部的粘连,成为60年代阶级斗争路线中作家们的困扰,而此时对浩然却是一个"契机"。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重提"阶级斗争"。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这使文学领域在召开新桥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后有所缓和的局面又骤然紧张起来。然而,政治的影响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作家的写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有自己难以移除的创作理念和惯性思维,所以,1962年前后仍然有不少吸引读者的文学作品。但对于正处于精神苦闷的浩然来说,这一口号的提出无疑给他带来惊天的影响。我们来看1974年12月浩然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编剧干部进修班座谈会"上做的题为《生活与创作》报告中一段发自肺腑的感言:
我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以前,写了将近一百个短篇,应当说是不少的。但是,可以说几乎全部作品都是写一般的新人新事的。从拿起笔来一直到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这样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从主观上说,我要很好地配合党的政治运动,想使自己的笔能够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怎样服务,怎么能够更好地配合政治运动,或者说怎么样写好新人新事,我确实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是这条路子却越走越窄。为什么呢?生活不熟悉吗?自己认为还是比较熟悉的。过去长期地工作在基层,以后也没有间断跟生活的联系。主要问题是因为我没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生活、认识世界。所以尽管承认生活是源泉,却没有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质和主流的东西。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自己才恍然大悟,开始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写了《艳阳天》。相对地讲,这部小说抓住了生活的一些本质和主流的东西,使自己对生活的深入进了一步,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鲜明的政策口号,让浩然恍然大悟,瞬间在惯有的政策创作路数中拾起一个新的方向性指示,《艳阳天》就是浩然获得这一创作精神支点后酝酿出的长篇。相比《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更能贴合主流文艺政策要求。他完全信服文学工具论的创作理念,使他的考虑不同于赵树理、柳青,浩然开始真正学会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生活、构思小说了。我们不得不惊奇在阶级斗争口号掀起不久,还没成为其他小说家认识角度的时候,浩然已经完全按照阶级斗争的路数创作出长篇小说,这种"贴合"无人能及。浩然曾自我称叹,《艳阳天》是他第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事实上,这大概也是全中国最早以反映农村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了。那么即使是在同类反映阶级斗争题材的小说中,浩然的创作能成为"样本"、"典范",他又怎样做到紧贴主流文艺政策的呢?
浩然通过相应的创作方法,把政治观念转化为生动的文学表达,采用了以下手法:
第一,突出人物,把那些跟人物关系不大的细节减少或者删除了,如风景描写等;也删去一些次要人物的历史介绍;能用行动表达人物内心活动的地方,就把静止的内心描写简略了一些。第二,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矛盾线,让这条线索更清楚明白。因此在写正面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地方,还加了些笔墨,而反面人物形象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第三,故事结构上也稍有改变,把倒插笔的情节,尽量扭顺当了,让它有头有尾;某一件事儿正在发生着,又被另一件事儿岔开的地方,也挪动一下,让它连贯一气,免得看着看着摸不着头脑。同时,还按照一位生产干部同志的意见,给每一节加上小标题,起点内容提要的作用。第四,语言也稍加润色,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腔"和作者出来在一旁发议论的地方,只要我发现了,就全改过来。
从这四点措施来看,浩然敏感地早于其他作家"贴准"文艺政策之处可归结为:一,极好地演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主流文艺创作手法,甚至最早践行了1968年"文革"中盛行的"三突出"手法;二,在结构和语言上,适应广大工农兵读者的阅读心理和水平,去除知识分子文艺腔。
在主流文艺政策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也是争议较大的文艺方法,虽1949年后经全国三次文代会不断巩固其主流文艺政策的地位,但在实际创作领域少有作家能成功地演绎它。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任文化部长的周扬代表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的最高原则;1958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到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将其正式认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唯一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直接地说,这个创作方法在文学效应上强调的不是认识现实,而在于改造现实,实际上就是用党政政策话语从意识形态上教育和改造人民,将他们改造成改变现实的力量。究其本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要求塑造工农兵新人形象,政党提出的直接针对性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