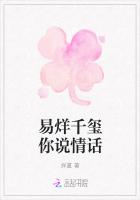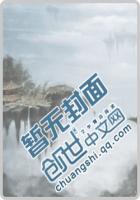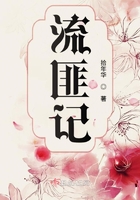令人感慨的是,依靠集体经济的实力和多年积累的经验,集体经济显示出的优势十分巨大:经过几十年大规模的农田建设,全乡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全乡统一治理沙岗,利用农业科技改良土壤,集体统一规划田地、树林、公路、电路,发展水利化、机械化和电气化,实现了田园化批量统一种植;并且实行"以工补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利用工业企业注入的资金,购置了大量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收割机、播种机等机械工具,从春种到秋收,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减轻人力、物力的重复投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此外,还依靠集体科技研发能力,各生产队对传统农业、畜牧业等技术加以改进,发挥土地统一经营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成无公害葡萄、优质种子田、出口鸭梨等大型专业化生产基地。由于实行专业分工,发挥规模效益,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都提高了,经济效益成倍增加。同时,周家庄人还陆续建起一批规模不等的社办工业企业,不但解决本乡供货需求,还经受住了市场考验,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占领全国市场。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集体化周家庄保留下这样的宗旨:"不让一户贫困,不让一家后退,不让一人掉队,不让一人受罪,团结互助劳动,共享幸福滋润。"周家庄呈现的是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兴旺景象。村容整洁,绿树成荫,水泥路面。全乡统一施工,为每户建立住宅楼。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周家庄还有多项公共福利:对65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津贴;65岁以上、连续工作20年以上的农村干部实行退休制,发放退休金;独生子女的老人,发放养老津贴;社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款由集体负担;社员享受合作社免费供应的自来水;社员重病,集体给予补助。
这些保障标准虽然还不高,但覆盖面广,惠及众人。周家庄还依靠集体的力量,实行义务教育,全乡入学率、普及率均达到100%。此外,社员们组织了自己的文学会、体育协会等文化娱乐组织,集体还出资建文化中心站、灯光体育场、农民文化宫、图书阅览室等设施。在周家庄,我们看到的是党风正、民风淳、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周家庄人均1万多元的年收入或许不算很高,但由于是集体生产,各家不用花钱购置农业生产资料,分红后基本上就是纯收入。加之合作社福利多,农民的生活较之其他地方富裕不少。在这里,大家共同劳动,共享成果。"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农村集体化经济在这里不是理想,而是现实的实践。
所以,任何一个历史道路都不是绝对正确的,都可以反复、对抗,甚至杂糅融合,现在的历史就是交织的状态。我们目前很难单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答复一段历史进程的对错。回头来看文学,我们说文学不是提供途经的参考书,它的魅力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心灵共振与交流。作品反映的是作家的内心世界,代表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和感受。在浩然的文学生涯里,他就是这样去感受这个世界的,他喜欢美德化的人与世界,向往人际的单纯、和谐,眷念集体化、大公无私的人群精神,作家始终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来看待世界。
从这个层面看浩然的文学,我们可以最大化地理解他笔下保持不变的集体化信仰不仅仅是作家对农村生产方式的个人理解,更是他以文学创作者的情感抒发着自我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无论这种情怀深邃与否,他的真诚与坚守在如今尔虞我诈、过分看重经济得失的现实生活里都显得分外可贵,他对美好人心的坚守多少使得某些形式纷呈、内质空乏的文学写作显得惭愧。联系如今的底层写作,当我们看到当下农民的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时候,不能不感慨农村的改革道路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历史的相互交织使我们知道没有一条绝对正确的道路,但不管途经何处,人与人之间的美善情感不可遗弃,作为一种人性,比诸向着更高生活水准追逐的原始驱动力,同样分量沉沉。而浩然的文学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反思与警醒。
作为人生情感的追求,我们理解浩然的文学,但是,我们看待作家、作品要深入肌理,不可以抽象地、理想化地对待世界和人事,要深入作品去看浩然创作中有没有围绕自我理想,故意忽视现实里血淋淋的矛盾。在十七年文学里,作家有过这样的弊病;在新时期文学里,置时代改革中的现实问题于不顾,同样是对艺术的损伤。经过反思的浩然在新时期文学里表现出独特的一面:迎着改革新风,他对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肯定,但面对旧意识形态的全面崩溃,他又体现出无限眷念,作品内在的矛盾性极有意味地展现出七八十年代新旧意识形态交替之际的复杂性。在经历社会大变动后的新时期作家格局里,浩然是独特而孤独的,在年龄以及创作理念上,他没有"归来一代"作家们劫后余生的控诉与诉苦,较之新时期崛起的新生作家,他根深蒂固的历史因袭又使他无法一开始就卷入思想解放的洪流,无拘无束地畅游在新时代。
眷念与不得不跟进的矛盾心态,造就了浩然在这一时期的独特性。长篇小说《苍生》是一个极好地体现了浩然问题的文本。主人公田保根的形象塑造生动地展现了作家的更新与眷念心态。这种有点新潮、浮浪的农民子弟是作家在十七年文学里批驳的对象,但鬼灵精怪、思维活跃的保根却成为浩然在新时期文学里的理想给予人物,这种转变显示出作家的跟进。当表现这个人物独闯人生、打破传统农民守旧生活模式情节的时候,浩然有足够的艺术本领使这个人物栩栩如生,但是,当浩然想赋予这个人物打败腐败干部邱志国,带领田家庄走集体化道路的使命的时候,这个人物开始大段大段地思考和讨论改革,说着某些理念化的套语,多少给人一种空泛的感觉,和之前个人闯荡的情节相比,语言显得冗长、浮泛,人物形象也有些概念化了。
它的致命的艺术缺陷是,保根作为关键人物,对于田家庄的改革,却始终是模糊的,他的反抗方式是利用他人找到邱志国的罪状,在远处"指挥作战",对改革成功的红旗大队只是投以羡慕的思考,远没有身体力行的能力,更多的是代表作者发出诸多感慨和肯定。与有声有色开创自己人生道路的保根相比,这个背负集体化道路理想的保根显得黯然乏力。尤其是当他拒绝女友陈耀华丰厚的物质生活诱惑的时候,他的回答多少有些不近人情,甚至不食人间烟火,按照改革初期青年人的躁动性情,保根应该是孙少平(《平凡的世界》)、门门(《鸡窝洼人家》)、金狗(《浮躁》)这样的"走出去"青年,但浩然让保根出城闯荡,最后返回,就是为了实现作者的理想坚守:努力创造集体共同富裕生活,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永不放弃努力。我们尊重作家的创作理念,但从艺术上把握,一个艺术家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感受人的痛苦,触摸人的现实,不可为了某些理念忽略现实的深度,过分理念化的作品始终有损艺术性。
与保根这个人物形象相比,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塑造的青年闯荡者孙少平的形象,值得我们重视。和保根一样,孙少平也是一个不甘心农村落后的青年,他的出走和保根类似,动机都不在于金钱或荣誉,而是反抗农村人命运的局限性。顺着孙少平的性格发展,我们在路遥笔下感受到的是这个人物坚实的人生力量和青春激情。同样是出走,孙少平更多为着人生价值精神追逐。作为一名受过现代文化教育的农村知识青年,他渴望打破农村局限,追求更高的人生精神境界,并一直脚踏实地地行走着。首先,孙少平面临的是穷苦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战胜自卑,坦然靠知识获得个人自尊。在黄原揽工的日子,因为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他主动选择饥寒、劳累作为自己找寻价值的基本考验,当为求生存辗转在社会底层时,孙少平逐渐超越物质层面,由苦难激发出坚忍的意志,进入人格自我磨砺的精神层面。
矿场的井下生活,彻底让孙少平找到自我的人生意义,自给、自足、善待自己和他人、承担生命的苦难、把握人生的幸福,使孙少平青春激情的追寻走进成熟人生阅历的回归。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改革之初的、不满农村命运、不断奋斗、饱受艰辛的真实生命个体。从挨饿的学生时代到黄原揽工的艰苦磨砺再到矿山的井下生活,孙少平不辞艰辛,为的是不断挑战人生、实现自我。他虽没有清晰的人生蓝图,但打破传统生活方式,寻找自我价值和对待苦难的坚韧,较之浩然笔下田保根身上带有的轻喜剧色彩,更能体现路遥艺术思考的深邃和对现实生活的触及力。孙少平的性格设置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他就是我们身边共同呼吸着的人物,从当时小说发表引发的社会关注、掀起的青年人共鸣,到至今读者阅读后的唏嘘不已,充分说明小说触及了社会真相,作家以真切的感受说出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
第四节 浩然"变"与"不变"的启示 (2)
从80年代何士光《乡场上》的受压者冯幺爸的一声呐喊,张一弓《黑娃照相》里黑娃在相机前的自信,到《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明确的自我价值追寻,不断体现出新时期文学里农民子弟开始主动走出乡村传统文化束缚,滋生了强烈的个性意识,以个人奋斗的形式,试图改变传统落后的命运。对于这种真实的需求,路遥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思考,作家停留在单一的道德美善上否定这种奋斗,而是真实地抓住历史变动,写出历史发展与道德冲突中,奋发者的苦楚与坚实、躁动与迷惑。
相比而言,浩然依然停留在自我理想化创作中,对人物的设计摆脱不了对个人理念的铺演。理念化的表达使田保根性格不大统一,前后就像油和水,始终没能完全融合,人物艺术形象受到损伤。为理想而执著写作,不可避免地让浩然小说失去了与现实真实触碰的机会,在80年代新旧意识形态交替之际,浩然不乏独特地真诚保留了"去政治化"时代后,对集体化道路、人际美善的向往与执著,这种保留个人历史思考、又不得不与时俱进的矛盾心态,在浩然文本里留下了"与众不同"的笔迹。我们既尊重作家的真诚思考,看到这份眷念对当下农村建设的意义,也看到这种矛盾心态对艺术造成的损伤。评价浩然的集体化眷恋,最终还是要用文学感受说话。
二、"大众化"与"农民化"文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