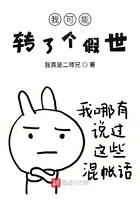1.悲剧
一生追求革命,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作为活跃在“五四”以后我国二三十年代主要的进步文学社团“狂飙”社主将高长虹,却曾被历史无情地淹没,逐步从文坛以致整个社会生活中退出和消失,如此落寞结束曾经辉煌过的生命。犹如彗星式的天才而陨落,却似昙花一现令人惋惜。青苗在《忆高长虹》一文中深切地抒发了他对高长虹悲剧结局的惋惜之情:“高长虹是中华民族中稀有之人,类似‘吉普赛人’那样贫苦的流浪者,在海外为衣食而奔波的华工中不难找到,但在高级知识分子和声望卓著的作家中却是很难找到的。从这个角度看,高长虹确是一位‘怪杰’。每次当我到五台山看到‘孤魂野子’的神龛时,我总不由地把‘孤魂野子’这位叛逆之神与高长虹相比……‘孤魂野子’是佛徒中的‘屈原’。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以托孤野子之名写出一部仿‘离骚’,以象征主义的诗作寄托我对高长虹的思念……你真像一条雨后的长虹,从蔚蓝色的天际消逝了!”执迷不悟的凛然,心照不宣的释然。如金庸笔下黄药师,非商纣,薄礼周,视礼教为粪土;任情纵性,大有魏晋名士风骨;生性哂然不拘行迹,在歧路与正途间跋涉,真情自在人演绎成悲剧,成为“孤魂野神”,邂逅与等待都是宿命式的凄凉,生命体上留下了一道道永恒的皴裂伤痕。
高长虹的悲剧与作为戏剧概念定义的悲剧不同。戏剧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让人看”。而高长虹的人生悲剧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却含有对他人生价值与人生经历的一定意义的肯定。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高长虹人生悲剧结局的原因与意义作一些探讨,阐述几点笔者见解。
高长虹的个性、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的怪僻和独异,也不能仅仅用他信奉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无政府等思想上的原因来解释,而是带有一定的心理与生理上的变异与病态倾向。这种变异与病态,是由于主观个性与客观环境矛盾冲突与自我意识的冲动所致。比如20年代中期与他同属《莽原》中人的台静农,始终说“此公狂妄自大,精神不大正常的样子。”高长虹晚年住招待所,周围有人称他“疯子”、“神经病”,不过这些到底是言犹在耳传还是真的,难以判断。读他的文集,间或也有些奇怪荒谬的言论,“真实的性行为必是时常需要变易的”。“倒是杂交可以暂且引出一部分人来直到光明的路上去。”(《论杂交》)还有些怪异、跳跃性的思维,也表现在作品中:“青春?青冢!面包!贵妇之肉?梦呢?爱呢?一切或无!杀……杀……杀!”还有他写的《猫眼睛》“唉唉,成功无名,自然之子,时间之神呵!”这样的诗,实在有些怪诞,令人费解。但从总体上看,高长虹创作的思路和文字都还是清晰的。他平时生活行为中表现出的也多属怪,而不是“疯”。有些人对他的评说是属误解。那些误解的不适之词,使高长虹形成精神上的压力与打击,一定程度上束缚与限制了他的思想行动,甚至窒息了他的才智。这是造成他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但切不可否认,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是造成高长虹悲剧的主要原因。
有的人认为,高长虹的悲剧是个性性格的悲剧,有一定道理,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个性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认识问题。
高长虹1941年到延安,写了大量作品,文史哲无所不涉,但因主观认识脱离当时实际,所写作品不合时宜,被采用的很少。1942年底完成专著《什么是法国法西斯蒂》,因某些观点同斯大林不一致,未能面世。这是否完全是高长虹的错误,不可武断,但至少表现他思想有一定的主观片面倾向。抗战胜利后高长虹同毛泽东谈话时,直言不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不欢而散。观点与斯大林不一致给斯大林提意见。这些当时的曲直是非很难判断,但因此而使高长虹受到了压制,由于他当时不能正确认识对待那些来自外在的客观人和事,使他的创作锋芒与锐气大减。30年代末,曾受“抢救运动”打击之后,情绪消沉,极少参加社会活动,这都是挫伤他锐气的客观原因。由于高长虹自我意识异常强烈,自信过度,奇特怪异,造成他思想上的盲动性和排他性,对来自外在客观的人和事,缺乏冷静思考,不管对与错,多半难以面对与接受,自觉不自觉地走上孤独人生路。正如高长虹在《反应》中写道:“我不愿苟同于人们的清高”。“我便成了目空一切了。”他在《震动一环》结尾写道:“冰变成最阴沉的冷。我的热达到最高潮。我纵跃在空中,无阻碍无牵挂,地球倒掉在我面前。我将—个没有睡觉的天文学家在报告书上写了下面两行字:——某月某夜,一彗星由地球侧面而驰出,在空中作一长蛇舞,火裂自灭,幸未伤及地球。”这段描述,正是高长虹的狂傲个性的象征,是他个性特色的画像。
高长虹在延安,拒绝接受文联职务,拒绝参加毛泽东邀请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而断然离开延安,这正是他走向人生悲剧的关键一步,这正是他思想上盲目性与排他性的集中表现。由于他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对社会发展道路,发展方向发展形势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对毛泽东革命文艺的方向与深远意义缺乏深刻认识,轻率妄自拒绝。
当时最使他不能接受的是,那场“抢救运动”。高长虹住在延安山上最高一层窑洞中,对山下发生的事一目了然,一批批干部被抓去,一声声逼供信声音传来……这使他无法理解。当时的那些现象,正反映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高长虹对此,缺乏深刻的认识。更幼稚的是他在重庆时几次找孔祥熙的儿子,建议开金矿。说明他对革命形势发展方向缺乏正确判断,导致他离开延安离开革命营垒而走向人生孤独境地。
至于高长虹当时他说他是搞经济的,是研究经济的,文艺只是他的业余活动。他说这话,是有一定原因的。他在外国游历数年,深深领悟到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深感中国经济落后,他说:“全国解放后,很需要建设资金,东北有金矿,我要去开采金矿,开采出来于国家建设有用。”当然,不可否认发展经济对国家是很重要,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面临的是即将投降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獗,再加上反动封建主义统治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影响,在这样复杂而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当时摆在共产党与广大人民大众面前的紧迫革命任务是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推翻三座大山而夺取政权,彻底解放劳苦大众,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要夺取和建立政权首先必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这就离不开革命的文艺,离不开革命舆论,而高长虹当时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其深层次实质问题,是高长虹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缺乏清醒认识。而这些问题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与学说,所以,高长虹在延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还不深刻,尚未达到明晰境地,由于他去过日本与欧洲许多国家,企图吸收西方的东西,但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愿望是好的,想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状况,但没有政权何以实现呢?在当时,“经济救国论”只是一种幻想。所以,他最后只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离开延安,逐渐走上孤独境地,甚至酿成人生悲剧。看来,造成高长虹人生悲剧的原因,除了个性之外,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他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缺乏深刻的认识。要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落后经济状况,必须推翻旧中国反动统治,必须从根本上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高长虹对此也缺乏明晰认识,他在《献给自然的女儿》诗中这样说:“我愿有一个超人时代,人类如兄弟,地球一家取消了一切障碍!人类如兄弟。”这句话,除了含有企盼和谐世界的美好意愿之外,但不可排除是他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的表现。当时,在延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积习,也不可能因为它是革命圣地就被吓得无影无踪。相反,那些简单粗暴、作风不民主、生活特殊化、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各种形形色色的表现都是封建阶级意识的表现。高长虹对此难以面对,难以理解,这就是阶级斗争意识与观念淡薄的表现,这正是与周围外界客观环境难以融洽的原因之一,也是他悲剧的深层原因。
生命本来就是一条曲线,高长虹却更蜿蜒曲折,哀是酝酿,悲是释放,天命攸归,却可无奈。高长虹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生。一生追求,一生挺立跋涉,表现出他的个性价值与人格力量。正如尼采所认为,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高长虹悲剧背后也隐含着对他人生的某些肯定。其实,“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让人看”这一悲剧定义,也含有对人生价值与经历的一些肯定。然而,高长虹的社会价值却没有真正实现。这是人们的遗憾,更是他的遗憾。他的很多作品和文学成就不为社会承认。后来,在鲁迅研究领域内,遭到贬损,成了一个“恩将仇报”的反面形象。“文革”中更被诬为“反动文人”,殃及子孙,这可以说是他人生悲剧的延续。然而,高长虹对自己的悲剧结局,似乎早有预料,而毫不介意。被冷落,被遗忘,他无半点牢骚。在他心目中,没有丝毫宠辱得失观念。他虽历经风霜,却正正堂堂,虽崎岖险阻,却潇潇洒洒。不了解高长虹的人,似乎还有些反感。如果真正潜心读读他的文著,你会觉得是一种崇高而圣洁的享受,因为他能开阔你的眼界,丰富你的智慧,会使你摆脱幼稚的狭隘与世俗的卑见而走向理智的成熟与高雅的认识境界。正如高长虹说的那样:“批评狂飙运动的人……必须读过狂飙运动的刊物。”但也不可否认,他文著中表现的一些非理性的情感冲动与强烈的主观自我意识倾向是不可取的,因此而造成的悲剧结局是令后人从中应记取的教训,这也正是他悲剧人生的意义所在。
2.“人性决定命运”。高长虹在《死的舞曲》诗中有讲坛:“让你的行为呵执行你的命运。”可见他在骨子里还是有一些“宿命”的色彩。高长虹个性执拗一根筋,而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与尼采“超人”哲学思想影响而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浅滩泥沼有一定关系,最终淹没了自己,成为文学史上的悲剧人物。高长虹的倔强执拗个性累遭受挫之后,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表现了他自我意识的强烈膨胀。在他一些散文中的“我”、“他”、“我们”、“N”几乎都是作者的投影,他们的喜怒哀乐、悲苦哀鸣,也都属于高长虹自己。他在《生的跃动》、《游离》、《从地狱到天堂》、《生命在什么地方》、《噩梦》等都是他追求幻梦,深厚主观感情的宣泄,也是他执拗个性的表现。他写的《曙》,不再用象征手法,全书浸透着孤寂、凄凉、悲怆的情调,哀叹人世经历之苦涩,这预示着他的悲剧结局。逐渐成为“五四”精神的落伍者。他的一生正如他在《现实的现实》中描写的“独行者”一样:“是在一个夜里,有一个踽踽独行,像在寻找着什么。他从此处望到彼处,从彼处望到此处。”这正是他的自画像。
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观念人”。高长虹正是一个典型的“观念人”。他的独立人格,独立思想,是可贵的,但知识分子如果脱离社会脱离人民大众将一事无成,这正是高长虹人生悲剧中应吸取的沉痛教训。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著名“皮毛”理论认为,知识分子是“毛”,他们过去依附在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两张皮,后来,只能依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艾思奇也曾经在解放初期形象地比喻说,知识分子就像块砖,要么砌到新社会的墙里,要么就被扔掉甚至打碎。高长虹似乎就是那块被打碎的砖,在这方面高长虹的教训是沉痛的,当他在延安时,如果识时务,合时宜,认清形势辨明方向,一定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文艺战士与文学家思想家。个性固执往往是产生于思想认识的错误。当然本真人性的作用也不可否认,生性难移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前面已经从某种程度也赞同苏童那样肯定基本人性自然主义意象主义作家,前面已经提到过,高长虹的创作思想,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注重人自然率性与生物本能的自然主义观点,他曾说,“我是一个主张自然主义的人”。自然主义的根本要义是在追求人生真相,这虽然是对人本真人性的肯定,但不可否认,自然主义带有一定的变相主观主义倾向,这也是高长虹人生悲剧思想认识上的根源。这也是他个性独立的一点负面表现。根据毛泽东的“皮毛”之说观点,知识分子的独立也必须有坚固的社会根基作基础。高长虹的悲剧的发生也正由于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高长虹是典型的“思想观念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思想观念的孕育、产生和传播是需要相当自由独立的空间的,而思想还有一种可能冒犯权势或大众的危险,无论是说出一种始则被权力有意掩盖,后又得到大众惰性支持而继续遮蔽的历史真相,或者追求一种自我认定的与主流有别的观念真理,都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观念人”永远会竞争与斗争,但最好能有一种稀薄群体意识,高长虹正是缺乏这点,他缺乏“惺惺惜惺惺”的感情——在双方互相争斗中,应当不损害对方的人格,不能因言论观点的对立而把对方置于死地而消灭。(当然,这样做似乎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道德人格)这也正是从高长虹悲剧人生中应记取的教训,也是他悲剧意义的所在。正如他在《艺术是人类的行为》写道:“当一个艺术家为人类而奋斗而感到失败的悲哀而犹奋斗到底的时候,他便写出伟大的悲剧来。”这正是他悲剧人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人生悲剧的快慰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