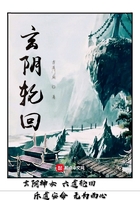只听一旁的两个男子在那叨续着:“这霜厨的菜啊真是汴梁城第一啊,赛皇宫里的厨子,但却不知道这个霜厨是啥模样子?是老是少,是男是女?”
“依我看啊!肯定是个大老爷们才有这火候,也不可能是年轻小子吧!”
“你说的也有道理,说不定还是个徐娘半老的美娇娘,渍渍!既是掌厨又是掌柜,哈哈!娶回家的话,那叫一个美得。”
“得瑟了吧你!若是个美娇娘,也是拾掇不到你,你个二百五何德何能啊!霜厨应该是个活寡妇,哈就像这盘鱼肉冬丝一样香脆柔滑。”
狄印扭头白了这两人一眼,咂巴咂巴了一下嘴,道:“什么破厨子?不就烧个菜吗?还霜厨!哼那是因为葛厨没来这地盘煞你威风呢。”说着说着也夹了一块糖醋熘鱼肉尝了尝,愣了一下,瞳孔放大,愕道:“这是糖醋熘鱼吗?怎么味道不一样,形状也和葛木头煮的不一样啊!”
“好像不是用鲤鱼做的.....”扈力钦双眼直勾勾的盯着那鱼,思索着说。
葛贯亭截口道:“是白鲢,还是活白鲢,我都不敢用这么鲜活的鱼煮,所以味道自然差很多的。”
“这位彬彬有礼的哥哥你说错了,其实是草鱼,是鲜活的鱼不假,茭白去皮洗净,又放了特质的西域香料,加上中火炮制,并且把鱼丁挂匀蛋清糊,待沸收浓卤汁,所以口感些微清淡。”说话之人却是当日在街边酒肆所看到的花裙小女孩,她浅浅一笑,双眸巧动,却是有着十分的自信与思量。
葛贯亭却不以为然,思索道:“说得对,所以这盘菜应该叫糖醋熘鱼丁才是,食材便宜,却能吃出极富极贵之味,真不简单,看来这个霜厨是个细心如针的女孩子吧。”
狄印大惑不解,渍渍地说:“这你也知道啊葛木头。”
葛贯亭双目如炬,心中自有一把自信之尺,用肯定地口吻说:“做法如此细心周到,我万分不及她也,确是女孩不假。”
“说的没错啊,我也觉得是女孩,肯定是漂亮可爱的女孩,不然怎么烧出如此周到的菜,这名字确实叫糖醋熘鱼丁,哥哥果然是高手中的高手。”说着花裙女孩白了狄印一眼,冷冷地说:“哪像有些粗人,吃饭没个吃样就算了,连大脑都被油渍堵塞了,哼哼!”
狄印气得鼻孔张得老大,一时哭一时笑,手指着她,气道:“这模样倒挺像一个人的,不过那家伙比你漂亮多了,牙尖嘴利的是镶了金牙还铜齿,满嘴的猪腥子,我呸!”
花裙女孩满脸厌恶之色,嗔道:“这么恶心的猪头男,还是没彬哥哥好。”说着说着躲到葛贯亭后头。
葛贯亭也是护着花裙女孩,对狄印道:“阿印!你是大男人,怎么可以欺负小妹妹呢?”
“好啊你个葛木头,怎么帮起外人来了,我们可是穿同条裤子长大的。”狄印略显妒忌地说,话中却是醋味浓烈。
只见扈力钦跑了出来,他见狄印与一位小丫头吵闹,实在看不下去,连忙上前劝说道:“好啦!别闹啦,好男不和女斗,更何况还是个小女孩呢。”
狄印抱胸,哼了一声,却是不在多言,花裙女孩甚是得意,笑道:“黑痣哥哥虽然丑了点,但后半句话说得比你这猪腥哥哥说得对多了,你不是好男,才和女斗。”说罢,朝狄印吐了吐舌头。
这时一个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三八来岁的妇女,手捧热气袅袅,从吐口而出的烧酒,这应该就是汴梁酒家所专门称为“酒博士”的“焌糟嫂嫂”,每次都为已空杯的客人满上好酒,但是焌糟嫂嫂径自走来,差点把酒洒了狄印一身。
狄印一脸骇然,闪身躲过,又看那冒着烟的烧酒水洒在地上,热烟直冒的样子,暗想:“这酒该有多烫啊?幸好躲得快,不然就成烧猪了。”想着想着,庆幸之余,也不免怒火陡生,加这火爆脾气一上心头,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狄印当下指着她那个“焌糟嫂嫂”鼻梁,破口大骂道:“你想烫死我啊臭母猪头!”
“焌糟嫂嫂”气得鼻子都快歪了,浓眉陡立,樱嘴骤圆,嗔道:“死小子你敢骂老娘,你才母猪头,不给你点颜色,不知道老娘我的厉害。”说罢便老腰枝一扭,手中烧酒壶往前一撩,滚烫的酒水瞬间喷洒而出。
扈力钦见状,一脚将旁边桌子一翻,踢到了狄印面前,烧酒水尽洒在那格挡的桌面上,狄印朝扈力钦会意一笑,立时提起腿来。
“喯”地一声。
狄印竟用自己的腿劈开了这个玉桌子,力道之强,令众人骇然,劈开桌子之时,内劲十足,绿光一闪,似乎有人暗中借其很强的灵力助他。
扈力钦察觉有异,扭头看着四周之人,却见一个灰衣斗笠男子掩面离开,想必此人定是认识了狄印,有意挑起争端,扈力钦刚要追上去时,那人早已被人来人往的人流给淹没了。
狄印气势大盛,挥拳直直打向早已愣住的“焌糟嫂嫂”的面门,葛贯亭立时稳稳接住了那一拳头,包于自己的掌心。
那一拳没有内劲,亦没有先前劈开桌子的绿光暗力,只有厚实的拳风和一股杀猪般的蛮劲,暗想狄印却也是不把“焌糟嫂嫂”放在眼里,可能也是方才那一腿子的威风,让狄印有些得意忘形了,所以对“焌糟嫂嫂”的怒气早已消了大半。
况且以狄印的性格也不至于痛下杀手,只是想来这一拳威吓威吓这不知死活的婆娘罢了。
葛贯亭灵力虽然深厚,却只猜到这其中缘由的七八分,又怕狄印玩过头了,本就心善的自己岂有不阻止的道理,他劝说道:“阿印!不要打人,毕竟这位大嫂也不是故意的,你是个男人,岂能如此这般的小气呢!”
花裙女孩抱胸一副得意自信的表情,白了狄印一眼,从鼻子冷哼道:“哼!他压根不是个男人,就知道欺负老弱妇孺咯!”
“臭丫头你这是在承认自己是孺了吧哈哈哈!”狄印不怒反笑,调侃了起来,连连大笑。
花裙女孩双手叉腰,哼了一声,不再理会狄印。
葛贯亭朝“焌糟嫂嫂”深深鞠了一躬,作揖歉然道:“这么大姐!我替我兄弟赔不是了,请您别放在心上。”
“焌糟嫂嫂”狠狠瞪了狄印一眼,看向葛贯亭,立即眉开眼笑,嗲里嗲气地说:“哎呦!还是这位小哥说话有礼貌,哪能啊?不生气不生气,嫂子我可犯不着和个死猪头计较。”
狄印面色铁青,却也是一脸无奈,嗔道:“葛木头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帮谁到底,明明是这个老母猪差点烫到我了,你却帮她啊你。”
扈力钦拍了拍狄印厚实的肩膀,温然道:“阿印!确实不该和女子一般计较,况且我们不是没饭钱吗?理亏着呢。”他小声附耳对狄印说,狄印一脸无奈,摆了摆手,也不说话,但脸上表情已经帮他说了一些啥似的。
“焌糟嫂嫂”笑逐颜开,咯咯笑道:“我才不和小娃子胡闹呢,算了算了,喝了我的烧酒就当赔罪。”说罢倒了一碗烧酒递到狄印面前,狄印毫不在乎,似乎喝下这碗酒,他就会颜面扫地似的,他下巴抬得高高的,嘴里微微吐出:“哼”的声音。
谁料不胜酒力的葛贯亭竟然率先拿过那碗烧酒,爽快地一饮而尽,洒脱自然,毫无儒士的酸礼腐节和扭扭妮妮。
一碗酒,湿了衣襟,却换来了潇洒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