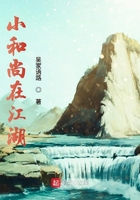这处境,他不会去乞求这些人能多有仁慈,这姿态,居高临下,此行就是为了瞧一眼圈养的家禽突然生落得如何而已。
“要不是你心高气傲,桀骜不驯,这等天资奇才何只为我们两族争光。”游离走入,盛气凌人。
伸手探向他腹部,激起抵抗,将手臂往墙面一甩,砸出声响,吞声忍泪,折射进大夏公爵的眼中。
地堡中,游离身后,释放瞳术的黑风衣加剧了威力,带走了他突然间产生的丝丝异动。
“只耗了两天功夫就把‘帝台棋’石磨到这种程度,你让为兄我赞赏的同时敬佩。”
戴上手套,再从袖中掏出一颗更大的‘帝台棋’石头,抛动跟前,等着他反应。
御牧瞪大了眼睛,眼前的恐惧,‘帝台棋’石的恐惧。
为时已迟,游离一手扣向喉部,捻挤,喉道大通,鹅卵大小的‘帝台棋’石投其咽下。
御牧的意识间,一座大山压下,癫痫卧地,呕心抽肠。
“熬过这漫长的几年,磨平了你骄性,便是重新走出这囚笼之时。”游离道,看向一边舅舅大夏霸,僵着脸,起身。
身后父母兄弟始终冷眼旁观,富贵浮云。
一行几人往外走,游离把倒下的‘熏华草’油灯扶起,口中作念,添加油脂,扶到禁槛外,御牧伸手碰不见的地方,再道;
“让它长生不息吧,对安抚你燥热的脾性有着绝佳的帮助。”
说罢点火,族人皆捂上鼻腔。
“灵儿在哪里!”御牧突然喊道,一字一吻。
惊到生父公爵大夏霸,惊慌在一瞬间让游离瞧得明明白白,急张拘諸。
“她死了!”游离道。
公爵惴惴不安,一腔戏弄就等着这一刻,这个心高气傲的生父愧对亲子,大杀锐气。
“死了!”御牧惊乍而起,斗气冲天,犀利得能将眼前众人拦腰尽斩。
躁起惊吓到姑姑大夏宛,踉跄后退,扶住丈夫。
身后两个胞弟‘大夏御胤’,‘大夏御天’气打一处来,踹穿牢门怒冲上前,扛起御牧一顿胖揍,打萎下去,趴卧在地。
再啐两口,瞧着再无反应。
游离点头,示意适可而止,转身点亮杵灯,御牧缓够了劲,拼足一口气依然不依不饶。
“我...再问...呼...”断续,换气,忍受。
”一遍,呼...”强忍;“灵儿...她到底在....哪里!”誓不罢休。
胞兄弟‘大夏御胤’,‘大夏御天’揎拳捋袖,游离拦住了去路。
“让他想,让他好好感受,让他一个人静静地感受,没有什么能比孤独中,一个人默默偿赎罪行更能惩戒,今天到此为止!”
游离慢条斯理,装模作样。
众人认为这远比肉刑之苦还能折磨一个人,便也妥协,退开几步,审视脚下这身狼狈,捂上鼻子。
灯亮了,任凭御牧在身后如何叫唤,众人便是不应不答,默然离去。
独留生父公爵大夏霸静在暗处,细细打量,御牧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绝路,百感交集。
安静有时会给烦躁者制造恐惧,更无需加以施压,亲生子,长嫡子大夏御牧终于疯了,公爵目睹了这漫长的经过。
御牧一天天在变化,堕落,血浓于身,爱子一步步自暴自弃,走向绝望,几度尝试自杀。
即便是自杀,也成奢求,游离总会在紧要关头出现,救下御牧,鬼门关前几遭来回,求生不得渡死不能。
御牧陷入空无际望的痴呆中。
如此过了无数个天干日,一个天干日按十天循环计算,度过一段颓废时日,丧如家犬。
数隔几天被喂以‘帝台棋’石,压制修仙体,灌以汤浆保证肉身不腐灭。
事迹传开,这一身瘦骨伶仃,毫无生气,到了一叶知秋的地步,探视放得松宽,城主月支天罡走了进来。
“你族中之事我无权管辖,但是这孩子经受得足够多了,选个吉辰放出来吧!”
天罡先生打量着年轻人,与昨日相比,天壤之别。
“哼!”游离啐了一口,牢什古子,挫骨扬灰,道;
“他要是还有骨气就自己站起来,负荆请罪,重新拥有该得的地位和名号,还是这幅模样,废其仙体,逐其名号,残其身,扔到山海大陆某个山脉与野人为居。”
嗤之以鼻,始终铁石肠心。
一旁生父,公爵被游离这番态度彻底激怒。
不明白游离会如此无情义,哪怕是对待一只畜生,颓废至此,即便没有可怜之心也不需施多惩戒。
这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哪容得你外甥一手专断,且这是如何回事?
如何干预都不能扰到眼前两人,纹丝不受影响,咄咄怪事。
“毕竟也是年轻,血气方刚呐!”城主怜惜身脚下人儿,昔日之比,马瘦毛长,十分可惜。
二人攀谈着离开了囚牢,公爵疾言厉色,生子御牧完全不是人样,却突然用着带血的手指在地面画了一个叉。
... ...
现实中,地堡里。
被带入幻境的公爵流露出真性情,情凄意切,悲不自胜。
游离重新排列了往事回忆,将以往情境中的自己,换成了公爵的长嫡子,表兄弟大夏御牧。
诚然,他看到了不一样的待遇,那或许还压在心头的某些悬念,舅舅会为了上阁名誉,大中至正。
诚然,透过游离的眼睛,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轻蔑,怨恨,铁了心要加以折磨。
入夜,看守的几个发现今日天象怪异,彗星南扫。
一股凄烈的寒流自北向南,带来一阵白雪,粉了半个昆仑山。
昆仑城上阁,大夏居府中,养在庭院辟邪的‘孟槐猪’。
原本生活在天乾卦位,北部第一山脉,黄河东岸的谯明山中,因其慧根灵性,适用于庭院看护,避邪凶灾,此刻正群集急躁地拱着沙土,敌视来者。
出现了几只飞禽闲信跺步,四翅,六眼,三脚,乃是生活在山海天地风巽卦位,北部第三山脉的景山上,命‘酸与鸟’。
这是凶邪禽类,一旦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要发生恐怖的事件。
一众‘孟槐猪’嚎起,四面八方聚拢而来,猪多势众,驱赶火红色的‘酸与鸟’,逼至角落。
‘酸与鸟’化成一束烈焰,尖鸣刺耳。
周旋上居府夜空,瞧中最高那一座阁楼,滚成火球,击破大门,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书房内。
朝着主位席的夫妇狰狞作势,一腔通鸣,令人发指,转瞬即逝。
留下几支在燃烧的羽发,化作一缕缕灰烬扬在大夏一族族长,公爵‘大夏霸’和妻子‘月支天芷’的脚下。
夫妇一人正端看着书籍,一人正拨弄着食果,感受这一诡异现象,肉跳心惊。
这是山海天地的征兆异禽,只有当恐怖事情要发生的时候它们才会出现。
而今天这势头,完全是冲着夫妇二人而来。
如此冲突,眼前被击穿的大门,一团火焰正滚滚在烧,浮想联翩,大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