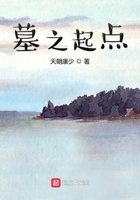次日清晨,萧奕峥轻装简行的出了尚都城,一人一马一赵信。
出城时,他对着笑呵呵迎上来的城门官说:“本王的印章还未收回。以此印章为凭,他日王妃出城,不得阻拦。”
城门官连连称是。
两人马不停蹄的赶路,直至晚间抵达驿站方才休息。用完晚膳,赵信去了马厩给两匹马喂食。萧奕峥也晃了过来。他急忙说:“殿下先去休息吧。”
萧奕峥恍若未闻,卷着稻草,抚摸着追尘的马背。“今年的端阳节,又没能让你在京中过。”他语气温和,带着歉意。
“我无事,这孑然一身的,在哪过都一样。倒是殿下,这刚刚新婚,便与王妃分开了。”
萧奕峥笑笑,也未搭话。
赵信觉得他心情不错,便继续道:“殿下今年许是收到了王妃的荷包?”
萧奕峥动作一顿,旋即摇了摇头。
赵信一脸不可思议,脱口而出:“嗯?怎会?”他与萧奕峥一起出入朝廷,闯荡江湖,情意自不是一般主仆可比。他在其面前也从来不做情绪的修饰隐藏。“月影曾问过我,殿下喜欢什么花色。我以为是王妃做荷包要用到。”
萧奕峥皱眉看向他:“月影问你?”
赵信点了点头,又觉得是不是自己说错了话,补充道:“昨日见殿下袖子有一荷包,我还以为……”他迅速住了口,觉得自己一错再错,便赶忙继续埋头给马儿喂草。
“那是皇后娘娘亲手缝制的。”萧奕峥淡淡道。
“是了,以往端阳节,皇后都会亲手给殿下做荷包。” 赵信附和。
萧奕峥唇角挂着淡淡的笑,想起宫中午宴后,萧奕和递上这个荷包,郑重交代的话:“六弟,此去西南,道阻且长,与以往任何时候你出京的情况都不同。父皇,母后,我这心都是悬着的。今年的荷包,母后想着你已成婚本不用再做的,但听到你要去西南的消息,还是替你做了一个,希望能祛灾避难。只是怕你媳妇多想,觉着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便让我私下给你了。”
他动容的接过荷包,“娘娘的手艺全尚都城也是数一数二的。让娘娘别担心。”
“你千万小心,我在尚都等你好消息。”萧奕和仍是一脸担忧。
他舒朗一笑,点了点头。
皇后制作的荷包精致小巧,他昨夜回到正则苑时,拿着那个荷包,满脑子回荡着太玄琴铿锵有力的豪迈之音,心里却想着:能奏出这般琴音的手做出的荷包该是什么样?
他对自己说,也不应十分在意未收到她亲手缝制的荷包,毕竟以他们的关系,做不做的也不好强求。但是内心却有说不出的期待与失落。尤其是今日一早,他看到清溪一身国朝大礼时才会着的王妃正装骄傲的立在王府门前送他远行时,这份不知道夹杂了什么情感的期待与失落尤胜。
他对她笑,她也报以了同样的笑容。两人什么话都未说。此时,想起朝阳下灿烂绚烂的笑容,萧奕峥却觉得也无需说什么话了,甚至关于荷包不荷包的那些想法也是自己矫情了。她本就不是一个后宅之中的普通女子。
“赵信,今晚好好睡。这接下来的,咱们得打仗了!” 他微一仰头,语气铿然。
这一夜,尚都城广王府书房内灯火通明。广王爷正在奋笔疾书。这几日,豫王,湘王是轮流来他府内做说客。无非就是让他配合朝廷,在家安心养老。事实上,他被削了军权后,并未给西南军去过任何消息。他也知道,自己怕是已被监视,任何消息出了王府,也便进了皇宫。但即便不下任何命令,西南军会如何,他都有百分百把握。即便湘王告诉他萧奕峥在养心殿那一番分析应对言论以及皇帝派他去了西南,他心道小六子倒是机灵,但真的丝毫不担心。 他在西南经营数十年,岂是他小六子轻易能撼动的。
“你到底怎么想的?究竟想干什么?”豫王问他。
他想干什么?他本不想干什么!他不甘心!不甘心被人莫名其妙夺了兵权,不甘心替朝廷立了功劳反倒被弹劾,不甘心他西南军的将士受委屈。
被豫王说烦了。他冒出一句:“大哥,你做老大的,这些年也憋屈吧。要不,咱一起干事业。”
这番话吓得豫王爷立即冒了冷汗,急忙告辞,再也未登过广王府的大门。
豫王第二日早早便进了宫,原原本本的将这番话报告给你皇帝。
萧辙听完,笑容宽和,反倒安慰他道:“九弟那脾气,发发牢骚也是有的,有些话当不得真。朕若真计较起来,那又得牵扯多少人。只要九弟不有所行动,朕也愿意睁只眼闭只眼。大哥,有些话也听过就算吧。”
豫王爷连连道是。
而此时广王的这封信却真正是写给副帅徐永胜的,叮嘱他无论如何不得进京。这封信,他也有渠道送出。信写完,他琢磨起大理寺监牢内的那几个人,看来有些事还是心软不得。
萧奕峥离开尚都后,清溪的日子尽比此前更加忙碌起来。
许是怕她孤单,皇后经常招她入宫相陪,游园赏花,品茗打牌,泛舟下棋,还次次活动都不一样,但次次皇后总是要提到六郎这,六郎那。就这样,她知道了萧奕峥少时的很多趣事。比如,练功也会偷懒被武装元师傅处罚却用书房老师那套说辞绕的师傅觉得处罚他是自己的错;比如为了让四公主出嫁前可以潇洒恣意一回,怂恿四公主换了百姓衣服,偷偷带着她出宫玩了一天才回来,被皇帝知道后大发雷霆,自己死活护着四姐姐,平生第一次被皇帝打了棍子。再比如,替听梦出头,教训总是欺负她的小内侍,但偏偏不以皇子的身份,而是换了夜行衣蒙着面行事。还振振有词道:“若用皇子身份压人,也不公平。他不知我是皇子,也可还手,剩了败了与人无尤。……
皇后说着这些往事,总是笑的见眉不见眼。清溪也觉有趣,心道这从小就不是个安稳的主啊,难怪尚都城容不下他那颗总要往外跑的心。
她进宫次数多了,便也和后宫中的娘娘们熟了,看上去也都是和善之人。只一人,她觉得有些特别。便是那位肖似孝懿皇后的念妃娘娘。她甚少出席宫中女眷的聚会,偶尔露脸,也甚少有笑意,整个人就那么安静无表情的坐着,和整个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而大家似乎也都不大在意,似乎也都习以为常。
只是清溪觉得这位念妃娘娘看自己的次数似乎多了些。她时常也捕捉到她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她问过沈桐:“念妃娘娘性情一直如此吗?”
沈桐凑在她的耳边说:“据说,她对着父皇和自己亲生的七皇帝也是这幅表情。”
“冷美人。” 清溪总结道。
沈桐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不解道:“可我总觉得作为母亲,是不是也太冷了点。对着父皇嘛,可以理解,毕竟也差了不少岁。可儿子是亲生的啊,总该热络热络。想想七皇弟才八岁,还是孩子。孩子们,谁不喜欢母亲宠溺爱护。”随即,她又笑道:“我这才一个多月,都觉着母子连心,想着以后该怎么对他好。”她的笑容满是即将为人母的喜悦与安慰。
清溪也笑的宁和。“这个孩子可是会万千宠爱于一身的。”
沈桐抚摸着肚子,抬头问她:“你担心六弟吗?”
清溪一顿,笑容未收,点了点头。
“算日子,他也到西南了。只是还没听太子提过有什么消息传回。”
清溪颔首,前日哥哥来过王府,也与她说了些事。“我既想有消息,又想无消息。”她收了笑容,低声道。
沈桐握了握她的手,柔声道:“太子说,父皇肯让他去,定是有万全准备的。”
清溪叹了一声:“我倒是愿意能帮他些什么。”
晚间,清溪从宫中返回王府。刚进王府,忠伯便迎了上来,先是行礼问候,后是禀报道:“今日府上来了一位访客,说是要求见王妃。门卫们本不大在意,问其哪府哪位,所谓何事。但对方却说,是殿下的江湖朋友,有殿下所赠信物为证,求见王妃。若王妃不见,恐会耽误大事。门卫们便不敢怠慢,层层传报给了我,我去见了访客,其手中却有王爷在外使用的小印。我问所谓何事,对方坚持要见到王妃才能说。但王妃今日不再府内,来客便说明日一早便登府,若王妃不见,便不会再来。”
“哦?”清溪皱眉。萧奕峥的江湖朋友为何要见自己?又所谓何事。似想起了什么,她突然问:“是男是女?”
忠伯面露难色,还是迅速低声回答:“是位姑娘。”
清溪面色一松,闭了闭眼,叹了一气,半晌道:“明日一早,那位姑娘若是来了,请她进来,去前厅等我。不得怠慢,好生招待。”
忠伯领命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