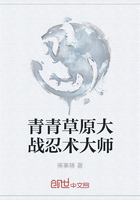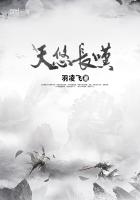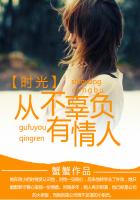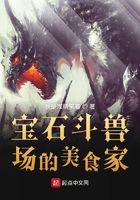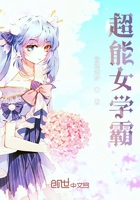在商周的铜器铭饰中,“亚”字也是一个极为神秘的符号,其涵义也很难确解。在甲骨文及金文中,“亚”与“巫”二字的外形极其相似,“亚”的古音读yu‘巫”读wu,语音也很接近,二者实际是同源语。也就是说“亚”与“巫”曾经表达同样的内容。据何新先生考证,“亚”字就是“宇”字,是一种表示四方上下的空间概念。这种空间概念,表示古人对宏大的空间的理解。所以,何新得出结论:“亚字本形,可能来源于象征太阳的十字。太阳光芒四射分布宇宙,所以推广而有宇宙之义”。笔者认为,这个结论虽然大胆,但却有理有据。
古金文中的“皇”字和“昊”字都与太阳崇拜密切相关。古文字学家王国维认为,金文中的皇字,像日光放射之形。清文字学家吴大澂说:“皇,从日有光”。张舜徽教授也认为,皇之本义为日,犹帝之本义为日。日为君象,所以古代用为帝王之称。昊字,从日从天。昊字正是头上顶着太阳的神。中国古代太阳神名称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太昊”。
太阳崇拜在远古时期的实际存在,还有大量的实物遗迹可以证实。比如,商周秦汉时期的铜镜,就是这种物证之一。铜镜本来就有象征光明的意味,其背后常常饰有十字形或与太阳母题有关的图案。由于过去不了解十字图案与太阳的关系,所以这种纹饰考古学界定为“脉纹”、“涡云纹”。现在看来,这些都意在表现太阳。
汉代有一种以曰光为母题的铜镜,其中心的日纹常采用变型十字图案,而且镜的背面常书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类的铭文。从这类题词中可以看出铜镜的星形和十字形背饰与太阳的关系。镜,在中国古代习俗中是具有辟邪功能的神器。比如,《本草纲目》云:
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恶。凡人家宜悬大镜,可辟邪魅。
即使今天,这种习俗仍然存在于民间,以镜子辟邪的方法经常被采用。甚至给佛教造像开光的时候,也用镜子。这些都是太阳崇拜的孑遗。秦汉的瓦当也装饰着类似的十字图纹。过去,此类瓦当也被定名为“涡云纹”或者“葵纹”。然而,我们在瓦当上却常常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黄阳”、“羽阳千岁”、“朝阳之宅”、“光和宇宙”、“与华无极”等。这些文字表明,瓦当上装饰的十字是日纹,包含着祈祷太阳神福佑的意义。
考古学家在山东、四川、内蒙、新疆等许多地区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岩画遗迹,其中有许多十字形和花纹式样的太阳图案。最值得注意的是沧源岩画中的图形,上面出现一位手持“十”字,立于太阳之中的巫师图形。
1979年连云港将军崖发现一处岩画遗迹,据推测,此岩画可能是龙山文化晚期的创作’距今大约5000年~7000年。崖岩画的题材虽多种多样,但紧紧围绕着太阳与星宿崇拜这一个主题。在将军崖岩画的A组中,有一个有光芒的头像,也许正是太阳神的形象。将军崖的太阳神岩画,南北排成一列,颇似太阳从海面升起的样子,绘成变形的人面,表明太阳神被人格化了。
中国人喜爱菊花,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菊花与太阳的关系,更不知道菊花也是太阳的象征。据《本草大观》卷六记:“菊花……一名日精”。古人把菊花看作是“日精”,不仅因为菊花外形像太阳,更是因为菊花耐寒的品性。由此推而广之,人们对所有能耐寒傲冬的植物都比较喜爱。
(二)古代的文献记载
在中国的上古时代,的确曾经存在过太阳神崇拜,这一点,还可以从古代文献资料中找到证据。比如,《礼记》载: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
郊祭就是祭天,但其最早的祭祀对象则是太阳,因为在古人眼里,太阳是天的主宰。对这段文字郑玄的注文是:天之神,曰为尊。
孔颖达在注疏中也赞同郑玄的观点。
天之诸神,莫大于日。祭诸神之时,日居群神之首,故云日为尊也。天之诸神,唯日为尊,故此祭者,日为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可见,祭天就是祭日,这并不是一家之言。古人在《诗经》中咏道: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这“昭”也就是太阳。据《左传·桓公十七年》载:天子有曰官,诸候有曰御。曰官居卿以底曰,礼也。所谓“底日”就是“致日”,“致”是致敬的意思,致日也就是出迎恭候太阳升起。据《周礼·冯相》载:“冬夏致日”。每年冬夏致日两次,这一定与太阳运行的规律有关。
在《周礼》中记载着中国古代有一种用羽毛舞崇祀太阳的风俗。这种舞蹈在《周礼·舞师》中被称为“皇舞”。皇,即太阳和光明,所以“皇舞”也就是歌颂太阳和光明之舞。郑玄注《周礼》“皇舞”道:
皇舞,以羽帽复头上,衣饰翡翠之羽。皇,杂五彩羽,如凤风色,持以舞。
这显然是用凤凰的羽毛象征太阳,持凤凰羽毛起舞,自然是对太阳神的歌颂和祭祀。之所以用羽冠,也许是象征光芒四射的太阳。正如《说文》云:
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
火在人的头顶,就是“光”字的原意。这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结合皇舞,就明白了。这人头顶上的火,其实就是舞者戴的羽毛头饰,是用来象征日光的。
在汉代刘向写的《五经通义》中对皇、昊和天的关系是这样描写的:天皇之大者曰:昊天大帝。
这正是对太阳神的歌颂之词。道教创立之后,上天的主宰之神被称作“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的原形依然是太阳神。比如,唐代人写的《初学记》中引用此文,并且注道:
即耀瑰宝也,亦曰玉皇大帝,亦曰太一。
这显然是道教的语言,耀瑰宝、玉皇大帝、太一等等称号,都指的是太阳神。在其他古代文献中还能见到许多。比如《帝王世纪》:天皇大帝耀魄宝地。据《广雅·异祥》的解释:朱明、耀灵、东君,日也。
可见,“耀灵”就是太阳。古人称天上的诸星为“耀”,正是因为诸星具有光明。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神话思维中,日神是百神之王,它实际上就是上帝和玉皇大帝的本来意义。正如《庄子·天运》中所云: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
能够“监照”下土的,自然是天上的太阳。人们因为其能够照临天下并赋予光明和温暖,所以拥戴它为“上皇”。这“上皇”,当然就是日神。其实,上古传说中诸位先王的名号,都与太阳崇拜有关。比如:太昊、燧人、烈山、黄帝、炎帝、高明、高辛、帝俊、尧、祝融等。
当然,太阳崇拜的形成,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古代先民对火的崇拜,也是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火与太阳有相似之处,都是人类光明与热量之源。古代先民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以不同的神话形式表现出来。太阳神崇拜与火崇拜往往相伴而生、相互渗透。比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祝融,既是火神也是日神,炎帝也是如此。《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淮南子·天文训》云: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同时,炎帝又为日神形象。《白虎通义·德论上·五行》云:
炎帝者,太阳也。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另一个人物祝融,也体现了火与太阳崇拜并存的特征。楚人奉火神祝融为祖先,在东郊祭神,“楚”字的金文是日照森林之状,可见祝融既是太阳神也是火神。
据《山海经·海内经》载,火神祝融为炎帝玄孙,这些都表明中华远古先民初步认识到火与太阳的密切联系。
我国新石器时代日纹器物有很多,有仰韶日纹,半山型日纹、半坡型日纹和大汶口型日纹,仰韶形日纹有多种形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皿上,也有日光纹,体现了当时或之前的太阳崇拜的状况。甘肃省榆中县马家孤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片日纹,殷商以来还有不少日纹镜。这些说明太阳崇拜曾经在我国黄河流域广泛盛行。
夏商时代太阳神崇拜曾经广泛盛行,太阳神具有崇髙的地位。而其政权的接替者周王朝则出现“天子”的概念。这个“天”就是太阳,所以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自称为“天子”,也就是“太阳之子”。这种说法并非唐突。因为,我国上古时期,一些着名部落的首领如伏羲、炎帝、黄帝等都被视为日神的化身。
(三)祭拜的礼仪形式
神话以信仰为基础,有信仰就有祭祀活动。所以拜日与祭日的风俗,也是太阳神话与太阳崇拜存在的证明。
考察太阳崇拜的礼仪,首先要考察礼仪举行的时间,因为祭祀时间最能够说明祭祀的目的,也最能够说明太阳神信仰发生的初始原因。一般情况下,祭拜太阳的时间总是在清晨和傍晚,也就是日出和日落之时。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从古代到今天,无论是中原还是周边少数民族’都习惯于一早一晚进行对太阳的祭拜。这在古代典籍中有大量的反映,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有这种拜日之俗和传统。朝阳意味着光明和温暖的到来,世界上许多信仰太阳神的民族中,都选择这一时刻进行对太阳的祭祀,都认为这是最适宜祀拜太阳的时间。日出祭拜太阳之俗遍布世界,并且反映在各民族的太阳神话和信仰里,这表明全球各民族对太阳神崇拜的最初缘由大致上是一致的。
记载中国古代早晨祭拜太阳的活动的证据也有很多。首先,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日神岩(崖)画中描绘的,人们举手拜日的情景;其次,是殷墟卜辞里记载的早晨拜日的情况,似乎夏、商、周三代早晨祭拜太阳的情况很普遍;再次,是古籍文献中的记载,比如《尚书·尧典》中所谓“宾出日”,就是对日出时分进行拜日活动的记载。又如,《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汉代匈奴每天早晨祭拜太阳的情况,而汉帝国自己也有“朝朝日,夕夕月,则揖”。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有朝祭太阳的传统。
除了以上所说的汉代的匈奴之外,在我国其他的少数民族中,早晨祭拜太阳是屡见不鲜的。比如,古代蒙古人就有“出帐南向,对日跪拜”的习俗;云南阿昌族、布依族以及阿尔泰的乌梁海族人,也有早上祭拜太阳的习俗。东北的鄂伦春族的祭拜太阳的习俗最特别。他们毎逢正月初一的早晨,必定举行祭拜太阳的仪式。在祭拜开始的时候,族人们先聚集在部落中心的热闹处,等待太阳升起。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朝向东方,匍匐在地,跪拜太阳,并小声或者默默祈祷,主要的意思是在感谢太阳神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幸福,并且祈祷新的一年平安、丰收。
祭拜太阳的时间,除了早晨比较普遍之外,就是黄昏了。殷墟卜辞记载有送日仪式。据古籍文献,历代封建王朝都有黄昏“送日”的风俗。黄昏祭日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里也广泛地存在。黄昏祭拜太阳又意在何为呢?每天日落时分,是白天结束的时候,也许是人们将太阳神拟人化,人们一般会认为太阳神会像人一样地需要休息。或许还会认为,夜的降临,太阳神被黑暗的世界所吞没,这是太阳神在冥界与黑暗之神搏斗的时刻,此时祭拜太阳就具有祈祷光明战胜黑暗,保持永久平安幸福之意。另外,曰落之后的黑暗使远古先民将太阳的落山与冥界直接联系在一起。古人们会把这一时刻理解为灵魂进入另一世界的时机。在古人心目中,太阳当空之时,也就是现实世界;太阳落山之时,则是鬼魂世界,或者来世。这样一来,对太阳的祭拜,就将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结合起来。对太阳的崇拜,不仅表现了对现实生活的爱好,也表达了对死亡世界的恐惧和对未来世界的憧憬。
祭拜太阳的场所,根据少数民族神话传说、近现代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及古代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归结为三大类:一、日常生活起居之处,氏族部落时期在酋长家,国家形成之后则在皇宫内;二、临时搭建的场所;三、固定的太阳庙或祭坛。这里的分类序列虽然不完全是时间上继起的,但的确反映了太阳祭拜的盛行程度的不同。
祭日于家中是太阳崇拜最朴素也许是最古老的情况。之所以称这种情况朴素或者古老,就是因为这种祭日形式,往往是正式的太阳神宗教信仰产生之前的情况。这种祭日形式目前普遍存在于我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之中。比如,我国的侗族、景颇族,他们的插竹筒拜日仪式就是在自己家门口完成的;云南阿昌族人也是在自家的屋檐下进行对太阳的祭拜的。然而’在汉族的民间情况则有些不同,民间农民往往将太阳神和灶神、财神等一样地在家里进行祭拜。这种祭拜之风俗在民间长期存在,比如,辽宁海城县的民俗,每逢农历正月初一,是庆祝太阳神生日的日子,所以“家家于院内设香案,以碗贮米,焚香礼拜,曰‘祭太阳’”。
所谓临时性场所,主要是指为了祭拜太阳神而临时搭建的祭日场所。往往是为了部落集体进行祭仪活动而建。该类场所虽然属临时性质,但是,祭拜的活动和礼仪却比较庄重,规模也比较大。据古代文献记载,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均有临时祭日的场所。比如,《礼记·祭义》有“祭日于坛”,坛较之于后世的庙则具有临时性。三国时魏明帝则“乙亥,朝日于东郊”。隋唐及五代十国时期,均有对祭拜太阳场所的记载,据《新唐书·乳乐一》记载,唐代祭日坛“广四文,高八尺”,这样的场所当然只是供一时之需的。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临时性祭日场所形式多样,比如绝巴族的博嘎尔部落,是在门外搭篷架,其上方中央画一太阳。阿尔泰人则朝日出方向放置三角架或小石堆,并且用火炭烧烤柏叶香以祭太阳。云南的拉祜族则是在每年的阴历八月十五同时祭拜日月,他们在村寨的东西两头各建一座房子,东边的房子祭太阳,西边的房子祭月亮。
固定的祭拜太阳神的场所,则被称之为太阳庙。其存在的条件是太阳崇拜的盛行。其固定性首先在于专门性,也就是只用作祭拜太阳神,也表明太阳神巳经成为独立甚至是唯一大神。比如,古埃及人有太阳庙,印第安人有太阳金字塔。我国远古时代固定的祭日场所就是“日坛”。据《礼记·祭义》载:
祭日于坛,祭月以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
可见,日月均有不同的祭拜场所,并且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体制结合起来,它们显然是固定而非一时搭建之物。
通过对祭拜仪式的考察,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古代人类的太阳神崇拜的虔诚程度,也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人进行太阳神崇拜的动机。我们大致可以通过祭祀时的动作,祭拜时用的牺牲以及祭拜的方位等三点来考察古代祭拜太阳神的仪式。
在祭拜太阳神的动作上,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区域,往往有着很大区别。比如,欧洲的农民多用手和眼表达对太阳神的崇拜之意。但是,我国古代人对太阳祭拜时的动作的幅度就要大得多,往往实行的是三拜九叩之礼。这种祭拜方式,与我国祭拜其他神灵的方式基本一样。不仅中原汉族如此,边疆其他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比如,鄂伦春人、云南昆明的彝族人,他们在祭拜太阳神时都使用跪拜礼。这种外部形体动作的大幅度性,如果出于内心信仰,则表明其虔诚程度,如果是出于无奈:则表明外在强制的程度。
在祭拜太阳的过程中,使用牺牲是很普遍的,其内容也非常丰富。大致也可以归列为三大类:一、农作物或半成品;二,活物;三,其他食物。通过对祭拜牺牲的归类、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太阳神信仰在太阳神信仰区域的民众的生活和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说来,在生活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信仰越虔诚,牺牲就越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