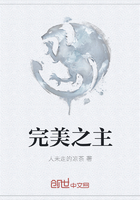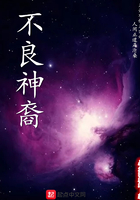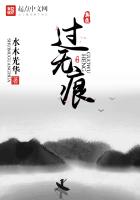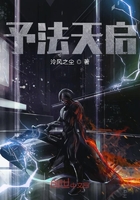法国人类学者雷诺根据近代原始民族一些事实,将图腾现象的特点归结为12个,主要内容是近代一些原始民族仍然存活的对某些特殊动物的崇拜现象,确信这些动物是自己氏族的祖先,能够保护本氏族成员不受伤害,并且制定一些禁忌以规范本氏族内成员的行为,部落中的某些有权力的人,可以以自己氏族尊崇的动物图腾作为自己的名字。
弗雷泽在《图腾观与外婚制》中,对图腾现象也做了简要的概括。他认为,图腾是原始民族迷信而崇拜的对象,他们相信,本氏族与这些对象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个人与图腾之间存在着自然利益的关系,人们崇敬它,以求得它的保护。如果图腾是一种动物,就禁止杀害它;如果是一种植物,就禁止砍伐它。图腾与偶像的不同在于,图腾是一类事物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对象,图腾很少是无生命的自然物,更不可能是人工制作的物体。
图腾观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远古先民与图腾之间具有一种尊敬和保护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不仅表示出同部族内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规定了部族之间的相应关系。“图腾社会”也是一种原始的婚姻制度,其主要内容在于禁止相同图腾的氏族成员之间发生婚姻或者性关系。原始婚姻制度是普遍存在于图腾制时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现象。
图腾观念与图腾制度起源于人类狩猎与采集的阶段。从许多现存的已经不再是原始的民族中残留的图腾遗迹来看,人类每一个民族都极有可能存在过图腾崇拜阶段。早期图腾崇拜很可能仅局限于动物。在以某种图腾动物为崇拜对象,在以此动物命名的图腾制部落中,氏族成员将自己看作图腾后代,并受到与图腾崇拜对象有关的禁忌的约束。禁忌内容包括:一般情况不能猎杀不能接触图腾崇拜对象,甚至不能直呼其名称。每隔一段时间举行图腾祭礼,并且宰杀图腾动物为牺牲。同时,还要举行仪式对被宰杀的祭物进行悲悼,请求宽恕以免遭报复。
在各种仪式和重要的宗教场合中,相同图腾崇拜的族人对图腾动物进行仿同:或用图腾的形态文身;或用图腾的皮毛装饰自己;或戴着图腾面具,模仿图腾动物姿态跳舞,并且学图腾物的吼叫,这就是最原始的祭祀歌舞。
在图腾制社会的群体中,图腾观念是氏族成员行为规范的基本内容。以图腾观为基础,建立起图腾崇拜的所有宗教和社会制度。在近代一些原始民族以及一些已经不再原始的民族历史中,存在着许多内容雷同的图腾起源神话。在这类神话中,一般都会有一个图腾祖先作为中心角色。这也是最原始的一种口头的历史,是图腾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原始先民,对这种神话视若圣史而世世相传,并且对其真实性确信无疑。
关于图腾崇拜的问题,中国学界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其焦点是:是否承认中国远古社会存在过图腾崇拜。争议的出现,不仅因为“图腾”这个名词和研究领域都完全是外来的,而且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确有着自己独特之处,是不能简单地用西方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硬套的。
笔者认为,“图腾”一词虽然是外来语,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是西方人类学的方法,其研究成果和对图腾制的基本定义也许与中国远古时代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中国古代神话中大量出现的人首动物身躯的神只形象,同时也是祖先崇拜的对象,这的确与图腾的一些特点相符。在这里笔者想到了关于“宗教”的定义,如果完全按照西方关于宗教的定义,中国古代是没有宗教的,这个结论显然无法解释中国的宗教现象。还有“哲学”这个定义也是如此,如果按照西方对哲学的定义,中国古代也是没有哲学的,这当然也是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不符合的,一个如此古老的民族怎么可能没有宗教,又怎么可能没有哲学?那么回到图腾的定义上来,问题大致相似。就是说,“图腾制”既然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过的社会现象,就像宗教和哲学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与思想发展史进程中一样,中华文化不可能特殊到与人类文化发展根本不同的地步。关键在于对“图腾”如何理解和解释。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不可能存在与西方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定义完全一样的图腾制,中国有自己的图腾制。其特殊性在于,中国古代的图腾制与古代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双性崇拜阶段,大量的人首龙(蛇)身的形象出现在文献资料、墓葬画像中。这些人兽结合的形象,表现着人类的祖先,同时以交尾的方式暗喻着人类的生殖与繁衍。所以,笔者将双性崇拜阶段又称为图腾崇拜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是生殖崇拜的一个特殊阶段。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的内容除了具有动物形象之外,其他的与西方人类学所研究的结论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中华文化与西方及其他民族文化不一样的地方。
与这个时代相应的神话就是伏羲、女娲兄妹成婚的传说。这个时期,男女两性是平等的,是母系氏族社会与父系氏族社会并存并向之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生殖崇拜表现为双性崇拜。正是这种特殊的双性崇拜,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阴阳两性之间的感应和交合,不仅是人类繁衍的过程,更是宇宙起源、天地演化、万物创生、人类出现的根本动力。
(三)太阳崇拜
太阳神是原始宗教与神话中一位显赫的神,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曾在古代世界大多数民族中盛行,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许多民族的风俗和神话传说中找到它的影子。我国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的太阳崇拜至少有七八千年的历史。
原始宗教形成之初的太阳崇拜产生于上古时代,太阳神信仰在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的中国曾经是重要的原始宗教形式。在与之大致相应的时代,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发源地也大都存在着太阳神信仰。为什么会有如此相似的情况呢?这是早期人类的生存环境决定的。
在远古时期,初民们生存的环境非常严酷,生产和生活方式又十分落后。当时的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艰难地挣扎。此时人类的思维方式十分简单,根本无法解释他们所面对的自然现象,觉得日月的存在,雷电的作用,都会决定人的生存,于是万物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有了神性,太阳神崇拜就是这种信仰的突出表现形式。如我国内蒙古阴山、广西宁明花山、四川珙县、云南沧源等地普遍存在有关太阳神和太阳崇拜的崖(岩)画。太阳神崇拜属于早期自然神信仰,与图腾崇拜先是相互并存或融合,后来逐渐独立存在。
在所有自然神灵中,人们最先认识到的自然神可能就是太阳神,它亦为诸神中最为显赫的神灵之一。日出东方是人们最先感受到的自然现象,黄昏日落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由于远古先人们无法解释日出日落这一类他们最早观察到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太阳运行的规律,所以他们以太阳为神灵是很自然的事。
太阳被崇拜为神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太阳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系。考古研究证明,太阳崇拜最迟产生于新石器时期,此时定居的农耕文明已经出现,人类的生活与太阳的升落、昼夜的交替和四季的变化密切相关,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显示着太阳神的威力。这正是太阳神成为农业文明时期主神的重要原因,因此古代农耕部族几乎都信仰太阳神。
气候与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对太阳神信仰的形成也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在北极圈附近的寒冷地区,阳光对居民的生存至关重要,所以古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遍信仰日神。相反,生活在赤道附近或沙漠地区的民族,由于太阳造成的酷热干燥而视太阳为恶神。中国古代有后羿射日的神话,这一定与曾经出现过的炎热干旱有关。虽然,这种因素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有关,因此缺乏普遍性,但是却表明地理环境与原始宗教存在着联系。
在有关太阳崇拜的神话传说中,太阳神诞生的内容十分突出,其形象各异反映出民族和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在中国上古时期和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太阳神的形象往往较多地与三趾乌、龙或蛇、凤凰、鸡或鸟联系起来。太阳龙这一形象,在中国比较普遍,民间普遍有龙衔太阳的图饰。这可能是远古时代太阳崇拜与龙(蛇)图腾崇拜相结合的表现。
日神最常见的还是人的形象,不仅具有人形,而且拥有人性。当然,太阳神以人的形象出现,是太阳崇拜的-个特殊阶段。早期阶段,太阳神的形象与动植物纠缠在一起,经过半人半兽的阶段,然后进入人格化的阶段。而太阳神的人格化过程,大致也有三个阶段。
一是半人半兽阶段。在这一阶段,日神的形象带有图腾信仰的遗迹。表明在远古神话中,图腾崇拜与太阳神信仰相互掺杂。二是神人合一的阶段。日神形象已基本人格化,部落的首领同时也是太阳神。崇拜太阳的部落将其被神化的首领与太阳神联系在一起。如中国上古时期黄帝、祝融、炎帝、颛顼等。三是抽象神的阶段。这是太阳神信仰由鼎盛走向衰落的阶段,太阳崇拜与信仰开始具有抽象的寓意,太阳神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神灵,与祖先崇拜和灵魂不灭等观念相联系,太阳神已经演变为抽象意义的神灵,最终形成“帝”或“天子”的概念。当“天子”的概念占据人们心中的主要位置之后,太阳神就演化为一种全新的抽象神,其人格形象便是人间的帝王。
太阳神在原始宗教中作为主神,体现了它的创世意义,由此对太阳神的信仰,演化为对伟大的创造能力的崇拜。太阳神及其信仰中所包含的创世意义,一方面说明太阳神信仰具有朴素的自然崇拜的特征,因为创造过程总是与自然现象相联系。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创世意义体现着人类思维的进化。虽然太阳神信仰依然属于原始宗教,但是人类的认识已经开始走出蒙昧,并且在向更高的阶段攀升。
这种走向的意义在于,太阳神信仰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太阳神逐渐成为农业神。因为,定居的农耕部落对太阳的运行规律性、四季的变化最敏感,也最需要掌握其中的规律。农耕文明是靠天吃饭的文明,人类赖以生存的庄稼的生长离不开阳光的照射;太阳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这是人类的祖先将太阳视为生命之神的重要原因。就是说,远古先民对太阳的崇拜,是与他们的生活内容和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是他们的生存需要的集中表现。
太阳神与农业生产密切关系的另一种表现,是太阳历法的发展。具有太阳崇拜的民族,太阳历法往往比较发达。上古时代,中国的天文历法产生了以十干(十日)作为纪年的太阳历法。太阳神在远古中国神话中同时具有司掌历法的能力。由于对太阳神的崇拜和信仰,加强了对于太阳的观测,从而取得天文和历法知识,推动了农业文明的进步。
当太阳崇拜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崇拜时,与政治权力并无太多联系。当太阳神崇拜发展到成为国家统一信仰之后,就会充分地显示出其政治意义。它起着统一部族内部认识和行动的作用,最终将成为团结部落成员的凝聚力量。
夏商时代太阳神崇拜曾经广泛盛行,太阳神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其政权的接替者周王朝则出现“天子”的概念。这个“天”就是太阳,所以封建王朝的最髙统治者,自称为“天子”,也就是“太阳之子”。这种说法并非唐突,因为,我国上古时期,一些着名部落的首领如伏羲、炎帝、黄帝等都被视为曰神的化身。
后羿射日神话,意味着统一的太阳神信仰最终被接受,最终达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政治统一。当祖先神完全与太阳神融为一体的时候,祖先神实际上也就取代了太阳神的地位。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的最终确立是一致的。此时,作为神话的太阳神也就终结了,取而代之的祖先神崇拜,依然是一种生殖崇拜,但却进入到神话的终结与神话历史化的进程中。太阳的形象也逐渐被“天”的抽象性所掩盖。人间帝王的祖先是天,所以被称为“天子”,天成为帝王权力的授予者、保护者和监督者。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观点是“天尊地卑”,与其相应的人间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是“君尊臣卑”、“男尊女卑”。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礼仪制度,并将宗法血缘观念制度化,最终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
这三类生殖崇拜的神话传说在时间上的顺序,也就成为本书结构的内在逻辑联系。然而,本书的主旨不是简单地介绍中国古代这三大系统的神话,而是要追溯它们的源头,并且论证这三大神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思维的影响。全书由上、中、下三编构成。上编追溯女娲神话的源头,这是中国远古生殖崇拜,也是母性崇拜的时期;中编追溯伏羲、女娲成婚神话的源头,这是中国远古图腾崇拜,也是双性崇拜的时期;下编追溯伏义神话的源头,这是中国远古太阳崇拜,也是祖先崇拜时期。这三个时期的顺序自然是逻辑上的排列,我们确信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点,但是神话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不可能如此的整齐划一,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会发生重叠,三个时期的神话和观念也往往会混杂在一起,这也正是逻辑与历史的不同之处。然而,写的历史并非历史本身,尤其是神话的历史,所以发生逻辑与历史的不一致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