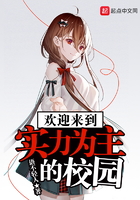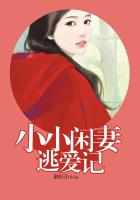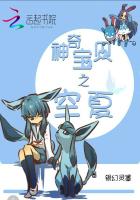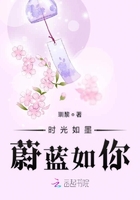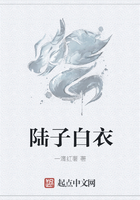如果说老子将天地根源比拟为“玄牝之门”,是源于母性生殖崇拜的神话思维的话,那么阴阳感应、天地化物、万物交感等思想的源头就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两性崇拜的神话。所以笔者在论证了兄妹成婚的起源之后,将分析《周易》一书中的有关哲学思想,以加深对两性生殖崇拜神话的哲学价值的认识。《周易》的哲学思想主要集体表现在《易传》的“十翼”之中,因其产生于特殊的年代,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吸收了诸子各派的思想,是战国时期学术大融合的产物。《周易》的哲学思想是非常复杂和丰富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内容贯穿其始终,这就是对自然界的阴阳感应、天地化物、万物交感等现象的揭示。这种思想,正是两性崇拜的哲学表达,与两性崇拜的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天地大德,万物化生
无论是母性崇拜还是双性崇拜,其核心观念是对生的崇拜,所以都会表现出对创造生命之伟力的歌颂与赞叹。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生殖崇拜的哲学命题。在《周易》中,“生”这一概念意义很复杂,从哲学范畴的角度思考,大致可以包括三重含义:一是抽象意义的产生;二是具体的生命过程;三是天地创造万物的过程。
(一)物之始生
“生”这个概念在《周易》中的第一层含义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从无到有的过程,并非特指生命过程。比如: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作易的人先设计好卦,即画出了64卦的卦画之后,再观察卦画之中的象,然后又系辞,即在卦与爻的下面系上文字说明,让人一看卦下和爻下之辞,就可以知道卦画所表达的吉凶了。那么“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中的“刚柔”也就是卦中的阳爻和阴爻,阴阳与刚柔本是一回事。从气的角度看,叫阴阳;从质的角度看,叫刚柔。卦中之爻是可见的,故应当从质的角度看,曰刚柔而不曰阴阳。也就说,两种相反的力量作用之下,事物发生变化。这是“生”的概念在《周易》中第一层意思。
“生”的过程,也可以不经过两种力量的作用。比如: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此句极赞《易》道之广大。“广”指坤,“大”指乾。乾坤广大,弥纶天地,有形无形都包括。从远处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抵御它;从近处看,它处处皆见,虽然至小、至近、至卑、至陋之事物,不待安排,都有它的存在之位;从整个宇宙的角度看,天地、万物、人事都包括在《易》的道理之中。而这广大的易理又是从乾坤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这里的“生”便是人类抽象思维的结果,与生命过程没有关系。
“生”在《易》中还有因果之间的联系的意思。比如: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孔子分析乱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一般情况,祸从口出,言语不慎,是造成祸乱的原因。所以为君者必须谨慎,否则会失去臣的拥护;为臣者也要出言谨慎,否则会招杀身之祸。至关重大的事情如果不谨慎就会造成巨大的灾害。所以孔子告诫人们言语和行事都要谨慎。那么,此处的“生”便是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了。
用“生”表示因果联系的还有许多,最典型的是用一连串的“生”,表达一系列的因果链条关系。比如: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易中包含着太极,因此生两仪。“两仪”也就是匹配或成对的意思,就像天地、夫妇、君臣、幽明、昼夜等自然和社会现象一样,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有两对事物内部的矛盾,所以会产生四象,再因四象而生八卦。这个“生”,是自然界演化过程的抽象概括,揭示了整个自然界由于太极这一总的根源的存在而逐渐形成。
《周易·系辞传上》。
“生”所具有的这种根源与因果联系的意味,自然可以引申出“出现”的意思来。比如: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天生神物’’并非说这神是由天生出来的,而是指这神自天而降,出现在圣人面前。所以这里的“生”与后来的“变化”、“垂”、“见”、“出”都是一个意思。这些神物、天地的变化,象和吉凶之兆,甚至河图与洛书,都是神秘的天呈现给圣人,以资其画卦用的。
这种自然的呈现,往往不以人的观察为条件,它是大自然的演化过程。比如: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这是万物与天地产生的先后顺序。先有天地,然后万物生成。那么“屯”所表示的则是天地间万物的总称。所以“屯”就是“盈”,也就是充满的意思。这种充满是一个过程,而屯就是这个盈的过程的起点,所以说是“物之始生’’。这里的“生”自然当作出现或呈现讲。虽然没有人,物就无所谓“呈现”,但是此处不提圣人则、象、效之等话语,则意在表示天地万物的纯客观的存在。那么这样的“生”也就是一种纯客观的过程了。
(二)人有生死
“生”概念在《周易》中的第二层意义,是具体生命的过程。比如《坤卦·彖传》曰: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而这里却说“至哉坤元”,乾元称“大”,坤元称“至”,显然“大”与“至”是有区别的。因为,乾象天,天之体大而无限,并且是无形的,所以称“大”;坤象地,地之体虽大但是有限,而且是有形的,所以称“至”。正是有形的坤或地,才能具有滋生万物的能力。而乾元则称“资始”。这一个“生”,一个“始”,其间的区别也在于有形和无形。从乾坤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出,此处的“生”,指的是有形的事物的生长,而能够在大地之上生长的东西,自然是生命体。
“生”的这层意思在“升”卦中表达得更加明确。比如《周易·升卦·象传》曰: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升卦是巽下而坤上,下边是木,上边是地,有木生于地中之象。后一句话意在表达,君子的修养德性的过程,就像木生于地中,由幼小细嫩之芽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那样的日积月累,从容渐进的过程,要积小以成高大。树不可一天成才,人亦不能一夜成圣。所以,不能以善小而不为,要积小善成大德。这种道德化的比拟,恰恰表明这里的“生”是生命成长的过程。
用“生”表示生命过程最直接的表述是人的生命,尤其是在作为与死相对立的概念并与之同时出现的时候,此意更加明确。比如: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据《经典释文》说,“原始反终”有的本子作“原始及终”,此解可能更接近原文。一是因为从道理上说得通,二是从字形上看相近。从道理上说,事物有始必有终,人有生必有死。人有生有死与事物有始有终,道理是一样的。知道了原出的“始”是什么事物,也就可以“及终”,即知道“终”之为何了。这是对孔子所谓“不知生,焉知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生死相对,所以“生”在这里专指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过程。
人是有生命的个体,人的生命过程也就是整个人生过程,所以生命的“生”,也就引申为人生的“生”。比如《周易·观卦·六三爻》曰:
观我生进退。
从卦爻的关系看,六爻之间的位置不同,关系不同,意义也有很大的差别。一般而言,三爻不居中,二爻居中,所以二爻好而三爻不好。但是,观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观卦的好与不好,要看离九五的远近。而六三爻在下体的最上头,又在上体的下面。它处在上下之间,可进可退,因此可以从容自观,也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人生处境,时机成熟便进,条件不具备便退,这就是“观我生进退”的意思。这里的“生”当然是人生了。
(三)天地大德
从生成变化之“生”,到生死之“生”,再到人生之“生”,最后达到对生命本体的“生”的髙度概括。《周易》中虽然没有表现出其间的逻辑演进过程,但是“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等命题无疑是对万物总根源和世界本性的思考,是《周易》哲学的最高成果,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进程。
前文说到,老子在《道德经》中设计出一套宇宙的演化模式,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们已经做了分析,这“三”不是数字之“三”,而是阴阳叠加成结构而形成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生”,所以说“三生万物,’。然而,同样推崇生命的《周易》却以另一种方式设计出不同的宇宙生成模式。《周易·系辞传上》曰: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钋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这里的“易”是指宇宙的根本规律,“两仪”就是阴阳,最根本的“易”就是太极。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过程,是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这与老子《道德经》中的“三生万物”的生在方式上不同,但其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生”的过程。《周易》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其中的生,等同于《道德经》中的“三”。也就说,虽然二者建构出完全不同的宇宙生成模式,但是宇宙的演化是一种生的过程,这一点是共同的。
在《道德经》中,最高的范畴是“道”,具体事物的规律和规范是“德”,在具体规范的德中,也有层次不同的,其中最高层次谓之“玄德”。在《周易》中,这种层次的德称为“大德”,这样的品德不可能是人所具备的,只能是创造万物与众生的天地才拥有。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里的“大”就是无限,具有无限创造力的天地,是万物的根源,也是我们人类的根源,没有天地就没有我们人类,所以人类应该对天地怀有感恩之心,将天地创造万物与人类看作是宇宙间最高的德性。老子所谓“天门开阖,能为雌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虽然也是在歌颂生的功德,但是他仅说“天门”,不说“天地”,因为老子心目中,“玄牝之门”是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就是说在天地之前,还有源头,而《周易》则把天地视为根源。这里的差别,似乎可以看作是母性生殖崇拜与双性生殖崇拜两种不同的神话思维的影响。
不过,《周易》中也有对生命的终极根源的追问。比如《周易·系辞传上》曰:
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所谓“大业”就是伟大的事业,其根本特征在于“富有”。“富有”不是指人的财富的富有,而是指自然界万物生机的富有,自然万物无所不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着物质资源。而且这种富有又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所以说“日新之谓盛德”。“日新”就是变化无穷,生长不息,变通不止的意思。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那么,是什么力量使世界如此富有至盛之德呢?就是“易”,也就是使生命之所以为生命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生生”的意思。这里的“生生”不是形容词,而是述宾结构或者使动用法,是使生命得以生的意思。那么,这个使生命得以生的总根源,就是易。这种力量,使乾成象,使坤效法乾?人只能通过占卜去把握它。正所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
二、天地氤氲,乾坤阴阳
《周易》特别发展了阴阳、天地、乾坤交合而生万物的思想,正是两性生殖崇拜的神话思维影响下的产物。构成两性对立关系而生万物的名称有很多,比如男女、天地、乾坤、刚柔、上下等。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它们的功能是一样的,就是《道德经》中所谓“二生三”。以下我们就几个不同名称所表达的两性交合具有生殖功能的观念加以简略介绍,以使读者明白,双性生殖崇拜的神话思维,对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发展的影响何其深远!
(一)男女构精
两性生殖崇拜神话的现实依据是对两性关系的生育功能的发现,所谓“近取诸身”也正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阴阳观念的形成,首先是以远古先民对自身两性关系的认识为起点的。比如《周易·系辞传上》曰: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这里的“男女”是泛指,不仅指人类的两性,还包括动物与植物雌雄或牝牡。万物所以有生命者,都各有阴阳之精气,精气相交,则可以化生万物。
正是基于对两性生殖的崇拜,两性关系在古人的心目中并非不洁的。和谐的性关系,不但是生育的开始,而且还会给当事人带来吉利。比如《周易·大过卦·九二爻辞》曰:
枯杨生秭,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杨生秭是老树生根的意思。“九二”已经是老阳,已经过了生命的最佳时段,所以爻辞将其比喻为“枯杨”、“老夫”。但是,老夫虽然老,却得到年轻的女人为妻,从而能够获得生育之功,所以“无不利”。
然而,老妇得士夫则与之相反了。也就是老男人可以娶年轻的新妇,而老女人则不能嫁年轻的男士。比如《周易·大过卦·九五爻辞》曰:
枯杨生华,老妇得士夫,无咎无誉。
士夫,就是年轻的丈夫。老妇嫁年轻人,虽然有枯杨开花之象,但是年轻的丈夫与年老的妇人在一起,却没有生育的功能,虽然并无凶兆,但也无吉利可言。《周易·大过卦·九五爻象辞》的评价就更明确了:
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枯树开花虽然表现出一线生机,但是花开于迟暮之年,非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使它仅存的一点阳气耗尽,自然不可能长久。老妇已然不能生育,即使得到年轻男子为夫,依然不能生育。所以,枯树开花,就不如枯树生根,表面看挺好,其实是件丑事。
正是以两性生殖崇拜的神话思维看待事物,所以古人认为异性相交可以创造生命,无不利,而同性在一起就会发生冲突、分离和争执,所以不吉。比如《周易·睽卦·彖传》曰:
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火动在上,泽动在下,水火不相容,自然是一种分离、争执的状态。就像二个女人同居一室,自然各有所归,志向不同。睽而不合,天地万物便要停止发展,所以睽而必合。由不合转而为合的关键在于,改变相关项的性质。所以说“男女睽而其志能”。睽或者分离,并非绝对不好,天在最上,地在最下,天地之间是最大的睽,男女之间也是睽的关系。然而因其性质相反,所以才会有万物化生,才会有生命诞生。所以,有分才有合,有合才有生,所以说“睽之时用大矣”。
(二)天地氤氲
万物是天地所生,先有天地而后有万物,诚如《周易·序卦传》所说:“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那么,进一步追问,天地是如何生万物的呢?《周易》对此的回答是十分明确的: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天是无限的,也是无形的,所以它是万物的起点;地是有限的,也是有形的,所以它为万物的生长提供了材料。但是,它创造生命的过程必须与天相结合,并且处于顺承的地位。关于天与地之间交合而生万物的功能,《周易·系辞传上》曰: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所谓“氤氲”就是天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化醇”就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正是天地间这种氤氲作用,才使得万物产生。
氤氲是一种比较抽象的说法,其实在古人的心目中,天地之间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雨雪、冰雹、雷电、风云等自然现象。尤其是雨雪等由天而降,施于大地的过程,是天地交合最形象直观的表现。正如《周易·益卦·彖》曰: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