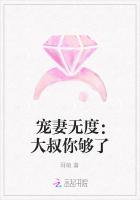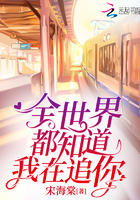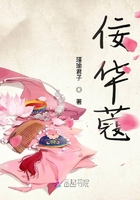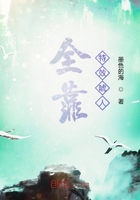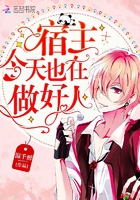这则神话传说表面看是有时间地点的历史事件,但是细分析起来却是一则神话,其中的矛盾之处,恰恰是历史与神话无法融合的表现。从时间上看,明确为汉武帝元鼎三年夏天,同年汉武帝派兵西征匈奴取胜,然后要将陇西分为两个郡。但是,细分析起来这时间很难统一。夏天发生的事情,即使到年底设郡取名,也只有半年时间,怎么可能有“春不涸,夏不溢,四季滢然”的“天河注水”之传说?显然,这“天河注水”的传说远远早于汉武帝元鼎三年。一旦发现时间与事情的不一致,那么这件事情的信史性就大打折扣了,只能按照神话去理解。如果说“天河注水”是神话,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会在这一带出现这样的神话呢?笔者以为,“天河注水”的神话与女娲补天的神话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前所述,女娲的诸神格中有“止淫水”一项,许多女娲神话都传说女娲是战胜洪水的神。补天神话正是与天雨不止的灾难有关。“天河注水”,如果地无法承接的话,对人类来说只能是一场灭顶之灾。然而,这则神话没有传说女娲补天,而是说大地裂开了一个大缝,将天河所注之水化做一汪湖水,不但化解了自然灾害,而且使这天河之水成为一方土地生命的泉水。正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属阴,阴便是母,只有伟大的地母才能有如此力量和胸怀,牺牲自己拯救人类。这就与上一则神话中,女娲将自己的身子补进天洞以止暴雨一样,反映出古代先民特有的神话思维的创造。一个是以自己的身躯补天,一个是大地裂开以承载天河,虽然有天地之别,但却都使人类从自然灾害中得救。虽然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会发生黏合、脱节和变形,近世的传说形态与其原初形态相距甚远,但是其中的基本精神会长存,那就是远古先人们通过神话思维所表达出的内心最诚恳的愿望,这是神话的内核,发现它,就找到了神话的原初形态。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可以大胆地作出结论:“天河注水”的神话是“女娲补天”神话的变形。当然,这与女娲神话的基本神格和女娲神话的最原初的形态依然存在着距离。这需要对女娲补天神话做进一步的解析,以寻找它的最初原形。
女娲补天的神格与女娲造人的原初神格有没有关系呢?也就是说,与自然灾难斗争的神话与生殖崇拜的信仰之间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笔者认为,女娲补天神话依然曲折地反映着人们的生殖崇拜的核心内容。或者说,远古先人企图将战胜生存困难的成功,扩大到对自然灾害的征服过程中。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古代文献对女娲补天神格的记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槛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这段文字中最关键的一句是“积芦灰以止淫水”,这是整个神话故事的核心内容。这里的淫水,表面上看是泛滥成灾的洪水,但细分析却说不通。因为,芦灰是芦苇燃烧后的残灰。草木灰能止住洪水吗?显然不可能。但是,人们在流传这则神话的时候,对此不加怀疑。那么芦灰能止住的是什么水呢?据《天水民俗录》记载:
旧时在农村在炕上铺上麦秸、谷草或草木灰,让婴儿生在草灰上,谓之“落草”。
产妇坐在草灰堆上,第三日扫灰炕,叫“起草”。落后的天水农村,女人生孩子时没有消毒设施,身下只能铺草木灰以防止感染。那么女娲积芦灰所止的淫水,自然就是女人生孩子时的血和羊水了。这种现在看来十分落后的防止感染的方式,在女娲时代则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发明。或者说,女娲第一次使用芦灰为女人接生,从而降低了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
女娲作为生殖崇拜的对象,不是她自己能生,因为一个女人再能生也是有限的,而是她会接生,也许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具有一定科学性手段的助产士。她接生的水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最高的。在以保持髙生殖率为种族得以延续的唯一方式的年代,一个接活率很高的助产士,该是何其伟大。在远古人类还处于蒙昧时期条件下,首先使用草木灰来止羊水,自然降低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这对当时的人类来说,是一项伟大的贡献。我们都知道,女娲是神话人物不是历史人物。那么,首先使用这种方法接生的氏族,一定会比其他氏族人丁兴旺,自然会发展壮大,这也许就是女娲成为生殖崇拜对象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天水一带民间依然把会接生的女人叫“疯婆子”,这个称呼自然和风姓族人擅长接生有关,当然也是女娲神话的起源在天水的又一力证。
正是因为草木灰有这种功能,所以天水一带民间妇女每到农历二月初二的“龙抬头”之日的清晨,便以簸箕盛草木灰沿着院落四周,一边用擀面杖敲打簸箕,使草木灰徐徐撒在墙根,一边口中念叨:“二月二,龙抬头,虼蚤壁虱别抬头,要抬头,一簸箕打在灰里头。”意即消灭害虫,祈求五谷丰登。天水一带的民俗,在人死人殓时,也要先在棺内垫以草木灰。
女娲“补天”的神话,依然可以与生殖崇拜联系起来。人们都知道,女人生产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是“血崩”,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止血的话,产妇和婴儿都可能生命不保。能够成为神话人物的女娲,一定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止血技术,这也是“止淫水”的又一种解释,具体是什么办法现在当然无从知晓。不过陇城一带民间广泛流传这样一则传说:
风沟的“女娲潭”边长满了毛腊草,女娲用毛腊草止血。村里的老人说,毛腊草在一百年前还有,现在潭达没草了。
这种草能否止血已经不重要,关键在于民间的确传说女娲掌握了一种较高水平的止血技术,这也是使她接生成活率高,从而成为生殖大神的重要原因。
(三)制作笙簧的真实含义
一个令人感到困扰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女娲作笙簧”的事迹。所谓“笙簧”实际指两种东西。“笙”就是一种多管乐器,它是由笙斗和笙管两部分构成的。其笙斗是一个空葫芦,竹管即环列插于葫芦斗中。而“簧”则是笙管中再安装的竹制(或铜制)的哨片,吹之即可发出声响。目前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广泛流行的葫芦笙、葫芦箫、葫芦丝、芦笙、排箫等就是笙在后世的遗存、发展和变异。大多数论及女娲事迹的古代文献和民间传说都提到女娲作笙簧的事迹。虽然我们知道,女娲的事迹在不断地被神化,附加在她身上的人类文明成果也不断地增多。但是,为什么偏偏把作笙簧这样的功劳加在女娲身上呢?笙簧与女娲的原始神格有没有关系呢?许多民间传说实际上也在解释这二者的关系,说笙是用葫芦做的葫芦文化也是一种生殖文化的表现。天水一带也有这样的神话传说:
一天,突然从竹林里传来“呜呜”的声音,伏羲感到很奇怪,循声朝竹林走去,一看,原来女娲手里拿个椭圆形小葫芦在傻吹呢。平时这么小的葫芦伏羲连看也不看,就是嫩的时候能吃,再没啥用处。伏羲感到很新鲜,学着女娲的样子,嘴巴也贴在小葫芦颈口上使劲吹了几下’竟也发出了“呜呜”的声音。两个人换着吹了一阵’女娲说:“就是声音太小,太单调’没意思。
怎样把声音扩大?又能吹出不同的声音来呢?女娲突发奇想,折了一根细竹子,朝葫芦的肚子上捅了三个小孔,然后用手指按住小孔,嘴巴贴在颈口上使劲一吹,手指抬起放下,发出的声音和原来不一样了,竟有四五种高低不同的声音。伏羲说:“吹出来的声音多了,就是声音还小。”
女娲又折了几段空心竹子,把竹管往葫芦肚子上的小孔里一插,试着朝葫芦一吹,竟然三孔齐鸣,几种声音混合在一起,应山应水,动听极了。
族人们听到这奇特的声音,全都跑到竹林里来看个究竟,见是伏羲、女娲在一个古怪的东西上吹出的声音,十分好听,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唱了起来。这就是“女娲作笙簧”典故的由来。
这个故事显然是后人编造的,是根据现实生活存在的笙杜撰出当年女娲、伏羲制作笙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女娲作笙簧”神话植根于先民的生殖崇拜。神话中女娲所作笙簧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一种乞生巫仪。并且指出,笙簧由竹管和葫芦构成,竹管象征男根,葫芦则寓意母体,二者的结合,象征性地表达先民对两性交合方能生人的认识?。这种解释似乎接触到了这则神话的原初形态。但是,女娲神话的产生,是以对母性生殖能力的崇拜为前提的,那个时候,古代先人还没有认识到男性在生育过程的作用。笔者虽然不赞同这种观点,但是对其思考问题的角度还是认同的。就是说,女娲作笙簧的确与生殖崇拜密切相关。
无论是古代文献、民间传说还是现代学者的研究,都首先接受了“女娲作笙簧”这个事实,然后再从实物和功能的角度去论证和解释何谓“笙簧”,以及它的象征意义。但是,人们都忽略了几个问题:一,“笙簧”本不是一物,两字连用仅在描写女娲作笙簧时出现,作为完整的乐器,仅有“笙”而无“簧”,更没有“笙簧”;二,女娲神话产生于新石器时代,那个时候能否加工出薄如蝉翼的簧片且另当别论,在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生”与“笙”,“簧”与“皇”之间,如何分得清楚呢?而且古音(现代某地方言亦如此)“皇”、“王”又不分,说女娲“作生皇(王)”,和说女娲“作笙簧”,如果没有文字表达,二者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结合前文的考证,女娲是生殖崇拜的偶像,也许历史上有这样一位聪明能干的母系社会的首领,她因为能够给人们带来生命的希望,能够使部族人丁兴旺,她自己成了生的象征,她因此而为皇(王),成为生之皇(王)。东汉许慎《说文》说: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可见女娲是大地之神,自然之神,她是“化万物者”,所以,就是“生皇”。“作生皇(王)”就是在远古先民心目中具有主宰生命力量的首领,她最终升格为生殖崇拜的大神。也是在此意义上,伏羲亦被视为春皇。东晋王嘉《拾遗记》说:
春皇者,庖羲氏之别号。
春是主导春暖花开,万物复生的春天,当然也有生殖的涵义。伏羲被称为“春皇”,表达的就是生殖崇拜的意义,比伏羲更早的女娲,为什么就不能“作生皇”呢?所以说女娲“作生皇(王)”,才是“女娲作笙簧”的本义。这让笔者想起闽台一带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神灵——“保生大帝”,其原型是一个道医,因为他济世救人,为民除病,死后被敬奉为神灵,受到广泛的信仰和祭祀。一个给部族带来生的希望的首领,被尊为“生皇(王)”是顺理成章的。不过,“春皇”与“生皇”略有不同。春皇是两性关系与生殖相联系的产物,而生皇则纯粹是母性生殖崇拜的结果,否则也不会将“作笙(生)簧(皇)”仅与女娲的神格联系在一起了。
在天水一带流传的一则“五谷的来历”的神话,虽然与“女娲作笙簧”的神话无关,但却证明着女娲是一位“生皇”。
冥冥远古,人们过着艰苦的原始生活。眼看着人们痛苦的呻吟,女娲娘娘被深深地感动了。
一天,女娲将自己的五个孩子唤到身旁,语重心长地说:“如今老百姓的天已经塌了,你们兄妹五人能为百姓找些食物吗?”五个孩子听后,异口同声说:“娘,您放心!我们一定找到食物。”谁知这五个孩子来到人间后再也没有回到天宫去。
一晃过了三年,女娲不见孩子音讯,于是下凡寻找。她走进山谷,看见一片奇形怪状的草向她点头哈腰,那麻绳似的草头上结满了粒粒珍珠,她高兴得笑出声来。不料,草丛深处却传来了大儿子的声音:“娘,您怎么来了?”女娲惊奇地叫道:“孩子啊,你在哪里?”“娘,我不是在给您叩头吗?”这片草将头弯得更低了,女娲全然明白,大儿子已化为植物了。女娲悲喜交加地说:“孩子,我行程万里,在这山谷中找到了你,娘给你取个名,就叫你‘谷子’吧。”只见谷子齐刷刷地朝妈妈又叩了头。
女娲爬上山梁,见山梁上长着一片个高头大的植物,它们的脸红到了耳根,女娲纳闷间听见二姑娘说:“娘,我刚才打了个盹,不知您来了。”女娲知道二姑娘也化为植物了,便说:“傻丫头,站直身子让娘看看,长高了没有。”二姑娘伸直了脖子,粉朴朴的脸蛋更红润了,女娲疼爱地叫她为“高粱”。
女娲跨过大海,来到一座小岛上,一片绿油油的草丛站在水里,手舞足蹈嬉戏玩耍。不待她开口,草丛里立刻传来了三儿子的声音:“娘啊!您也下来洗个澡吧!”女娲看见三儿子和往常一样调皮捣蛋,因此,给他取名叫“水稻”。
女娲经过一座独大桥时,忽听有人喊她:“娘,你看我这身衣服漂亮吗?”她四下一望,原来是一片红竿绿叶黑脸蛋的植物在叫她。女娲觉得四姑娘还是娇滴滴的天性,便给取名叫“荞麦”。
女娲找遍了五湖四海,还是找不到最小的儿子,她思子心切,迷失了方向。一天晚上,她在一片草地中刚躺下,便听到了小儿子熟睡的声音,原来这又是一片粮食作物,于是,就给最小的儿子取名为“糜子”。
这则女娲神话故事的内容是比较少见的,写得极富人情味而且很感人。虽然后世人创作和编撰的痕迹很重,但是有一个核心的精神却清楚地表达出来,即五谷都是女娲儿女,是女娲亲生的。这则神话其实是女娲化生万物的形象化表达。这一则神话的核心内容既保留了古人对生殖大神的崇拜,也寓意着后人对始母神女娲深深的怀念和感激之情。这正是中国古代生命哲学观点的神话源头,也是这种哲学思想的社会、心理与情感基础。
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思想的精华是哲学,所以神话起源的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思维定势与核心内容。以女娲神话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母性生殖崇拜对中国古代哲学有很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中。联系中国古代女娲神话和母性生殖崇拜的观念重读《道德经》,笔者发现其中有三个方面表现出其受到母性生殖崇拜的影响。一是《道德经》在对道的思考和解释以及对天地自然和人类的起源的追问过程中,提出和使用的几个重要的概念,即“母”、“门”和“帝”等;二是对“生”这一概念的运用,其内涵既有作为日常生命现象的“生”,也有作为宇宙和生命根源的“生”;三是对阴性或水性的推崇,所谓“上善若水”和“以柔克刚”正是母性崇拜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