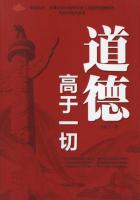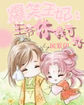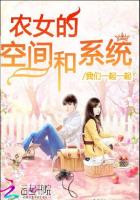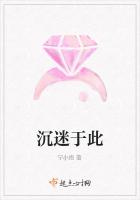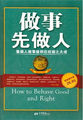女娲、伏羲既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初祖,是三皇之首,又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神话中的神只。虽然历史不是神话,但神话折射着历史。前人对女娲、伏羲神话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女娲、伏羲神话的源头在何处,却由于神话传说年代久远,至今是个谜。如果对神话的源头没有充分认识,神话研究就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只有真正探寻到了神话的源头,才可能进一步了解神话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总体看来,我国的神话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话曾经被视为迷信和唯心主义的东西,神话研究的学术地位也比较低下。然而,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因此,人们一再被疯狂的宗教情绪所控制,现代神话不断地被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所以,笔者认为对神话这种人类精神的特殊现象,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这样,既可以充分认识神话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给神话这种人类文明的曙光以正确的评价;又可以通过对神话发展的某些规律的总结,正确地面对现代神话的制造者对人类精神的蒙蔽。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现在,探讨神话是为了把握现实。当我们对中国最古老的神话的源头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我们会对现代人类的精神生活有更清晰的认识,并且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神话源头的依据
女娲和伏羲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最古老,也最着名的两位神只。然而,女娲和伏羲并不是历史人物,所以没有故里。这里所谓的“娲义故里”是指女娲、伏羲神话传说的源头。如果将女娲、伏义视为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那么对其故里的考证就必须有直接的地下文物发掘作实证。然而,神话就是神话,经过如此久远的传说过程,它与地下出土的文物之间很难建立令人信服的直接联系。就是说,一味地要求地下考古资料证明神话传说中的神只的真实存在,是把神话等同于历史,如同把文学艺术等同于现实生活一样,这是神话研究的死路。因为,神话不是历史,它是远古先人观念的产物。如果摆脱历史主义的束缚,恢复女娲、伏羲传说的神话面貌,那么只要能够证明这神话的源头在哪儿,就证明了那里是神只的故里。所以,神话人物的故里就是神话传说的源头。由于神话传说年代久远,流布极广,其起源地究竟在什么地方,几乎成为不可知的谜。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三种方法追溯神话传说的源头:首先追溯文化的源头,因为神话是重要的文化现象,文化的起源是神话起源的现实基础,甚至文化的起源与神话的起源是同步的;其次是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对文化起源的确切地点加以证实;第三是将远古神话与民间信仰加以区别,将神话与其在传说过程中的粘连及复合物进行剥离,尽可能将神话的原初形态呈现出来,然后将各地的神话传说加以比照,哪里的神话最具原初性,那里就最可能是该神话的起源地。
(一)追溯文化的源头
女娲、伏羲虽然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只,但也被传统史官们誉为三皇之首,所以追溯女娲、伏羲神话的源头,自然要追溯中华文化的源头,因为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起源相一致。女娲、伏羲并不只是汉族神话传说中的神只,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先神,而且女娲、伏羲的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也遍布中华大地。那么女娲、伏羲神话的源头究竟在什么地方,就要看有女娲、伏羲神话传说的地区,谁的文化起源更久远了。
然而,关于中华文化的源头问题,观点并不一致。主要分歧在于一元还是多元。一元论观点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只有一个;多元论观点则认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一个。而一元论或多元论观点内部也有分歧。一元论观点的内在分歧在于,这一元是源自西方还是源自中华大地;多元论观点的内在分歧在于,这多元是哪些元,各个元在文化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是均衡的还是不均衡的,也就是说,这多元的文化源头哪一元是主要的,哪一元更为久远。这些分歧目前还没有定论。
自17世纪西欧开始对中国有所了解起,就有人认为中国人与中华文化不是中华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埃及。以后又相继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源自西亚、中亚、南亚或东南亚。于是就有所谓“西来说”、“南来说”,还有认为来自西伯利亚、蒙古的“北来说”。如此等等,一句话,皆可归为中华文化“外来说”。其中’曾经产生过相当大影响的是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始终备受国内外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重视。从考古学在我国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这长达数十年的国际论争。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于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开始了对我国第一次考古发掘之后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为早已存在于部分西方学者头脑中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作了历史背景的诠释。文化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虽是两个含义不同的问题,但两者却紧密联系。然而,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不断证伪着“西来说”的观点。到了20世纪40年代,“西来说”基本不再占据主流,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销声匿迹。中华文化本土生长说和中华文明独立起源说以其不可否认的事实逐渐为包括安特生在内的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虽然,偶尔还能听到个别人持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观点,甚至主张中华文化源自于“苏美尔”,但这种观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已经不值一驳了。中国文化起源于华夏大地,是本土生长,多元发展的,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有一个总的趋势,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被发现,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起源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一致,也越来越接近历史事实,这表现出我们对自己民族和文化起源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一方面不断摆脱崇洋媚外的殖民心态,另一方面也逐渐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从而使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起源的认识不断地走向深化,不断地走向理性和科学。
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同样经历了这样一种从一元到多元的曲折的认识过程。19世纪中叶’埃及被认为是世界文明的唯一发源地,其他地方的文化都是以埃及为中心四下传播的结果。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这种观念早已不再被人提及。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埃及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之源,世界文明的起源地还包括两河流域、中国、印度和美洲,世界文明的起源也是多元的。
中华文化本土生长、独立发展的事实,目前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但是中华文化起源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学术界依然存在争议。以往,中原地区一直是全国考古工作的重点,因为这里是夏商文明的发祥地。也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总是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摇篮。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进人蓬勃发展时期,考古学科可谓硕果累累,其中史前文化研究尤其为我们追溯中华文化的起源以重要的启示。
要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地下发现的材料提供证据,而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科学依据。虽然,许多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有些重大问题还缺少关键性的环节,但是根据我国旧、新石器考古发掘成果和人类学研究的进展,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起源的角度进行总结,我们不仅彻底推翻了各种中华文化“外来说”,而且还使认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一元论的传统观点得到了修正。
考古发掘材料还证明,中华文化在新石器时期的发展就呈现出多元性的特点,就其区域分布而言,就大致包括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四个文化区:
其一,黄河中游区域。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陕甘交界一带,北涉长城一线,南至汝、颍上游,即河南中部。时间在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000年。
其二,黄河下游区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地区为主,向南延伸到淮河以北,东沿东海,北达辽东,时间为公元前5400年~公元前1500年。
其三,长江中游区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迄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东端,北达豫南,时间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400年;是楚汉文化的前身。
其四,长江下游区域。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迄杭州湾地区,北以南京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时间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200年。
当然,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远远不止这些区域。1986年在巴蜀地区发现的巴蜀文化,不仅对一元论观点是个猛烈的冲击,而且为中华文化又增加了一个发源地。三星堆一、二号祭坑出土的金、银、铜、玉器,既有殷商文化的因素,又有巴蜀文化的特色,尤其是身高1.72米的青铜人像、铜面具、同真人头像大小相仿的青铜头像,均系我国首次出土。这是我国首次在中原地区以外发现的早期文明,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它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并驾齐驱。这个发现为文明起源多元说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我们今天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在我国的史前时期存在着若干个自成系列、特点鲜明、既独立发展又相互影响的文化区。中国的史前文化具有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特点,它既是本土生长的,又是多元发展的。
这诸多的文化区域,在发展水平和时间上并不平衡,也就是说,它们虽然有着统一性,但却并非同步生长和发展的。诸文化起源地的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并不一致,黄河中游区域文化的起点较其他地区要久远些。也就是说,在这多种源头之中,依然存在着一个主要源头。这个源头就是黄河流域文化区。这也许就是中华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的传统观点产生的原因。传统观点的错误并不在于看到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而仅在于持一元论观点,认为此源头是唯一的。虽然现代科学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的源头是多元的,但是并没有也无法否认黄河流域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而且是历史更加久远的源头这一结论。
传统的观点由来已久,自春秋战国时起,人们就认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黄河中下游。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传说中的尧舜投“四罪”于四裔。这“四罪”指共工、欢兜、三苗和鲧。所谓“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余于羽山,以变东夷。”?于是有了“蛮夷戎狄”的称谓。古代这种既歧视周边少数民族,又认为它们与华夏同出一源,而必须服从汉族统治的正统观,影响是很深的。即使到了清朝末年,当时满清统治者依然将西方列强称之为“夷”,正是这种传统思想影响的表现。
然而,这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根据当时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写的中国远古历史。他没有提及女娲、伏羲,是因为他不相信神话具有信史价值。但是,五帝并非中华文化历史的起点,五帝之前自然还有过漫长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女娲、伏羲等神话传说虽然不是信史,但它反映了中国远古时期的一段历史状态。因为,神话是观念的产物,观念是现实的反映,神话不是历史,但它折射历史。女娲、伏羲神话所折射的历史比尧舜时期还早,而且还是尧舜的祖先。黄河中、下游并非尧舜的起源地而是他们崛起的地方,所以他们的源头应该更往西。时间的上溯与地缘的回眸往往有一致性。壳舜是从西向东发展而来的,那么中原的西部就是更久远的文化发源区域。这个更久远的文化区域通过考古发掘已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就是甘肃东部一带的广袤土地。远古称“成纪”,中古称“秦、雍”,现在称“天水”。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以大地湾文化遗址为代表,其最底层文化遗存的时代远远早于中原地区的黄河中下游文化。
(二)考古发掘的证明
当然,甘肃省东部的地理范围要比“天水”大得多,主要包括天水、平凉、庆阳三地区以及定西地区东部、陇南地区北部。从水系的角度看,主要是泾、渭河流域以及西汉水的上游地区。在这片土地上,陇山纵贯其间将其分为陇东、陇西两块黄土高原。这里有大地湾前仰韶文化遗址,而且通过近年来考古部门在这个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的调査和发掘,包括对师赵村、西坪山,镇原的常山,甘谷的毛家坪,合水的九站,崇信的于家湾等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人们初步弄清了这些古文化的面貌并且建立起这一带的文化发展谱系。初步的考古发掘材料证明,该地区至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古人类生存,目前已有陇东泾水流域的“泾川人”和陇西渭河流域的“武山人”人骨化石发现。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已经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进程、各阶段的面貌以及内部外部相互之间的联系。在大地湾、天水师赵村、西山坪、西和宁家庄发现了7000年以前,即新石器早期的农业文化,说明甘肃东部是我国远古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这是一个发展历史久远、文化绵延不断的地区,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出现文明的因素。正是在这里,至今广泛流传着女娲、伏羲的传说。天水有伏羲庙,秦安有女娲洞,民间对女娲、伏义的信仰依然很兴盛。虽然考古发现不能为神话中的神只或传说中人物提供直接的实证材料,但是地下考古材料却能够证实一种文化和观念的存在。而这种文化观念往往会与当地的神话传说具有一致之处。这就间接地证明了神话源头之所在。
(三)区别神话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