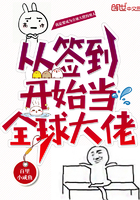她心里一颤,不知为何,竟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他看着心疼,俯身吻去她脸上的泪,咸咸的、涩涩的,她终于忍不住低声地哭了出来,他亦已无法忍受,狠狠地吻上了她的唇,辗转、吮吻,他的舌在她口中攻城掠地,那样的疯狂,她觉得自己就快要窒息,他却适时地度给她空气,她的力气像是被人抽尽,意乱情迷,她禁不住伸出手去揽住了他的腰。
她只是被他诱惑了,好像在梦中,她还可以离他这么近,在她一伸手就能够到的距离。
“咚”的一声,卷轴落地。
不过是片刻的失神,天地已经变了方向,她被他打横抱起,他就伏在她的耳畔,轻声道:“流年,我想要你。”
有泪珠跌落,她知道她应该拒绝,可却像是失了声音,说不出一个字。他抱着她走进卧室,将她轻轻地放在床上,将她脸上的泪一一吻去,那般的小心翼翼,如同对待一件稀世的珍宝。
呼吸都变得炙热,他伸手解开她衣服的扣子,一颗一颗,他吻着她,大掌已探入她的里衣,触碰到了她光滑的肌肤,他的手上带了些许凉意,激的她不由得缩了一下,他却已径直撩开了她衣服。
她没有推拒,眼眶里不断地有液体滑出,她的内心有着片刻的迟疑和挣扎,却还是微微地仰起头回应了他的吻。
寒夜、故地,青丝散乱,他的进入让她觉得有些许的痛,却远抵不上心中那份绝望带来的窒息感,眼泪似乎没有停止过,她抱着的和抱着她的人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到她觉得就好像是在梦里。
她轻声地唤:“止墨…”一次又一次,明明已经绝望,却还能感觉的失望。窗外是漆黑的天际,连星星都无,她的心也仿佛坠入了这无边的黑暗中,再也不想醒来。
脑子里仿佛已经空了,她什么都不愿再去想,这一刻就是永远,就是天长地久。
不知道纠缠了多久,她才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意识模糊之时她似乎听到他在她耳旁说:“流年,我爱你,永远。”
她微微笑了一下,好像是这样回答他的:“止墨,我不恨你,永远。”
这一觉睡的格外的踏实,想念了许久的怀抱让她舍不得离开。潜意识里抗拒着清醒,醒来就意味着不得不分开,哪怕是一直睡下去呢,她宁愿溺死在这样的温暖中!
可是终归还是醒了,像是被人从悬崖上推了下去的感觉,心里似乎空了一块,她一下子就睁开了眼,入目,是白色的天花板,伸手,身边的人已经不在,余温还未来得及散尽。
她裹着被子爬起来,习惯性地拿起床头柜上的杯子喝一口水,可是还没有咽下就忽然想起昨天晚上她和染止墨都是临时过来的,这里又怎么会有接好水的杯子?
心像是被谁揉捏了一下,她放下杯子,不经意的一个偏头就看到了柜子上面放着的东西--苏轼的那幅字,上面放着一张纸条写着:再见,流年。
刚劲有力的字,就像他的人一样,是她逃脱不了的梦靥。这是别离,他和她说“再见”,也许是再也不见,她突然记起昨天下午的时候他在医院没有分成的那个梨,记起昨天晚上他欲言又止的那句话,不安的感觉再次袭来,她想做些什么去阻止它的蔓延,却无力阻止。用被子更紧地包住自己,她抱住双腿,整个人蜷在一起,低低地哭了出来。
离开的时候,流年从口袋里拿出了止墨让伊落落转交的那块表放在了床头柜上,她在止墨的那句话下面写道:止墨,如果还有再见。
鞋柜上有备用钥匙,流年出了屋子,想要再向里面多看一眼,最终却一狠心,用力将房门关了上。
好像有幕帘徐徐地放下,隔开了台前和幕后,这就是散场,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过各自天涯,再无关联。
终只是离开,就好像从没有来过一样。
请了半天的假,流年回到家,找来锯费力地将卷轴锯了开,这一次,她竟然真的猜对了,这卷轴里果然有东西,她放下锯,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拿出那些卷在一起了的纸,一打纸,每一张上面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流年辨认了一下,发现这竟然是个账本!
将另一个卷轴锯开,里面同样是记满账的纸,一张张地翻看,她看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还有一个个很大的数字,其中包括邵启仁,下面的数字是:190、320、187、278、579…单位是万。
在这一瞬间,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止墨和邵启仁都那么在意父亲留下的东西,为什么邵启仁再三嘱咐她找到什么东西一定要交给他,原来是这样。
流年清楚的知道自己手中的东西足以让本市半个领导班子重换一批,攸关身家性命的东西,没有人会等闲视之,她想起止墨对她说的那句“无论你找到什么都不要把它交出去,更不要拿它做任何交易”,还有那句“这段时间…要保护好自己”, 她只觉得像是坠入了一个无底的寒窟。
当初到底是为什么,父亲宁愿将所有的骂名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也没有把这账本交出去?又是为什么,止墨和她说的是不要把它交出去,而不是把它交给他?
流年觉得心都要跳出来,太多的问题需要一个答案,她拿着纸的手不由更加用力了几分,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先将它收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她有一种预感,这东西不久以后一定会被用上的。
下午去了报社,陈姐的脸色不太好,流年却还不得不火上浇一勺油,对陈姐说她没有办法完成采访染止墨的任务。
虽然这任务的确困难了些,但陈姐的原则一贯是只看结果不管原因,流年此次出尔反尔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她自知理亏,低了头老老实实地认错。
陈姐听到她的话,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有失望的神情流露,却只是冷冷地说道:“你出去吧。”
随后的几天,陈姐再没有单独找过流年,就算有任务也是让别人带给她的,比起这样,流年更希望陈姐骂她一顿,至少内心的愧疚不会像现在这样与日俱增。
她其实很害怕别人信任她,因为她害怕最后让别人失望,就像现在,然后,眼睁睁的看着曾经的那份信任消失,相比之下,她宁愿从来没有过。
上下班的时候偶尔会看到陈姐,她的脸色不太好,同事议论说陈姐最近比原来还容易发火,主编办公室都快成了地狱的代名词,被冷落了的流年又似乎是被特别照顾而幸免遇难的对象。
有时能从电视里看到染止墨,不久前本市市委书记因涉嫌参与到洗黑钱一案中而被双规,染止墨作为案件调查的主要负责人和新任市委书记的竞选者,即使生病在医院却也难免忙的厉害。每当看见电视上出现那张熟悉的面孔,流年原本调着台的手就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动作,她一直注视着电视,过了很久才忽然回过神来,然而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继续调着台。
她看着他,像是在看另一个世界的人,可她却常常沉浸在那个世界,不能自拔。
大约是过了半个月,星期一的早上,流年照常去报社上班,不经意地一瞥,竟看到来上班的陈姐脸上带了一份笑容!
流年的心不明原因地开始发慌,整个一天心都没能安定下来,眼皮一直在跳,流年感觉到莫名地恐惧。
这一天过的小心翼翼,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临近下班,流年收拾东西正准备回家,老白却忽然一路小跑进了报社,口中喊着:“拿到了拿到了!”
他大口地喘着气,周围的人不由奇怪地问道:“什么?”
“市委副书记涉嫌贪污案的最新情况!”
流年的脑子里“嘭”地一下炸了开,一日的反常终于找到了缘由,然而她还是强装出镇定的样子,心里安慰自己道:不会是他的,市委副书记不是还有一个人吗?叫什么吴…吴什么来着?
流年正努力回忆着那人的名字,只听社里其他人问道:“是那个姓吴的吗?”
老白摆了摆手说:“不是,是染止墨!”
三个字,如同雷轰一般,流年当场呆在了原地。
怎么会…怎么可能…染止墨怎么会和贪污这两个字挂上钩?
不敢相信的不只是流年,社里自有对这位形象与能力俱佳的市委副书记心存爱慕的女子,难以置信地说道:“怎么可能?”
老白不以为意的说道:“你怎么知道不可能,你见过他几回啊,知人知面还不知心呢!”
那女子还想要反驳些什么,可是却又什么都没说出,只是不甘地咬住了下唇。
的确,知人知面不知心,就算流年从小和他一起长大, 也毕竟有七年的时间是空白,谁又能说的准他是不是变了呢?
然而就是从心里的笃定,笃定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即使天下的人都怀疑他,她也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他。
流年的手不由自主地攥紧,脑海里不断地回放着最后见到他那个晚上的情形,她想起他说的那句“这段时间…记得保护好自己”,似乎有寻出了更深一层的解释,他难道早就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事?
脑子里乱成一团,她拿出手机,一遍又一遍地拨着染止墨的电话号码,却始终没有人接,不知是他接不了电话还是故意不接她的电话。
心里的担忧让她坐立难安,手机偏巧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她接起,伊落落焦急的声音传来:“流年,染学长出事了!我听我在检察院的表哥说…我听说是因为他负责的那个案子,听说有人故意要报复他!”
心里的猜想被证实,她就知道这是一定另有隐情,可如果他猜到对方的意图,为什么不提前防范?还是说对方人数太多力量太强,根本防范不了?
流年不由陷入了沉思,到底是谁…会是谁这样做的,那洗黑钱的案子里又有谁逃脱了呢?
洗黑钱…贪污…脑子里迸出一个火花,就在这一瞬间,流年忽然想起自己从卷轴里找到的那个账本上记录的人名,难道说会是他们?
他们应该是免不了被牵扯在其中的!
想到这里,流年对电话那边的伊落落说道:“落落,你能问下你的表哥,他能想到的想要报复止…染止墨的都有谁吗?”
“我试试看吧,但是流年…”伊落落的话还没有说完,流年就已经接了过去:“我明白。”
只怕对方大多都是高官,伊落落的表哥能够告诉她有人想要陷害染止墨已经很不容易了,具体的人,没有确凿证据,他又哪里敢瞎说?
“恩,流年,别太难过,我相信染学长一定会没事的!”伊落落安慰流年道。
“我知道。”
流年和自己说,不难过,因为他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他出了这样的事,她该像电视里那些复仇的女主一样,满怀欣喜,感叹善恶有报,当初他利用了她,如今也轮到他尝尝这从高处跌落的滋味。
流年一下子冷静下来,她说不恨他,却也不代表着她可以毫不介意当初,他该怎么样,要怎么样,都已和她无关,更何况他既已猜到会有这样的情况,总会有办法应对的,她又在这里着些什么急?
想到这里,流年走出了报社,像平常一样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