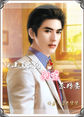在法兰克福的那段时光里,我经历到的不仅仅是那些寄居在夏洛特膳宿公寓里的人。由于这样的经历每日都在延续,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而它不可低估。就餐的时候,大家总是在固定的座位上就座,坐在自己对面的也总是同一个人,因而他对自己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形象。大多数人总保持一成不变,他们嘴里永远不会说出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但其中一些人会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天性,如果他突然发生转变,是会令人感到吃惊的。这就像一出戏,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而我没有一次不是带着急切和好奇走进用餐间的。
对于学校里的老师,除了一个人之外,我都不感兴趣。脾气暴躁的拉丁语老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会大发雷霆,然后骂我们“大笨蛋”,这还不是他唯一的骂人话。他的教学方法很可笑,要我们必须背出那些“例句”。出于对他的厌恶,我没有忘记在苏黎世学到的拉丁语,这真值得惊奇。他冲动时的那种难堪与喧嚣是我在任何一所学校都没经历过的。战争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一定是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为了能稍稍感到好受一点,有时候大家私底下就这么说。有些老师身上的战争印记尽管不明显,但还是能看得出来。他们当中也真有一个非常热情的,对学生的感情都要漫溢出来了。还有一位出色的数学老师,自身有点精神错乱,不过他的精神错乱只作用于自身,而不会针对他的学生。他上课时全身心地投入,认真的态度几近惊人。
我简直忍不住想通过观察这些老师来描绘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不同影响,但要想这么做,必须了解他们的经历,而他们对此却从不提起。我只看得到他们的面孔和外形,只熟悉他们在课堂上的举动;除此之外,有关他们的任何事情都只是道听途说。
但在此我要提到一个内向而正派的人——盖尔伯,我们的德语老师,对他我怀有感激之情。与其他老师相比,他为人谨小慎微。通过作文,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形式的友谊。作文的题目都是他确定的。起初,这些作文让我感到乏味,它们往往是有关玛丽·斯图亚特[3]或是类似的内容,不过写这些东西不费什么力气,而且他对我的作文也相当满意。然后,题目逐渐变得有趣,我可以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是对学校的不满,因此已经是相当地反叛了,而且肯定也不符合他本人的观点。但他却接受了它们,用红笔在结尾处写下长长的评语,给我一些东西去思考。写评语时,他非常宽容,对我发表个人观点的方式大加赞赏。而他表示异议的地方,我也从没当成是反对意见,就算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对此我也感到高兴。他不是一个会激励人的老师,却非常善解人意。他长得小手小脚,举手投足的动作幅度也很小。要不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慢吞吞的话,那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给人的感觉都稍稍弱化了,就连他的声音都不同于其他老师,不是那种喋喋不休、令人厌烦的男声。
盖尔伯将他管理的教师图书馆向我开放,我想读多少,他就借给我多少。我痴迷于古典文学,一本接一本地读着德文译本:历史学家、戏剧家、诗人、演说家,只有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还没有去碰。其余所有领域我真是全都涉猎过,不仅仅是那些大作家,还有另外一些仅仅提供了素材的作家,也令我感兴趣,例如迪奥多拉[4]和斯特拉博[5]。我无休无止的阅读欲令盖尔伯惊异不已。两年以来,我从他那里只借阅这方面的书籍。当我开始读斯特拉博的时候,他轻轻摇了摇头,问我要不要换一本,去读读中世纪的作品,但当时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一次,当我们在教师图书馆碰到的时候,盖尔伯小心翼翼地、近乎温柔地问我将来想从事什么工作。我已经感觉到他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了,但我却说是医生,虽然有些迟疑。他很失望,考虑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那您可以成为第二个卡尔·路德维希·施莱希[6]。”他很欣赏此人的回忆录,但他更希望我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他,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从此以后,一旦能扯上些关系,他都会不经意地提起这位经常写作的医生。
在他的课上,我们会分角色朗读节选的作品。老实讲,我不觉得这有意思。但这是他的一种尝试,希望让那些对文学不怎么感兴趣的人,通过担任一个角色来融入进去。他很少会选那些无聊透顶的文章。我们读的是《强盗》[7]、《艾格蒙特》[8]、《李尔王》,而且还有机会去剧院里看这些戏的演出。
在夏洛特膳宿公寓里,人们常会谈起剧院里的演出,还会对此展开深入讨论。他们以《法兰克福报》上的评论为出发点探讨着,即使持有其他观点,也会对那高品位的、印刷出来的主流观点表示自己的敬意,而且因为总有房客中的内行们参与,所以,这类谈话具有一定的水准,也许还比谈论其他事情的时候更加严肃。大家十分关心戏剧,并为此感到自豪。如果演出失败了,人们会感到震惊,而且不会满足于单纯的轻蔑的攻击。剧院是一处得到公众认可的机构,因此,即便是那些平时站在大家对立面的人,都不敢轻易触及这个话题。舒特先生因为重伤致残,几乎从来不去剧院,但是大家可以从他那不多的话中听出,他会从昆迪希小姐那里了解每一次演出。他的话听起来十分肯定,好像他亲自去看了一样。谁要是对这个话题真没什么话说,就会保持沉默,要是在这方面出了洋相的话,那可是最让人难堪的了。
由于一般所谈论的大多数事情看上去都不太确定——一切都摇摆不定,而且并不仅仅限于表面,当各种观点相左的时候——因此,像我这样年纪轻轻的人就会觉得,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东西,那就是戏剧。
我经常去剧院看演出,有一场戏尤为吸引我,我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去看了好几次。剧中出现了一位女演员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时至今日,我眼前还会清晰地浮现出她的样子:盖尔达·穆勒扮演的彭忒西勒娅[9]。这一狂热融进了我的身体,对此我从没有怀疑过,我对爱情的认识始于克莱斯特[10]的剧作《彭忒西勒娅》。她给我的感觉就像自己当时在读的一部希腊悲剧《酒神的伴侣》[11]。亚马逊人作战时的野性就像疯狂的女人在撒泼,在克莱斯特的作品里,活活地将国王咬得粉碎的不是那些行动如闪电般的人,而是彭忒西勒娅本人,她放出群狗撕咬阿希尔,并且自己也加入其中,将自己的牙齿嵌进他的肉里。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勇气观看舞台上的这一幕,而我每次读到这部分的时候,就会听见她的声音,并且这声音从此未有减弱。我对这位女演员保持着忠诚,她向我说明了爱情的真谛。
我没把这与公寓里隔壁的哀求联系起来,《一个傻瓜的忏悔》也仍被我视作谎言。
在那些经常出场的演员中,卡尔·艾伯特最初是经常登台表演的,后来就只是客座演员。数年之后,他因与此无关的其他事情而名声大噪。早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扮演的是卡尔·摩尔[12]和艾格蒙特。我习惯看他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会就冲着他去看演出,而且从不为此感到羞愧,因为我在法兰克福的那段时光里经历的最重要的事情就归功于此。在一次周日的早场演出中,他要朗诵一部我还没有听说过的作品,是一首巴比伦的史诗,年代比《圣经》还要久远。我知道,巴比伦那里也出现过《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据称,那里的传说后来被记载到了《圣经》中。这些就是我所能期待的一切,但倘若仅此而已,我是不会去的,然而,朗诵的那个人是卡尔·艾伯特,而我又狂热崇拜这位值得爱戴的《吉尔伽美什》演员,他对我的生活、对生活最本质的意义、对信仰、力量和期待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比拟的。
吉尔伽美什因朋友恩奇都死去而作的悲诉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为了他,我日夜流泪,
我不承认人们已经埋葬了他——
我的朋友是否会因为我的呼唤而站立起来——
七个白昼七个黑夜,
虫子已经侵蚀了他的面孔。
自从他去了那里,我不知道怎样生活,
像个强盗一样在草原上游荡。
接下来是他反抗死亡的行动,他穿越天山的黑暗,横渡死亡之水,找到了自己被从洪水中救起的祖先乌特纳皮施提姆,这个被上天赐予不死之身的人。吉尔伽美什想从他那里得知自己如何才能长生不死。是的,吉尔伽美什失败了,自己也死了。但这却增强了别人对他这种行动必要性的认同。
从听到这个神话起,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以多种方式对它进行反复思考,但却没有一次认真地质疑过它。由此我知道了神话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我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接受的,在我的心中它也是一个统一体,对此我不能吹毛求疵。至于我是否相信这个故事,无关紧要,面对我由之构成的这最本质的东西,我怎么能决定自己是否相信它呢。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至今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并不是目的,关键在于做出决定,人们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还是抗拒它。通过抗拒死亡,我获得了感知光辉、财富、痛苦和绝望的权利。我生活在这无尽的反抗中。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会失去周围的亲人,如果这种痛苦毫不亚于吉尔伽美什失去恩奇都之痛,那么,我至少有一点是胜过这位巨人的:我关心的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不仅仅是我的亲人的。
在那个喧嚣的年代里我碰到了这首史诗,它集中表现少数几个人物,与这个时代形成鲜明的对比。记忆中的法兰克福岁月充斥着带有公众性质的事件,它们接踵而至。此前总是谣言满天飞,公寓的饭桌上充满了各种谣言,但未必都是假的。我记得,关于拉特瑙被谋杀这件事,大家是早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那时候还没有收音机)。最常出现在谣言里的是法国人。他们占领过法兰克福,然后又迁走了,突然间,传言他们又要回来了。镇压与赔款成了日常用语。在我们学校地窖里发现的军火库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经过调查,证实一名年轻的教师要对私藏军火事件负责,我只是看见过他,他非常受欢迎,是学校里最受爱戴的教师。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最早见到的那些示威游行。示威游行并不少见,并且总是反战的。两派人中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那些站在推翻现政权一边的人,希望通过推翻政府来结束战争,而另一派人的愤怒不是针对战争的,而是对一年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不满。这是最重要的分歧,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了。在一次抗议拉特瑙被害的示威游行中,我第一次对群体有了感性认识。此次经历带给我的影响体现在几年之后的讨论中,所以在此先不多叙,届时再细谈。
在法兰克福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小家庭又是一幅瓦解景象。母亲觉得身体不适,也许她是受不了我们每日的争论。她去了南方,就像她以往多次所为一样。我们离开了夏洛特膳宿公寓,三兄弟一起来到另一个家庭,负责照顾这个家的苏塞太太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就算是自己的母亲也不会这样对我们。这个家庭里有父亲、母亲、两个和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一位祖母和一个女佣。我同他们中的每个人以及住在我们旁边的两三个外国房客都很熟,要想介绍他们的话,非得写一整本书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记下我当时对人的理解。
当时,通货膨胀发展到了顶峰,每日翻番,最终达到了一万亿的程度,这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极端严重的后果,即便它们不尽相同。关注这一切真是件可怕的事:无论发生什么,发生的事情那么多,都是由于唯一的一件事引起的,即纸币的迅速贬值。向人们袭来的不仅仅是混乱,而是像每日爆炸一样的东西,今天这个人如果还余下什么的话,次日就到了别人的手里。我并非只是看到了其总体的影响,我看得清清楚楚,在每个家庭的每位家庭成员身上,最细微、最个别、最私人的事情都起因于同一件事——纸币的癫狂运动。
为了战胜我自己家里钻进钱眼子里的人,我把蔑视金钱当成了某种合理的道德观。我把钱看成是无聊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无法赢得才智。那些屈服于金钱的人,会逐渐因此而变得才情枯竭、索然无味。现在,我突然从可怕的另一面认识了它——它像拿着巨大鞭子的魔鬼,鞭打一切,包括人,还触及他们最隐秘的老鼠洞。
也许正是这件事所引起的外在后果,让母亲逃离了法兰克福。她起初对此漠不关心,但我不停地让她想起这些事。她又回到了维也纳。一旦她的病情稍有好转,她就把两个弟弟带出家门,在维也纳为他们找学校。我还得在法兰克福待半年,因为高中毕业考试就要到了,之后我再去维也纳读大学。
在法兰克福的最后半年里,虽然还是住在同一个家庭里,但我感觉到了完全的自由。我经常参加集会,听夜晚在大街上进行的辩论,听到各种见解、各种理由、各种信念与其他的看法产生碰撞。大家热情地讨论着,激昂万分;我从不参与讨论,只是认真地听别人说,思想很紧张,这令今天的我都感到恐惧,因为我没有反抗的力量。自己的见解是无法承载这种过度的重压的。很多我无法驳斥的东西都冲向我,有些还吸引着我,我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不能理解交织碰撞到一起的语言的分离性。那时,听过他们说话的那些人我都不能知道他们的真实形象,甚至无法模仿他们。我把握到的是那些观点的分离性,认清了各种理由的坚实核心,这就像魔鬼手下热气翻腾的大锅,其中所有的成分都有着自己的气味,都能辨别得出来。
我对人们内心那种不安的感知,后来再也没有像在那半年那样。作为人,他们之间存在很大区别,但这并不重要;在以后的岁月里,假如我回首过去,我几乎是不会注意到这点的。我留意的是每个理由,尽管它们与我意见相左。有些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说的人,对自己演说所产生的影响很有把握,我却视他们为招摇撞骗者。而在大街上,大家东一群西一堆,那些人并非演说者,而是试图说服对方,这时,我能感受到他们的不安,我会认真看待他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将这个时期称为我跟阿里斯托芬学徒的时期,听上去应该不是狂妄或轻率的。当时,我在读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的每部喜剧都源自一个突发奇想,并且每部作品都通篇一致而有力。在我接触的第一部《吕西斯忒拉忒》中,女性对男人实行的“性”罢工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的结束。类似这种奇特的想法,在他的作品里还有很多。由于他的大部分喜剧作品都失传了,因此他的很多奇想自然也没保存下来。我要是没注意到这些与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相似性,那我肯定是瞎了。现实生活的一切也都源自一个前提条件,即纸币汇率的波动。但这不是突发事件,这是事实,正因为如此,这才不可笑,而是可怕;如果人们试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会发现它与那些喜剧是那么相似。人们也许会说,阿里斯托芬式的看问题的方法虽然残酷,但却是唯一能将碎成千份的小部分组合在一起的方法。
从此以后,我对舞台上单纯表现私人境况的反感变得根深蒂固起来。在形成于雅典的新旧喜剧的矛盾冲突中,虽然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毫不犹豫地站到旧的一边。只有将公众当成整体去塑造,我才认为它具有在舞台上表现的价值。那种表现具体人物的个人喜剧,即使它本身不错,我也总会感到有点难为情,而且在这种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退回到藏身之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类似进食一类的原因,我才会离开这个藏身之处。如同阿里斯托芬所开创了的先河那样,对我而言,喜剧的生命力源于自身的一般利益,以及将世界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观察;它可以对之为所欲为,突发奇想,甚至将其推到疯狂的边缘,连接,分离,变换,对比,为新的想法找到新的结构;不重复,不平庸,挖掘观众最后一丝潜力,触动他,攫住他,耗尽他。
肯定是很久之后的反思让我发现,我选择那些戏剧就是为了上述目的,并且在那时就已经定型了。我不认为自己这样做是错误的,否则如何解释我对法兰克福最后岁月的记忆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第一次读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时我就突然发现,现实与阿里斯托芬式喜剧中的世界是同一个。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在这二者之间,一方逐渐变为另一方,这种紧密相连的关系进入了我的记忆,从而使之成为对我来说是当时最重要的事,并且一方对另一方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某个与吉尔伽美什相关但又相对的东西,它涉及的是与其他所有人相分离的单个人的命运:这个人一定会死去,无论他是否接受,死亡都在前方等待着他。
注释:
[1]吉尔伽美什,古巴比伦同名史诗中的人物。
[2]阿里斯托芬(约前445-前385),古希腊剧作家,被公认为“喜剧之父”。
[3]玛丽·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德国诗人席勒曾据其事迹创作了同名诗剧。
[4]迪奥多拉,古代史学家。
[5]斯特拉博(前64-23),古罗马历史学家、地理学家。
[6]卡尔·路德维希·施莱希(1859-1922),德国医生、作家,以其对临床麻醉学的贡献而广为人知。
[7]《强盗》,席勒剧作。
[8]《艾格蒙特》,歌德剧作。
[9]彭忒西勒娅,古希腊神话中的亚马逊女王。
[10]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
[11]《酒神的伴侣》,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
[12]卡尔·摩尔,席勒剧作《强盗》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