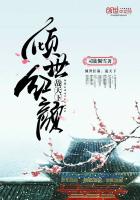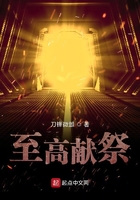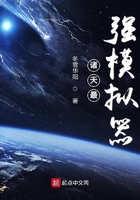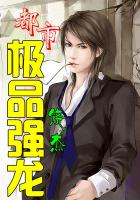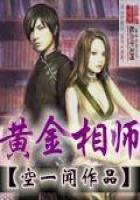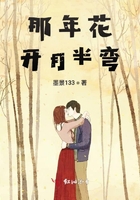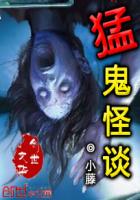罗马的共和政治从来没有达到代议制的性质,也从来没有人想到过推举市民代表来代表市民意旨。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特别注意。罗马的平民会议永远也无法与美国的参议院以及英国的下议院同日而语。在理论上,平民会议包括了全体市民;但实际上,平民会议却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第二次布匿战役后,罗马帝国的普通市民,都落入极其悲惨的境遇中。他们物质贫乏,有的失去了田地,有的被奴隶夺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产业,更糟的是他们失去了可以扭转局面的政治权力。因此,对于失去了任何参政权力的他们而言,表达民意的惟一方式就是罢工与叛乱。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国内政治史,是一篇于事无补的革命运动史。那些企图废除贵族地产,恢复自由农民的田地,免除全部或部分债务的提案,以及其他种种纷乱争斗的情形,本书限于篇幅,实在无法详述。总之,暴动和市民起义连绵不断,扰攘不息。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大暴动,使得意大利人心急如焚。因为这些起义者中有很多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角斗士,所以这次奴隶暴动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斯巴达克斯在当时似乎是死火山的维苏威火山口顽强战斗了两年。然而,这次暴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公元前71年,6000名被俘的斯巴达克斯战士,被残忍地钉死在罗马南边的阿比斯大路旁的十字架上。
平民们终究没能成功地反抗征服和剥削他们的压迫者。相反,那些压迫了他们的大富翁,不但打败了他们,而且在他们自己和平民之上扶植了一个新的势力:军队。
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前,罗马军队都是应征而来的自由农民组成,他们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或骑马、或徒步奔赴战场。这种军队非常适用于近距离作战,但但却无法适应远征或长期征战。随着奴隶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具有自由精神的农民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一位叫马略的农民领袖创建了一种新的形式。迦太基文明没落后,北非成为半开化状态的努米底亚王国。罗马与这个国家的国王朱古达常有冲突,却屡次受挫,始终没有征服它。为了挽回面子,马略被推举为执政官,组织了雇佣军队,进行严格训练,终于击破了朱古达军。公元前106年,朱古达被锁着铁链押解到罗马。马略虽然任期已满,但仗着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军团,仍然继续不法执政。此时的罗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奈何了他。
从马略开始,罗马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军人共和时期。这时雇佣军的领袖们都想统治罗马,于是争权夺利的战争开始了。与马略作对的,是他曾经的属下,远征过非洲的贵族苏拉。他们肆意屠杀政敌,被他们放逐或杀戮的人数以千计,其地产则被拍卖。继他们的血腥火并及斯巴达克斯暴动之后,卢古鲁斯、庞培大帝、克拉苏、恺撒等先后做了军政当局的首脑,控制了罗马政治。克拉苏击败了斯巴达克斯。卢古鲁斯征服了小亚细亚,入侵亚美尼亚,攫取大批财富后归隐山林。克拉苏远征波斯,被安息人打败阵亡。在长期的战乱后,庞培被恺撒打败,公元前48年,在埃及被杀。最后,恺撒硕果仅存,成了罗马的惟一主人。(李军版79左下)
恺撒的故事激发了人类的想象,难以想像其中他的功绩和真实的重要性的合理成分到底有多少。他成了传奇中的偶像或崇拜的象征。但在我们看来,他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初期帝国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从军人共和时期到罗马扩张的第四阶段。当时的罗马虽然国内经济、政治骚动,内乱四起、社会衰败,但其疆域依然在不断扩张。到公元100年,罗马的版图达到了最大的程度。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的扩张进入了停滞的低潮时期。在马略重整军制前,又一次元气大伤,而斯巴达克斯的暴动则使它第三次伤筋动骨。此时,恺撒因征服高卢,也就是现在法国、比利时一带,而一举成名。(高卢国内的主要居民都是属于凯尔特族的高卢人,他们曾占领意大利北部,侵入小亚细亚并定居在该地的加拉太斯。)恺撒将入侵日耳曼的高卢人驱逐出境,并把高卢地区并入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他曾经两次渡过多佛尔海峡(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入侵不列颠,但都遭到了强有力的抵抗。与此同时,庞培大帝也正在东到里海的地方巩固了罗马的统治,并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公元前1世纪中期,罗马元老院在名义上仍然是罗马的政治中心,有权任命执政官和其他官吏,并可以赋予他们种种权利等等。许多政治家仍然为保持罗马的共和传统,以及继续尊重罗马的法律而奋斗,其中以西塞罗最为突出。但是,市民权的精神,已随着自由农民的锐减而逐渐颓废衰微。意大利成了既不清楚自由为何物,也不要求得到自由的奴隶和贫民的国度。元老院里的共和主义领导者已经没有什么依靠力量,而在他们畏惧并想压制的大冒险家背后,却有着强大的军团。克拉苏、庞培和恺撒三个人的势力远远超过了元老院,他们三分天下,这就是最初的三雄执政。后来,克拉苏在卡里尔莱战役中被安息人杀死,庞培和恺撒也决裂了。庞培支持共和政体,以恺撒违反法律、不服从元老院的命令为借口,依照法律通过了传讯恺撒的提案。
当时,卢比孔河是恺撒的法定驻地和意大利本土之间的分界线,如果将军率军逾越驻地是不合法的。公元前49年,恺撒宣称“事已至此,毫无退路”,越过了这条分界线,向庞培和罗马进军。
过去,罗马的惯例是,在军情紧急时候,推举一位权力至高无上的“独裁官”来挽救罗马。恺撒击败庞培,被推举为独裁官,任期10年。后来,他又被推举为终身独裁官(公元前45年),实际上就是罗马的终身统治者。当时也有人主张建立帝制,但自从5个世纪前驱逐伊特鲁里亚人后,罗马人一直对皇帝很反感。恺撒坚决不称帝,但却接受了皇帝的宝座和玉笏。恺撒击败庞培后,曾率军进入埃及,在这片由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国土上,恺撒爱上了美轮美奂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她似乎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把她灌输的埃及“神圣的王”的观念带回了罗马。恺撒在一座神庙内树立了自己的雕像,并刻上了“献给无敌之神”的铭文。然而行将朽木的罗马共和精神,做了最后一击,在元老院刺杀了恺撒,他恰好倒在自己杀死的对手庞培大帝的雕像脚下。
这种个人争名夺利的战斗又持续了13年。其后形成了雷比达、安东尼奥及恺撒的侄子屋大维三足鼎立的第二次三雄执政。屋大维象他的叔父一样占据了贫瘠而多事的西方各省,招募了最精锐的军队。公元前31年,在亚克兴海战中,他一举击溃自己惟一的敌人安东尼奥,成为罗马的惟一执政官。但屋大维和恺撒完全不同。他从未有做神做王等愚不可及的欲望,也没有过令他目眩神迷的皇后情人。他既坚决不做独裁官,而且把自由还给元老院和民众。元老院为了表示感谢之意,仍把实际的权威交给了他。屋大维不称皇帝,而是被称为“元首”或“奥古斯都”(尊严的意思)。就这样,他成为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恺撒(公元前27年至公元14年)。
其后的皇位继承人,依次为提庇留(公元14年至37年)、加里古拉、克芬狄和尼禄。后来是图拉真(公元98年)、哈德良(公元117年)、庇乌(公元138年)和奥勒留(公元161年至180年)。这些皇帝都是行伍出身。军队可以拥立皇帝,也可以推翻皇帝。元老院渐渐在罗马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皇帝及其行政官。至此,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张达到了极点。不列颠的大部分都被并入帝国版图,特兰西瓦尼亚被划分为新省达契亚(即新属地之义);图拉真则渡过了幼发拉底河,而哈德良的做法则可以使我们立刻想起世界另一边(指中国)的情况。与秦始皇一样,哈德良为了抵御北方的野蛮民族入侵而筑造城墙;其中之一横穿不列颠。此外,他又在莱茵河及多瑙河间建造了栅栏,并放弃了一部分图拉真的领土。
罗马帝国的扩张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