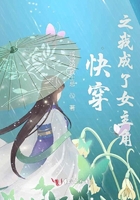浦阳大典当日,集市上人潮涌动,这是几年一度的欢乐时候,并担着祈福,保佑秋收顺利,与接下来的几年都风调雨顺的责任。
陈桐生一大早便起了,站在街口看着百姓来往,脸上都带着被节日气氛感染的笑脸。好几个年轻姑娘此时也挎着花篮,结着伴儿地去集市上卖花。
“怎么不用早饭?”
陈桐生转过身去,看见宋川白笑意盈盈的,清晨的阳光轻薄,落在他发间肩头,是很淡,很清雅的一层金。
陈桐生头一次主动表现出她的无力,说:“侯爷......”念了两个字,自己觉得没意思,于是又转回去,假装自己没有露出过一点带有求助的意思。宋川白站在她身边跟她一起看,看毫无意义的欢欣快乐,浦阳活着的有多少人啊,哪里值得为区区四十条人命悲伤难过,破坏今天的大好日子呢。
宋川白一直很有耐心,懂得不主动才能把握主动权的道理,陈桐生站了半响终于忍不住了,说:“郭福安的,尸体,在安葬地。后山的土,土坑里,埋了,四十三个人,挖出来最小的,还是婴孩。”她伸手比了一下:“只有这么大。”
昨夜陈桐生打着灯,对那个小孩子的遗骨看了很久,仔仔细细地辨认着。
她无法揣摩出那些人的死到底有什么用意。昨夜县令也算是闹开了,他直着脖子说:“怎么禁呐!伽金教中几百人,这飞光现在是收了,可是那些人怎么办呢!杜公子说的是实话,让那些吃过飞光的人戒,那就是要他们的命!下官为什么纵容他们存在,那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呀。几百个人抓起来关在哪里?养在哪里?这批人闹起来怎么办,逼急了给我杀人放火怎么办?!”
可是飞光留下,就有更多人去吃的可能,到时候传开来,浦阳人都不用好好活了!
后来宋川白说,飞光收由官府,由官家的人向上瘾者发放,保证不再流出毒害他人,县令这才罢休,去处理飞光存放事宜。过了半响,县令带着做账的进来了,道:“侯爷,飞光不够。这没收的量,才够不到两年,两年之后该怎么办呢?”
宋川白回答:“这件事明天再说。”
县令以为自己被打发,苦着脸走了。
浦阳像就是一个积埋了无数脏污废料的田土,只要稍微一刨开,便能闻见久积的腐臭气味。偏偏每一任在这里的官吏,都不曾去刨开看过,只是一味地将土堆上去,觉得闻不见,那些东西也就会随之消失。
今日典礼上一定要有老爹,这也是之前百姓去请愿让放人的原因之一。
无论他是否有罪,无论他是否有资格为浦阳向老天求这来年的风调雨顺,按照规矩,应该要老爹在,那么杜善作为老爹,就要在。
出乎意料的是宋川白今日也没有要求县令命人一大早就冲进杜宅,把那个断腿的老东西拎出来问个清楚,相反,他在此时表现出了对浦阳乱七八糟规矩的完全尊重,甚至默许了县令给自己放假。
宋川白问:“去典礼看看吧?”
陈桐生道:“可是......”
“老爹也会去典礼,就算是监视。不跟他见面,怎么好问清楚呢?”
陈桐生觉得有道理,现在黑街也关了,飞光也收了,杜珲春也没放,更何况他们只是发现了尸体,还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能证明杜善跟所谓的安葬地有关系,不能直接怎么样,于是点了点头。
她去的时候没有想其他的,结果一到集市,老远便听见一声:“宋小姐!”
宋川白一扬眉,记性很好,心情也很好地跟陈桐生说:“是那个没出息的啊。”
语气好像看到什么摇头摆尾的大狗。
林风今天把自己拾掇的体面许多,束冠佩玉,照例一站到陈桐生眼前就开始脸红,一看有宋川白在,他脸红更甚,嘻嘻着说:“没想到宋小姐真的会来,这可真是赏了我一个天大的面子。”
“那个......”他挠挠头,十分羞涩的说:“虽然我昨儿跟宋小姐说,今日大典是我主持,但其实不是我......”看见陈桐生疑问的表情,他连连摆手道:“但是我没有骗你啊!也有我,也有我!只是我站在我老板后头,就,就给人家递个东西啥的......也许会有我说话的份儿吧......”
陈桐生也没说穿自己来根本不是为了看他,笑了笑,好心安稳说:“没事。”
这个林风,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是他可能很不简单,陈桐生决定主动出击:“你那天,跟我说的,关于行智的事情,帮了我很大忙,谢谢你。”
他又挠头:“没有,没有,这算什么忙......”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知道,知道什么?”
陈桐生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很随意,很温和,抿出一个笑容来,完全不知道自己刻意笑的多扭曲:“行智调查老爹,这些事情。”
奈何漂亮的人表情扭曲也漂亮,林风毫无察觉地道:“害......”
然后他看看宋川白:“我知道你们这两日在县衙...”又把目光转回来:“我是信任你们才说的,我知道你们有办法。我原不是浦阳人,我娘带着我来浦阳的时候,在城外就被老爹的人抓去了,我后来被广珍行老板收养,才能长这么大。我也看老爹不顺眼啊,但我有什么办法?是行智发现我有时候会跟踪老爹,他主动来找我的。别把我供出去啊,我可不想像行智一样死......”
这时有人过来喊林风,林风又强调了一句:“别说是我说的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说完就扭头跑了。
宋川白低声自语:“装过头。”
陈桐生问:“什么?”
“没什么。”
他们在集市上逛了良久,陈桐生记得郭福安的使,愣是一点儿零嘴也没买。倒是宋川白很有兴致地问她要不要挑胭脂,被陈桐生回以茫然的眼神。宋川白于是开始教导她:“小姑娘不可以不喜爱逛集会,逛集会不可以不买东西,也不能光买吃的。”
他给陈桐生举例子,单是宋芷兰,她发了饷银,第一件事便是去定两件料子时新的衣裳,虽然她做出来都不一定会穿。其次便是首饰,耳环手镯,长簪子短簪子,玉雕的木刻的,带金流苏的不带金流苏的。什么样花色的衣裳配什么款式的簪子,什么样的耳坠子配什么样的手镯子。宋芷兰边买边配,边配边买,夏天什么款式花色的扇子,冬日什么款式花样的扇子......
陈桐生:“冬天还要,买扇子?”
宋川白:“......”
总之要买,各样都不能拉下。
宋川白习以为常道:“你别看我娘常年随夫戎边,她每回回来去买胭脂,都是论箱搬进来的。”
“长公主......用得完么?”陈桐生不由得感受到了一股女人豪气,小心翼翼问。
“哦,她不用。”宋川白说:“她用的胭脂是特制,外面没有卖的,她就是爱把胭脂收集起来。摸摸盒子,看看颜色,再给身边的人擦着玩儿。”
宋川白说完期待地看着陈桐生,显然已经准备看她开启一套宋芷兰式购买模式,在找杜善之余横扫集市,陈桐生感觉他钱都准备好了。
但是她还是要说:“我,没有......”
果然宋川白眼前一亮,早有预谋地从袖中抽出一叠银票,出手迅疾无比,一把塞进陈桐生的手中:“你的饷银。”
范瑞默默站在身后使劲儿拿眼瞟,心中暗自悲愤流泪:好厚一叠!好偏心的侯爷!你分明就很嫌弃宋芷兰,每回她提前把钱花完,去账房预支饷银的时候都会遭到侯爷的嘲笑!你还威胁宋芷兰再不节制,就要扣她钱!
陈桐生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的大约是范瑞两三年的工钱,但银票上面的面值确实不小。
“......”陈桐生说:“这么多,侯爷,我这是要签,签卖身契了吗。”
“多么?”宋川白装傻:“宋芷兰一次也要花这么多吧。”
范瑞:“?”
你骗鬼。
陈桐生:“???”
原来在侯府当差有这么多钱的吗!还是说因为宋芷兰跟侯爷有一份亲缘关系所以领的钱额外多?那我为什么拿这么多钱?
当街跟宋川白推诿起来是不现实的,他全然没有给出去又收回来的理由。陈桐生想起了,她小些的时候干过一件很蠢的事情,那时宋川白来见方鹤鸣,那一年冬天没有下雪,显得很干。宋川白穿着大氅,看见陈桐生,便叫身边人封个红包给她意思一下。
陈桐生不愿意接,她记忆里红包是长辈封的,宋川白架子挺大,可是看上去年纪未必比她大,更何况那红包封的也大,这就不禁会令人想到另一层含义。方鹤鸣身份特殊,他自己要注意,他身边的人也不是什么都能收的,陈桐生从小养成了这方面的警惕性,方鹤鸣又不在眼前,她更不敢收了。但是对方好像地位很高,拒绝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陈桐生接了红包,突然一撒手,做作捧读:“哎呀,掉了。”
封红包的下人:“?”
当时的宋川白:“?”
陈桐生愣着不动,下人赶快去给她捡,结果就在趁人家捡的空儿,她飞速地行完礼脚底抹油告退了。
这件事本来她也记得不是很清了,但方鹤鸣有事没事就拿出来提,说宋川白笑了她一整天,临走了想起来还在笑。
念及到此,陈桐生以史为鉴,痛定思痛,不动声色地道了谢收下钱,决定找个空悄悄地塞回去。
宋芷兰一次能有这么多银两?
她才不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