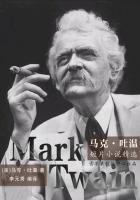“我不会让她们活。”
地上的女子一言不发,只是跪在地上,而陈桐生在紫烟中站着,也未发出声音,一时间这屋内乃至整个祭司的宫殿,都寂静无声,犹如被黑夜笼罩。
陈桐生有些奇怪地抬了抬头,想听见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听见。
只有极其轻微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呼吸声罢了。
陈桐生之前离开京都四处闯荡查案时,很少到这样寂静的场景中去。世人都说乡野清净,实际上乡野中鸟鸣不断,路上有时遇泉水,有时遇见什么警觉野兽动物,哪怕是在夜晚,都能听见不断的虫鸣蛙叫,只有在城镇中,才会遇到如此没有生机的寂静。
只有在人都睡去了,不再活动,整个城镇都归于沉寂时,才会有这样安静而突兀的气氛。
陈辛澜的行宫就在皇宫之内,也不偏僻,怎么这样安静?
“你今日去找陛下,为的是什么?”陈辛澜终于说:“是谁告诉你的那些话?”
说着目光往站得最远的宋川白身上扫去,陈桐生立即道:“不是清临。”
“哦?”陈辛澜冷笑着说:“那就是另外几个不安分的了?闻人常,还是北猎堂,还是你爹?”
好家伙,一次性给她又报了三个人出来。
这三个里面陈桐生只听过北猎堂一个名字,在陈辛澜吐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下意识的眉头一动,却被陈辛澜敏锐地捕捉到:“北猎堂么?”
她说着眼神往下一瞟:“北猎堂的倒也够手长的。”
怎么回事?
陈桐生想,难道这个跪着的人,她也跟北猎堂有什么关系?
“重午,”陈辛澜念出地上那个人的名字:“北猎堂这么多年腐朽枯竭,里面的人做事不成,逃跑却很是积极,你把自己的妹妹托付到这些人手上,究竟哪一种结局更好,恐怕也不一定呢。”
“哪怕她死在逃亡的路上,”重午低着头终于发声:“也要比惊恐绝望的就死在这里好。”
“所有我让你不要告诉她,这样她就不会那么痛苦。”陈辛澜:“你觉得呢,桐生?”
陈桐生无话可说,但总要回答,陈辛澜似乎认定了自己已经知道了什么,陈桐生长了张口,说:“我不知道。”
幸亏陈辛澜说的是一个问句,这样回答倒也无可厚非,陈辛澜闻言果然又笑了一声,点了点头说:“也是,你懂什么,你被夸奖的再聪明,也不过是四处听着别人的话,用你那葵花子一样的脑仁去愚蠢地思考这些你根本想不明白的事物罢了。”
陈桐生:“......”
这娘怕是真的很嫌弃她。
现在的对话就像是在打哑谜一样,陈桐生要不停的从对方的话去抓获可取的信息,去猜测对方的想法,即便如此,能得到的消息也非常少。
“於菟,”陈桐生突然开口问:“是什么?”
宋川白明显惊了一下,未曾料到陈桐生在此刻会如此直接。
她根本不想管什么北猎堂什么闻人常,这背后一切的根本就是於菟,只有於菟,倘若已经到了陈辛澜这里,她都不知道自己正在面临什么,那就也没什么必要再耽误下去了。
陈桐生已经感觉到莫名的紧迫了。
总不能这北朝中,知晓偶的只有陈恪吧。
陈辛澜漠然凝视了她片刻,母女对视,陈桐生的眼神完全不属于孩子,半响陈辛澜道:“你已经开始了?”
“我还没有死,但是你已经开始了?”
其余人全部被赶了出去,陈辛澜带着她再次穿过长而窄,墙壁上镶嵌着夜明石的道路,将她领进了陈桐生最开始来到此地见到的那个大殿中,只是这一次那椭圆的大门是紧闭着的,殿内昏暗,星星点点的浮着灯。
陈辛澜脚步不停,径直走到大殿中那面目模糊的神像前,按动开关,那偌大的神像便当着陈桐生的面缓缓转移,露出下面的入口。
“进来。”
自方正的入口下去,又是一条又一条狭窄弯曲的长道,极陡的阶梯走的陈桐生颇为费力,生怕自己一个不注意就一脚踩空,咕噜咕噜地滚着撞到前面的陈辛澜身上去。
前面的道路还装扮的十分讲究,墙既上了浆,又镶着夜明石,还能见零散的壁画,陈桐生没看清上面具体花了些什么,一眼扫过去却能感觉到精致用心。
但随着进入,两边的墙壁便越发的粗糙,简直就像是直接在土里挖出来的道路,一摸便是一手的土渣子。空气也越发的浑浊,夜明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粗暴的火把,脚下分明的阶梯开始变得粗糙。
“知道为什么建的这样窄么?”
陈辛澜冷不丁的说。
“为什么?”
“阻止逃跑,”陈辛澜道:“若是地下出了什么事,地下的人急着逃出,就往往会困在这狭窄的道路里,至少也是被阻碍,无法快速脱身。”
怎么还有人在隧道里起这种心?
陈桐生问:“下面有什么?”
说着陈辛澜推开了两道门,机关运转发出嗒嗒的声音,扑面而来的冷气,来自地下。
陈桐生迟疑地慢慢走下去,终于看见了她梦中无数次见过的神像。
伽拉的神像。
跟神殿中她瞥见的不同,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差不多一人高,还得是那些高个男子的身高。
伽拉神像也不是像以往一般手中拿着淋漓的血碗,也没有穿着冠冕富丽的服饰。而是膝上横置着一把长弓,身后又挂着刀,就是陈桐生记忆里风尘仆仆四处奔波的寻常装扮,闭眼坐于台上。
那神像雕刻的过于逼真,以至于陈桐生产生一种,若你走上前去触碰她的长弓,她便会徐徐睁开眼睛望着你的错觉。
“伽拉,”陈桐生念出她的名字:“伽拉希阿。”
“你果然已经见过她了。”陈辛澜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桐生看着陈辛澜的身影:“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问?难道你知道我能够见到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从你生下来就比寻常孩子伶俐,又比他们古怪时,便能知道了。”陈辛澜说:“你似乎经常做梦,醒来后往往就分不清梦境与现实,虽说讲话比正常的孩子要早,学会走路也比别人要早,但你却总是神智恍惚,后来就不亲近人了。”
“回想我年幼时也未曾有你这样大的动静,只是在正式任职祭司,看见了伽拉之后,才开始频繁地夜梦,出现类似的症状。”
说着她转过头来,语气里是对这循环不断的命运极其厌恶的情绪:“而我也亲眼见过我的母亲,是如何被困在梦境中无法脱身,最终死去的。”
陈辛澜在黑暗中点燃了什么,于是周围骤然亮起一片,陈桐生惊讶地抬眼望去,只见周围墙上挂的都是画像,一个一个年纪或大或小,面目不同的人,接连地挂在一起。
“这又是什么?”
陈辛澜望着那些画回答:“是你。”
“你可还记得你前往神殿的御道两侧排列的石像中,有一个死状看上去极为痛苦的?”
陈桐生应了一声,只听陈辛澜道:“她与你倒是像,也是年纪小小的就表现出了对伽拉的感应,而她本人对此也十分得意,听了关于伽拉故土的传说,便想要去,也不知她顺着伽拉的指示走到了哪里,突然有一日出现在都城的大街中,疯疯癫癫的,再要送她去,她就死活不愿意了。后来将她送到神殿,半夜里,她在庭院中赏月,无端自燃身亡。”
陈辛澜道:“于是后来便传她对伽拉不敬,是个表里不一的叛离者,应当前往伽拉故土,却半途逃脱,所以才招来如此惩罚。”
“真的么?”陈桐生问:“哪里会有无端自燃身亡这种事?”
陈辛澜笑了一声:“谁知道呢,只是像你与她这种天生对伽拉有感应,甚至食用了未曾处理的原液也不会被影响的人,实在也是少见,三四代祭司,两三百年的光阴里,都未必能出一个。实在少见。”
“所以,爹才想把我送去......”
“是,”陈辛澜说:“实际上我与神殿从来不是同一阵营,神殿中人管理原液,与伽拉留下的北猎堂相互连结,而祭司之位,则是在伽拉消亡之后,由一个人建立起来,不同根也不同本,职责也不同。”
“神殿除去管理原液,祭祀事宜,更大限度上尊崇伽拉的意愿,他们为了将伽拉送回故土,哪怕牺牲整个神殿,甚至牵连无辜百姓也在所不惜。而我,”陈辛澜轻描淡写地说:“只用保证伽拉的诅咒能够传下去就可以了。”
实际上只有神殿与北猎堂才是真正的伽拉一脉,而祭司这个位置本来便是於菟所创,与神殿不对付也在情理之中了。
陈辛澜头一偏::“但为了所谓的血脉传承,我们又不得不生下你。”
她说完顿了顿,随即笑了起来。
不是轻笑,也不仅仅是脸上的一个笑容,陈辛澜已经笑出了声,身子不断颤动着,几乎要捧腹了。
“去吧,”陈辛澜手按在她肩膀上,往前一推:“看过之后你也会跟我一样,厌恶这些事情,厌恶着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愚蠢的谎言了。”
“看过之后你就会知道,我们所依托着生存的,是多可笑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