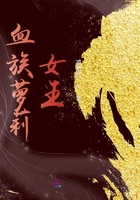“会不会自己穿?”
陈桐生:?
......会吧。陈桐生两只手有些费劲的抓着衣服想,看上去倒也不难,更何况就算她不会,还能让宋川白动手给她穿不成?
......
为什么不能呢?
陈桐生在心里反问:我现在只是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张着手让人服侍着把衣服穿上?
这可是侯爷啊,若是放在平常,能遇到几回这么可以顺理成章让他给自己换衣裳,穿衣裳的时间?
陈桐生心里在拒绝与答应之间反复横跳,蠢蠢欲动,问了一句:“侯爷会穿么?”
谁知宋川白抿唇一笑,非常自然无辜的样子:“我不会。”
陈桐生:“?”
那你给我整的这一句,让我平白地想了半天!
陈桐生脸往下一拉,道:“那还不是要我自己来。”
宋川白便笑起来,还是弯着腰,声音很缓和的说:“但是我可以试一试啊。”
其实被伺候宽衣解带的愉悦只持续了那么一小会会儿,这衣服表面看上去大气,实际上里面带子扣子对襟的云肩的,层层叠叠,陈桐生从一开始的面带得意,到后面面无表情地张着双臂打了个哈欠,百无聊赖地问:“你说龙袍有没有这么麻烦?”
宋川白回答:“没有。但龙袍穿上比这要累。”
陈桐生眨眼看过去,宋川白也把一根长带轻轻从她身后绕过去,顺势对她眨了一下眼。他眼尾修长,这么轻巧如燕尾地一眨,好似一个什么东西在陈桐生的心里跟着那个眨眼的动作跳了一下,闪闪发光的,是一个含满了喜悦的泡泡,彭地一下炸开了,流淌着浸透了胸膛。
陈桐生小小的嘶了一声,短暂的抿了一下嘴,但那股子高兴劲儿,又好像一只摇头摆尾的小狗在心里乱跳乱蹦,要找一个突破口撒爪子奔出去,呼哧呼哧地摇起尾巴表达自己对面前人的喜爱。
小狗在心里蹦着,面上就忍不住,情不自禁地绽开一个好灿烂的笑容了,宋川白低头仔细地抚平衣料,抬头便对上这个笑容,意外的一愣,问:“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看见你就觉得高兴。”
宋川白似乎对陈桐生突然而来的表白已经习以为常了,也就保持着那个笑意,转手拿了镶宝圆环来,示意她转过头去,好为她佩上。
头饰倒没有衣裳戴着那么复杂,很快的戴好了,轻轻动一动,也能听见细碎的玉铃声,脆而空灵,陈桐生摸了摸头饰,还没明白这发声的地方是在哪里,便听得外面有人敲了敲门,谨慎而恭敬的道:“駮车已经等在外头了,请您准备出发。”
除了陈桐生一开始在的那个大殿,其他地方都是冷冷清清的,几乎不见什么人。陈桐生身边似乎也只有清临在照顾,其他的下人竟然也没有见。
陈桐生奇怪地看了宋川白一眼,被抱下圆凳牵着手往外走,边走还边在想这个駮车是个什么东西。
马车她知道,牛车她也知道,这駮是个什么东西?
难道这不是在说什么动物,而是一个车辆的制式?
结果顺着墙壁嵌满夜明石的长廊走下去,越走方向越是往下,这长廊又是如此的狭窄且曲折。头顶的墙壁又越发的低了下来,出现了阶梯,脚下一阶一阶的阶梯也显得比一般的阶梯陡。陈桐生都要担心这是走在了山洞里似的。
顺着长廊走出去,眼前便逐渐开阔,陈桐生眯了眯眼,然后愕然的站在了门口。
她总算是想起来这駮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身形似马,通体雪白,长尾漆黑,头长一角,虎牙虎爪,声似击鼓。
陈桐生站在那个巨大而怪异的野兽前,望着这身宽有两匹马身体大,一呼一吸间喷出灼热鼻息的的巨兽。駮好似注意到她的目光,斜过眼睛,眼神并不如食草动物温和,并且在甩头的过程中,陈桐生还看见了它口中尖锐的利齿。
......她好像记得这种古兽是吃肉的。
还可能吃人。
陈桐生即将登上的车厢巨大,光是拉车的駮便用了三匹,装饰美耀奢华无比,外沿依旧绘满了北朝常见而独有的花纹。
车厢自下而上分了三层,第一层盘位最低,方便人登上去。第二层铺在第一层之上,已经是精雕细琢的剔透软银座,接着一抬脚,再到第三层。第三层立起三面镂空雕花的木壁,下铺白玉,而顶部华盖高悬,在木壁与华盖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隙,足以让陈桐生把脑袋探出去。
然而当她上了车,才发自己如今的身高得仰视那条挺宽的缝儿。手边两只金兽香炉,也依旧是点着迷蒙紫烟,陈桐生低头嗅了嗅,疑惑地“嗯?”了一声,不知是在室外,且用量也小的缘故,这紫烟的香味一点儿都不明显,甚至都说不上香,一股特别的味道在车厢中散开,并不是婉转升向天空,反而盘旋着向下缠在一起,囊囊蒙蒙的一团,围绕着陈桐生的座位徐徐旋转,把她衬得格外如神降之子。
宋川白此时的身份也不能与她同登上内座,只能站在木壁外,但两人只一转头,便能在镂空的花纹中看见彼此的脸。
这是一条长长的车队,陈桐生对这种大型的出行盛况有些印象,心里竟然还有些期待。
除去陈桐生所座的这辆駮车外,其余便是普通的马车,个个高头大马,在駮仰头发出一声响亮的鸣叫后,马匹们纷纷打着响鼻回应,这车队便这么走起来了。
此时陈桐生前后相顾,她方才登上駮车,几乎没有人来迎接,更没有人像大周的皇宫贵族出行一般,跟着几个人来像模像样的扶上一扶,只有一个眉目清秀,眼下绘有两弯淡红的男子,在陈桐生最先走进駮车时,低头轻声细语地说请她上车静待出发,转头便翩然而去,上了另外一辆车,连一个告辞的意思都没有。
陈桐生看他眼下红痕的弧度,以及那身严肃正统的长袍与高帽,便猜想着他大约也是有些身份的。
就目前而至,陈桐生遇见的事物都太过奇怪,皇帝当的不像皇帝,祭司当的不像臣子,母女也不像母女,在这个地方,仿佛一切传统而约定俗成的习惯于伦理都难以成立,直让人不停地想,奇怪,奇怪,奇怪。
车队安安静静地向前走,陈桐生如今身子小,便爬到精致的凳上,扒着往外头看。
即便到了这里,也是一条平坦而寂静的长道,高而疏的林木沿着长道排下去,除去马蹄与车轮声,静谧非常。
駮时以四爪行走,走起路来如同狮虎这样的野兽一般没有声音,陈桐生所座的这个华美而庞大的车厢大约也做工不菲,行进时很是轻便,一路走下去,陈桐生这里的动静又是最小的。
感受到特殊地位的特殊待遇了呢。
陈桐生见道路两旁可见石像,并且安排再次地不符合常理,这两边林道上的石像都是不对称的,一个一个错开,大都是形状古怪各异的兽,偶尔见有人立状,也十分扭曲古怪,不像正经人像。
这是要去哪儿?
再接一段路,便开始爬坡了,陈桐生也没有人能来给她解释一番,不安分的转着脑袋看来看去,却突然见前面突然从正在前进的马车前跳下来一个人,脚步快而轻地走过来,定睛一望,还是开头那个来迎接她人......大概也算迎接吧。那人轻盈一跳便上了三层,动作轻灵地出乎常人,对方双手成掌,前后叠在一起,在他上跳的时候都未见分开,可见其厉害的程度。
他这么一跳,陈桐生反倒还回过味儿了,生出了一点儿“就是要这样”的感叹。毕竟她这无师自通的诡奇身手承自伽拉希阿,她也曾亲自感受过伽拉那如同战神般骇人的战斗力,北朝人要是个个普通斯文,倒还让人觉得不匹配。
那清秀的男子眼睛一垂,表情平板的几乎看不出应有的温和,只是例行公事般的,语调毫无起伏地说:“请您安坐,莫要对伽拉不敬。”
陈桐生看着他,忽然问:“我不尊敬会怎么样?”
清秀的男子不动,宋川白倒让她这一句引得转过头来看。
男子一点儿都不意外似的,对着林道上的一尊石像一指:“就会变成那样。”
你们还真遇到过不尊敬伽拉神的啊?
陈桐生连忙往外去看那尊像,之间石像所雕之人几乎都看不起五官,模模糊糊觉着她的脸是扭曲的,而粘腻的液体拔地而起,自上而下的将她整个包裹住,似乎在向地下拖去,而那个人则向上方痛苦的伸长了手,手臂骨节都是完全扭曲过去的。仔细看下去,仿佛都能挺见她绝望而痛苦的嘶喊。
陈桐生深吸一口气,乖乖地并着腿在椅凳上坐直了。
男子便满意地一点头,转身欲退,听见陈桐生接着问:“是你们杀的么?不尊重伽拉的人?”
“不,您误会了,”男子回头一望,平静道:“她不是死了,只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