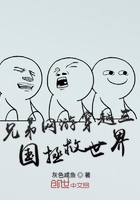阮梫掸了掸烟灰,微眯着眼睛望着黑蓝中透着暗红色的天空,车子的雨刷倦怠地一下一下扫着挡风玻璃上的雨滴。整座城市的灯红酒绿将夜空烤得变了色,仿佛来年真的便是世界末日,饮食男女,人治大于存焉。
烟灰缸里已经扎满了牙签似的烟头,手机忽然有来电,显示是阮宅的。他下意识地猛咳一阵然后才接起电话,听见是周姨的声音,他支起嘴角笑嘻嘻地说:“我这就回去了,老爷子这些天身子还好吧?”
周姨的声音在遥远的电话那头嗔骂道:“隔着电话都能闻到烟味,又不听话吸烟了吧?今天是平安夜,那女人估摸着是趁你不在故意要搞什么庆祝晚会,现在一伙子人都在老爷的房间呢。你快些回来,要让老爷子知道他还生着病你就跑出去瞎混,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蛾子!”
他“嗯”了一声,指间的烟灰已经燃了长长一段的灰烬、随着窗口吹进来的夜风落到他的黑色的西装裤上。车子从医院出来就一直卡在市中心,街上到处是出来狂欢过节的人,三三两两勾肩搭背的,车喇叭和年轻女孩子“咯咯”的笑声在夜风中回荡。
他焦躁不安的伸了伸长腿、煎熬地望着前面像糖葫芦似的一串串艳红的车灯,忍不住扫了一眼后车镜,车厢里仿佛还萦绕着她头发上的馨香。忍着不去向后看的时候,又总觉得她还如很多年前那样总是静静地坐在车后座望着窗外,一双眼睛总是漾着盈盈欲泣的泪光。
堵了近半个小时才终于出了三环上了高速,回到阮宅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房子里静悄悄的。一进门便看见周姨绕着毛线球正打哈欠,客厅里只开了一盏橙黄色的立灯,照得青白色的大理石地板幽幽的。他悄声走过去将大衣披在周姨身上,她打了个战惊醒了、站起来用手捂着阮梫的脸:“怎么这样冰?”见他垂着头不说话,周姨摸摸他的脸柔声说:“回来就好,伤还没好你就一声不吭溜出去了,你要是出了什么差错,我怎么向夫人交代?”
他淡淡笑笑:“我这不是没事么。”他顿了顿,渐渐敛了面上的笑容,“他们还在上面么?”
周姨摇摇头:“都结束了,瞧你这脸色,快去洗了热水澡早点去睡吧,反正明天才是圣诞节,我们俩再给老爷子办一个就是,这回才不叫他们外人。”说着,周姨狡黠地眨着眼睛笑着,紧紧攥了攥他冰凉的手。
阮梫点点头,回了自己的房间,想起了小软,又悄声上楼去看她。孩子似乎睡得极薄,一听见他开门就穿着睡衣睡裤跳了起来要他抱,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小脸贴着他的面颊:“爸爸,小软还以为你们都不要我了,妈妈呢?妈妈也回来了么?我想妈妈……”孩子说着便哽咽着哭起来,又像是不敢,便只小小声地哭泣。
他捧起小软的脸亲了亲,想了许久才柔声说:“妈妈还没回来,过两天她就回来陪小软了。这两天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欺负小软?”
小软眨着含着泪光的大眼睛望着他,一副有话却不敢说的样子。他顿时着急起来,握住小软的两只小手坚定地看着她说:“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不要怕,快告诉爸爸。”
孩子可怜巴巴,一副犯了错的样子小声说:“老师说我学字慢,说其他小朋友都会背三字经了,我连鹅鹅鹅都不会……爸爸,我不喜欢老师,因为她好像不喜欢小软……”
阮梫心疼地揽住孩子小小的身体、紧紧地抱着:“好,小软不喜欢,我们就请别的老师,好不好?以后谁欺负了你都要和爸爸讲,爸爸会永远保护小软的。”
孩子犹豫了一下、重重地点点头,只是看起来却十分伤心,大眼睛总是失落地垂着。阮梫拿过芭比娃娃小套装,从梳妆盒里找出一把粉红色的小梳子笨拙地给她梳小辫子、又讲了几个故事,小软这才安心地睡着了。他在床边守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关上了房间门,走廊里传来的灯光越来越窄,他看着桌子上立着的黑色长发的芭比娃娃晃了晃神。
他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想事情,其实脑子里乱乱地什么也理不清楚,就只是发呆而已。他习惯性地去摸衣袋里的烟盒,空落落的,于是心脏更突突地跳得发疼。等一股脑推开了门,他才发觉自己竟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阮峥嵘的房间,空气里弥漫着的药味更浓烈了些。他刚想转头离开,忽然听到房间那一头传来的沙哑的干巴巴的咳嗽声,一时间便站在原地定住了。
“周姨,是不是小梫回来了?”
他愣了愣,只得硬着头皮走过去,阮峥嵘躺在病床上竟已动弹不得、眼神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他走之前明明还是好好的、金医生还说老头子恢复得不错,怎么只两三天的功夫竟似已病入膏肓了?他不知阮峥嵘此时能不能瞧见自己,面对父亲他一向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什么好说,此时进不能退不是,仿佛有千万根钉子从脚底将他牢牢钉住、嘴巴也木了。
阮峥嵘咳嗽了两声、艰难地用气声说:“这么晚了那浑小子也不知道又去哪里厮混了,快打电话叫他回来,他开车子跟拼命似的,还是叫他坐出租车吧。”
阮梫看着阮峥嵘因长时间卧病在床而有些萎缩的小臂,沉默了半晌,开口说:“爸,我回来了。”
好半天都听不见阮峥嵘的回应,或许老爷子又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了,阮梫不自觉地舒了口气,步子动了动,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他静立不动、竖着耳朵听着床上的动静,空气仿佛凝滞了、隐隐泛着消毒水呛人的味道。他骇然到出神,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这个情景,此时却只是手足无措。
阮峥嵘却忽然“嗯”了一声,再无他话。阮梫看着床上那个熟悉却陌生的身形紧紧攥起拳头,手心里竟满是冷汗,一句话还未来得及犹豫便已冲出嘴边。
“爸,你爱过我妈么?”
阮峥嵘没有作声、安静得仿佛枯木,只等着最后一簇生命之火将自己燃成灰烬,落叶归根,似乎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与空间于他都再无意义。
这样也好,没有答案也好,阮梫转过身,阮峥嵘枯槁的声音却又从背后传来:“我爱过她,只是她一直不肯爱我。我知道,她恨我。”
他猛地转过身来、攥紧拳头盯着床上那个模糊了的身形低吼:“是你对不起我妈!既然你爱她,为什么把那个女人带回家?就算我妈恨你,也是你活该!”他气喘吁吁,胸口翻滚着灼烧的血液。
空气凝滞了半响,阮峥嵘的声音从房间那一头传来,虚弱得如一缕青烟,一阵清风都会吹散,却平静如水。“小梫,我爱你妈妈,但等她去世之后,我就知道我们的婚姻是一个错误。要是没有和我结婚,你妈妈或许现在还过得很幸福,子孙满堂,我们两个都不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阮峥嵘咳嗽了一阵,又支撑着继续说:“我对你从没有过多要求,只要你以后和一个真心爱你的人结婚生子、一辈子平安幸福就够了,我到了那一头也好向你妈妈交代。”
他浑身发抖:“你撒谎!你若是爱我妈,怎么会将她一个人丢在医院、疗养院?如果你当初没有带那个女人回家的话,妈妈也不会气出病,她也不会那么年轻就过世!你一直说我妈不爱你、为了让她宽心才让她一个人住在外面,这不过是你的借口!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妈妈也不会!”
他憋着一口气跑了出去,扶着楼梯走廊的墙壁跌跌撞撞地半走半滑下去,一到客厅便扑到衣架边去找大衣口袋里的烟盒。手指哆哆嗦嗦地点上了火,深深地吸了两口后才慢慢镇定下来,大立钟的秒针“沙沙”转动着,一分一秒、周而复始。他忽然萌生出想把这房子里的一切都砸烂的冲动,他忍了十几年,八九岁的小孩子起妈妈便叫他忍耐、不可任性与“那一房”的惹事生非。
他纵然恨阮峥嵘,却有一句话深深烙印在脑海里,“假如当初我们没有结婚,我和她都不会走向今天这样的结局”。那样的话,妈妈一定会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个世界上便没有他这么个人了,可是那有什么所谓?只要妈妈能幸福快乐就行了,反正这个世界上他也是孤零零一个人,来与不来没有什么区别。
若是没有他这么个人的话,她应该早就与她的教授结婚了吧,那样的话,她也会过得很幸福,至少不会恨他。
这仿佛是记忆中阮峥嵘同他说得最多的一次话,却正中他的要害,将他心头一点点残存的希望都抹去了。若情种便已是坏的,即便长出了情果,等不到瓜熟蒂落果实便会腐败凋落。见过了父母的悲剧,他作为一个受害者,本应该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总会怀念起那一点点甜,她曾经短暂地照亮过他阴暗的人生,便像上了瘾,总想再多要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