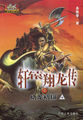几天后,布鲁诺在他的房间里,躺在床上,看着头上的天花板。白色的油漆已经裂了,开始剥落,非常难看,不像柏林的房子有那样好的油漆活儿,那里的墙漆从来不会有裂痕,每年夏天母亲都要请装修工人进行保养。这天下午,他躺在这里,看着像蜘蛛网一样的裂缝,眯着眼睛想像着在那裂缝后面会有些什么东西。他想像着那些在油漆和天花板之间的空间里住着的小虫子,它们在不停地往外推,于是把裂缝弄得越来越大,直到张开来,弄出一条豁口,这样它们就可以挤出来,并从窗户逃跑。布鲁诺想,没有什么东西,哪怕是小虫子也不会选择在“一起出去”生活。
“这里的每件东西都让人讨厌,”他大声说着,虽然跟前没有任何人可以听到他的话,但是他自己听到这些话说出来,还是让他感觉舒服一点。“我恨这个房子,恨我的房间,甚至恨这里的油漆活儿。我恨这里的一切。恨所有东西。”
刚说完,玛丽娅就抱着他的一大堆洗熨好的衣服进来了。当她见到布鲁诺躺在床上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稍微低下了头,安静地走到衣柜跟前。
“你好。”布鲁诺说,虽然跟女佣说话不能跟那些朋友说话相比,但是这里没有其他人可以聊天,况且,有人聊总比自言自语要强一些。格蕾特尔也不见了,他开始担心自己要无聊到发疯了。
“布鲁诺少爷,”玛丽娅安静地回答,然后把他的背心和裤子、内衣分开,分别放入不同层的抽屉。
“我想你跟我是一样的,对这次的安排很不满意。”布鲁诺说。玛丽娅转过身来,用表情告诉他,她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这里,”他从床上坐起来,环顾四周,解释道,“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很讨厌,不是吗?你不也恨它们吗?”
玛丽娅张开嘴想说些什么,但是很快又合上了。她似乎在小心考虑她的回答,字斟句酌,话到嘴边,她认真考虑了一下,又全都咽了回去。布鲁诺对她太了解了--他三岁的时候玛丽娅就来到他们家工作--他们平时相处得非常好,只是她好像没有前半生一样,没有任何信息。她只管做自己的事情,擦洗家具,洗衣服,帮着采购和做饭,有时候送他上学又接他放学,在布鲁诺八岁的时候更加频繁;但是当他九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大了,于是决定独自上下学。
“您不喜欢这里?”最后她就这么问了一句。
“喜欢这里?”布鲁诺微笑着回答,“喜欢这里?” 他又重复了一遍,但是这次声音大了些。“我当然不喜欢这里!这里太恶心了。没有事情可以做,没有人可以聊天,也没有人一起玩。你不会告诉我你来这里以后过得很高兴吧?”
“我很喜欢柏林那个家的花园,”玛丽娅答非所问,“有时候,下午很暖和,我就喜欢坐在外面晒太阳,在池塘边的常春藤下吃午饭。那里的花很漂亮。还有花香。蜜蜂绕着花儿忙碌,只要你不惊扰它们,它们也不会惊扰你。”
“所以你不喜欢这里?”布鲁诺问,“你跟我一样认为这里很糟糕,是吗?”
玛丽娅皱起了眉头。“这个并不重要。”她说。
“什么不重要?”
“我的想法不重要。”
“嗯,当然很重要,”布鲁诺生气地说,好像她在故意捉弄他。“你是家庭一员,不是吗?”
“我不敢肯定您父亲也这么认为,”玛丽娅说,脸上浮出微笑,因为布鲁诺刚才的话打动了她。
“嗯,你被带到这里来,这违背了你的意愿,就像我一样。如果你问我的感受,我觉得我们上了同一条破船,而且现在这船还正在漏水。”
似乎有一个时刻,布鲁诺觉得玛丽娅打算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她把剩下的衣服放在床上,手攥成了拳头,似乎非常气愤。她张开嘴,但又像僵住了一样,好像如果她真要说出来,她会被她所说的话吓坏似的。
她把目光从布鲁诺身上移开,过了一会儿,悲伤地摇了摇头,转过脸来面对他。“您的父亲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她说,“您应该相信这一点。”
“但恐怕我无法相信这一点,”布鲁诺说,“我想他可能犯了一个大错特错的错误。”
“一个需要我们一起承担的错误。”
“我犯错的时候会受到惩罚,”布鲁诺坚持说,他感到愤怒,因为他发现用来对付小孩子的规矩对大人似乎通通都不适用(虽然事实上,大人才是推行这些规则的人)。“愚蠢的父亲。”他摒着呼吸加了一句。
玛丽娅睁大了眼睛,向他迈了一步,因为害怕而用手在嘴上捂了好一会儿。她向四周看了一眼,确信没有人在听他们说话,没有人听到布鲁诺刚才说的话。“您不能说这样的话,”她说,“您再也不能这样说您的父亲。”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布鲁诺说。他为自己刚才的言辞感到羞愧,但是他只是坐了回去,因为没有人在乎他的想法,他是个局外人。
“因为您的父亲是一位好人,”玛丽娅说,“一位非常好的好人。他照顾着我们所有的人。”
“把我们全家人带到这样一个地方了,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地方,你的意思是这就是照顾我们吗?”
“您父亲做了很多事情,”她说,“很多值得您骄傲的事情。如果不是您父亲,我现在又能在哪儿呢?”
“在柏林,我想,”布鲁诺说,“在一个漂亮房子里工作。在常春藤下吃午饭,和蜜蜂一起。”
“您不记得我刚来为您工作的时候了吧?”她平静地问,然后在布鲁诺的床边坐了下来,以前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不过您怎么能记得呢?那时候您才三岁。您父亲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收留我,帮助我。他给了我工作、家和食物。您无法想象渴望食物的感觉。您从来没有挨过饿,是吧?”
布鲁诺皱着眉头想了想。他想说他现在就觉得有点饿,但是,他没有说,而是朝玛丽娅看过去,他突然意识到,他从来没有完全把玛丽娅看作是一个有自己的生命和经历的人。毕竟,(就布鲁诺所看到的)她从来没有扮演过他家女仆以外的角色。除了女仆制服以外,他甚至没有见过玛丽娅穿别的衣服。但是,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承认,在玛丽娅的生命中,除了为他和他的家人服务,还应该有些别的东西。她脑子里一定也有想法,就像自己一样。她一定也在思念着什么,一定也想见见从前的朋友。来这里以后她一定也是每天哭泣着入睡,就像那些比自己小、也不如自己勇敢的小男孩一样。布鲁诺注意到她还很漂亮,这样想着,布鲁诺心里觉得很有趣。
“当您的父亲在您这么大的时候,我的母亲认识了您的父亲,”过了一会儿玛丽娅说,“她为您的祖母工作。您祖母年轻的时候在德国进行巡演,我母亲负责她的演出服。她负责打理您祖母所有的演出服装--清洗、熨烫、缝补。那都是华丽的盛装!还有针线活儿,布鲁诺!那些衣服就像艺术品,每个设计都很精巧。现在你可找不到那么好的裁缝了。”她摇摇头,微笑着,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布鲁诺则耐心地听着。“她要保证在您祖母演出之前来到更衣室,当您祖母到来的时候,所有的服装都已经准备就绪。您祖母退休以后,非常友好地邀请我的母亲和她住在一起,并给了她一笔小小的抚恤金。但是,日子不景气,于是您的父亲又给了我一份工作,这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几个月后,我的母亲病重,需要大量的医院护理,又是您的父亲一手安排好了一切,虽然他根本没有这个义务,但是他却自己掏腰包支付了医药费,只是因为,我母亲是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把我收留在你们家。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又是您的父亲支付了所有的丧葬费。所以,您不能再说您父亲愚蠢了,布鲁诺。不要在我面前说,我不会允许的。”
布鲁诺咬着嘴唇。他原本是想在这场逃离“一起出去”的战役中拉拢玛丽娅的,但是现在,他看到了玛丽娅对父亲的忠诚。不过当他听完这个故事,不得不承认,他很为他的父亲感到骄傲。
“嗯,”他说,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说的话了,“我想他挺好的。”
“是的,”玛丽娅说,站起来走到窗前,从那里可以远远看见那些小屋和里面的人们。“他对我很好,”她一边继续说,一边思考着,看着远处那些人和走动的士兵。“他的灵魂很仁慈,的确是这样的,这让我想……”当她看着那些人的时候,她的腔调突然变了,听起来好像要哭了。
“想什么?”布鲁诺说。
“想他怎么可以……”
“他可以怎么?”布鲁诺追问。
楼下传来一声重重的摔门声,余音在整个屋子里回荡--就像枪声--布鲁诺吓了一跳,玛丽娅也吓得轻声尖叫。布鲁诺听到砰砰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快,他爬上床,紧紧贴着墙,突然很害怕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他摒住呼吸,等待着麻烦的到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只是格蕾特尔,那个“无可救药”的人。她把头伸进来,看到她的弟弟正和女仆谈话,似乎感到很吃惊。
“怎么了?”格蕾特尔问。
“没什么,”布鲁诺有所防备地说,“你想干什么,出去。”
“你出去,”她回应,虽然这是布鲁诺的房间。然后她转过脸来看着玛丽娅,眯着眼睛透出怀疑的目光。“给我洗个澡,好吧?”她问。
“你为什么不自己洗澡?”布鲁诺生气地说。
“因为她是仆人,”格蕾特尔说,“她在这里就是干这活的。”
“这不是她要干的活。”布鲁诺大声喊着,站起来冲到姐姐面前,“她在这里不是为了每时每刻都替我们干活的,你知道的。特别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我们得自己做。”
格蕾特尔瞪着弟弟,好像他疯了似的,然后看着玛丽娅,玛丽娅连连摇头。
“当然可以,格蕾特尔小姐,”玛丽娅说,“等我整理好您弟弟的衣物,我马上过来找您。”
“行,别太久了,”格蕾特尔粗鲁地说--她不像布鲁诺,她从不认为玛丽娅跟她一样会有感情--然后她大步走回了房间,把门甩上了。玛丽娅的眼神没有跟着格蕾特尔,但是脸上泛出一抹红晕。
“我还是认为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几分钟后,布鲁诺平静地说,好像为他姐姐的行为道歉,但又不知道这么做是否正确。像这样的场景总是让布鲁诺很不舒服,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对别人无礼,即使是为你工作的人。但是这样的情形就是时有发生。
“即使您是对的,您也不能大声说出来,”玛丽娅迅速地回答,走到布鲁诺跟前,好像要向他灌输某种东西。“答应我您不会的。”
“但是为什么?”他皱着眉头问,“我只是说出了我的真实感受。我可以这么做的,是吗?”
“不可以,”她说,“您不可以这么做。”
“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感受?”他重复道,似乎不相信这个说法。
“不可以,”她坚持说,好像有点被激怒了。“请保持沉默,布鲁诺。您知道您会惹多大的麻烦吗?给我们所有的人?”
布鲁诺瞪着她。她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一种狂乱的焦虑,这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他妥协了。“好的,”他轻声说,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他突然很想离开她,“我只是说我不喜欢这里,就是这样。我只是在你整理衣服的时候随便说说。这并不意味着我要逃跑或者别的什么。虽然我说了,但我想别人是不会因此而批评我的。”
“您想让您的父母担心死吗?”玛丽娅问,“布鲁诺,如果你懂一点事的话,您会保持沉默,把心思都放在学校的功课上,放在您父亲让您做的事情上。我们必须在一切结束以前保证我们大家的安全。这就是我要做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改变不了现状。”
突然,布鲁诺没有了任何理由,很想嚎啕大哭一场。这个想法让他自己都有些吃惊,于是他拼命地眨眼,不想让玛丽娅知道他的感受。虽然当他再次遇到她的目光时,感觉到空气里有种怪怪的东西,因为她的眼睛里似乎也含着泪水。总而言之,他觉得很难堪,于是背对着玛丽娅,朝门口走去。
“您要去哪里?”玛丽娅问。
“外面,”布鲁诺生气地说,“这你管不着吧?”
他本来走得很慢,但是一出门就很快地走向楼梯,然后快速冲了下去,他突然觉得如果他不赶紧冲出去,他就会晕倒在这个房子里。几秒钟时间,他就到了屋外,在马路上来回狂奔,他要做一点积极的事情,能够让他精疲力尽的事情。他远远地看见那扇大门,门外就是通向火车站的马路,到了火车站就能坐火车回到柏林的家。但是,一想到逃回家后只能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着,他就觉得还不如留下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