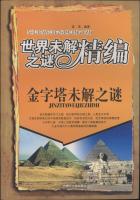白乐天、元稹两个人共同攻习制科考试,中第以后,白居易寄一首诗给元稹说:“皆当少壮日,同惜盛明时。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攻文朝,讲学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锋锐若锥。”注释说:“当时白居易和元稹共同收集策试范本,总共收集了上百篇,每人都有纤锋细管的毛笔,带在身上去参加考试,参考后两个人相对而笑,称之为‘毫锥’。”由此可知举子们对付考试,把范本编排在一起记诵,从唐朝时就已经有了。“毫锥”笔的名称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门生门下见门生
【原文】
后唐裴尚书年老致政。清泰初,其门生马裔孙知举,放榜后引新进士谒谢于裴,裴欢宴永日,书一绝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时人荣之。事见苏耆《开谭录》。予以《五代登科记》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举,四年放进士八人,裔孙预焉。后十年,裔孙为翰林学士,以清泰三年放进士十三人,兹所书是已。裔孙寻拜相,新史亦载此一句云。白乐天诗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篇。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予考《登科记》乐天以贞元十六年庚辰中书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郢以宝应二年癸卯礼部侍郎萧昕下第九人登科,迨郢拜太常时,几四十年矣。昕自癸卯放进士之后,二十四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再知贡举,可谓寿俊。观白公所赋,益可见唐世举子之尊尚主司也。
【译文】
五代后唐裴皞
尚书年事高迈,致仕居家。后唐末帝清泰初年,他的门生马裔孙知贡举(负责主持科举考试),放榜以后,带领新科进士到裴皞府上谢恩,裴皞非常高兴,和他们欢快地宴饮了整整一天。在这一天,他写了一首绝句说:“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当时士大夫都以此事,赞誉裴皞。这件事见苏耆写的《开谭录》一书。我取《五代登科记》考试此事裴皞在后唐庄帝同光年中曾三次知贡举,同光四年录取的进士共八名,马裔孙就在其中。十年后,马裔孙任翰林学士,清泰三年放榜时,共取进士十三人,《开谭录》所说的不错。不久,马裔孙当了丞相,《新五代史》也记载了这一句。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一首。诗在注释说:“今科座主高郢侍郎是萧昕尚书门下及第。”我取《唐登科记》考查,白居易在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在中书舍人高郢门下以第四名中进士,而高郢则是在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萧昕门下以第九名中进士,到高郢被升为太常卿时,差不多四十年了。萧昕自从宝应二年癸卯知贡举以后,二十四年后的贞元三年丁卯,又以礼部尚书之职再次知贡举,真可说是长寿之俊了。看到白居易诗中所写,更可以看出唐朝的举子们是多么尊重主考的座主了。
韩苏杜公叙马
【原文】
韩公《人物画记》,其叙马处云:“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焉,行者,牵者,奔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而相戏者,怒相踶啮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焉。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谓其叙事该而不烦,故仿之而作《罗汉记》。坡公赋《韩干十四马》诗云:“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之与记,其体虽异,其为布置铺写则同。诵坡公之语,盖不待见画也。予《云林绘监》中有临本,略无小异。杜老《观曹将军画马图》云:“昔日太宗拳毛马呙,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廝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其语视东坡,似若不及,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不妨独步也。杜又有《画马赞》云:“韩干画马,毫端有神。骅骝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雹,一日天池。瞻彼骏骨,实惟龙媒”之句。坡公《九马赞》言:“薛绍彭家藏曹将军《九马图》,杜子美所为作诗者也。”其词云:“牧者万岁,绘者惟霸。甫为作诵,伟哉九马。”读此诗文数篇,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气橫出,可谓“妙绝动宫商”矣。
【译文】
韩愈《人物画记》中描述马的那一段说:“马肥大的共有九匹。在马群中又有上等好马和普通的马。有正在行走的,有想摆脱牵缚的,有狂奔的,有过水的,有跳跃的,有翘着头的,有回头看的,有引颈长鸣的,有卧息不动的,有嘶叫的,有站立的,有踢咬的,有饮水的,有解溲的,有上坡的,有下坡的,有身痒树上磨蹭的,有喷鼻的,有闻味的,有高兴相互嬉戏的,有发怒而互相踢咬的,有正在吃草的,有被人骑着的,有快速跑动的,有慢慢走动的,有驮着服饰器物的,有驮着野兔狐狸的,马的活动形态共二十七类。这幅画一共画了八十三匹马,却没有一点雷同。”秦少游称道此文叙述马事完备而不烦琐,因此模仿它的格套写了一篇《罗汉记》。苏轼作《韩干十四马》诗写道:“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鬃尾齐。一马任前双举后,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诗和记的体裁虽然大不相同,但它们的铺陈描绘则是相同的。读完苏轼的试,几乎不用再看图画了。我的《云林绘监》里有这幅画的写本,与原画毫厘不差。杜甫的《观曹将军画马图》说:“昔日太宗拳毛马呙,近时郭家师子花。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霜蹄蹴踏长楸间,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顾视清高气深稳。”这些诗句和苏轼的诗相比,似乎稍逊一筹,至于“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一句,可以说再没有能够超越的语句。杜甫还有一篇《画马赞》说:“韩干画马,笔端像有神助。骅骝(骏骆)老大,(骏马名)清新”以及“四蹄如雷电,一日到天池。看它骏骨相,无疑是龙媒”的句子。苏轼的《九马赞》说:“薛绍彭家收藏有曹将军《九马图》,就是杜甫为之作诗的那幅画。”赞词说:“有马的是天子,画马的是曹霸,杜甫为它作诗赞诵,了不起啊,九匹骏马!”读了这几篇诗文,真能令人心意超然,意气风发,可以说“妙绝动宫墙”了!
风灾霜旱
【原文】
庆元四年,饶州盛夏中,时雨频降,六七月之间未尝请祷,农家水车龙具,倚之于壁,父老以为所未见,指期西成有秋,当倍常岁,而低下之田,遂以潦告。余干、安仁乃于八月罹地火之厄。地火者,盖苗根及心,孽虫生之,茎干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谓蟊贼也。九月十四日,严霜连降,晚稻未实者,皆为所薄,不能复生,诸县多然。有常产者,诉于郡县,郡守孜孜爱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无此两项。”又云:“九月正是霜降节,不足为异。”案白乐天讽谏《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此明证也。予因记元祐五年苏公守杭日,与宰相吕汲公书,论浙西灾伤曰:“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争言无灾,或有灾而不甚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闭拒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苏公及此,可谓仁人之言。岂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谓风灾、所谓早霜之类,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稽考,惧贪民乘时,或成冒滥,故不轻启其端。今日之计,固难添创条式。但凡有灾伤,出于水旱之外者,专委良守令推而行之,则实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祸,仁政之上也。
【译文】
宋宁宗庆元四年,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在盛夏时节连连降雨,六月、七月两个月里一次也没有祈雨,农夫家的水车龙具都斜靠在家中的墙壁上,老年人都说这种天气前所未见,于是盼望着今年秋天的收成比往年要好上一倍。然而不久,那些耕种低洼田地的农夫们便说已经遭涝了。余干、安仁两县在八月里又遭受了地火之灾。什么叫地火呢?那就是庄稼从苗根到苗心都生了孽虫,致使禾茎变枯变焦,远远望去,像是金黄的烈火一样,这正是古时候所说的“蟊贼”之害。
九月十四日,又接连下了寒霜,晚稻还没有灌浆成粒的都被这场大霜冻死,饶州所属各县大都如此。一些有田产的农夫到郡县衙门去报告灾情,知州是一位体察民情的官,闻知此情,便有了减免租赋的打算,可是属官们却纷纷说:“皇朝法典规定的减免租赋,可没有说到‘蟊贼’和‘早霜’两种情况啊!”还说:“九月里就该有霜降节,下霜也不足为奇。”按:白居易有一首《杜陵叟》诗说:“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这是九月不应该下霜的明证。
我因而又记起哲宗元祐五年苏轼作杭州知府时,给宰相吕大防写过一封信,专论浙西的灾伤情形,信中说:“贤哲之臣听到灾伤之情,绝不会放任不管,只是怕世俗庸人欺君昧上已成恶习,报喜不报忧,争着说本处并没有灾荒,或者说虽有灾情,不很严重。八月下旬,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几千民众到州衙报知本州发生了风灾,州官认定法典上只有报知水灾旱灾的而没有报知风灾的,因此闭门不听百性的诉说,州衙外百姓非常气愤,混乱中踩死了十一位老人和孩子。由此事可知:地方官吏只喜欢说丰收、不喜欢说灾害的,十人之中就有九人,这种情形不能不明察。”苏轼说到这一步,真可以说是仁人之言了。这是不是古人在创立法律的时候,考虑到像风灾、像早霜一样的灾情不像时旱、时涝那样一看便知,而怕一些刁民借此为由,冒领赈济,滥减租赋,所以不便轻易地将它们纳入法律条文呢?如今看来,把这类灾情重新纳入法典怕是太难,但是只要出现了灾情,那些不包括在水灾、旱灾之内的灾情,朝廷应该专门委派贤良的地方长官实行救助,这样便可以使百姓切实感受到天子的恩德,避免造成大量灾民流离失所,这是施行仁政的上好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