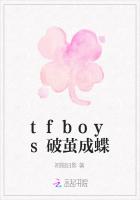日韩杂俳
浅草寺
浅草寺前景曈曈
未见浅草见灯笼
不经意
鉴真弟子擦肩去
日本字
乍到日本未觉奇
地名人名似依稀
平假名
片假名
偏旁部首有颜筋
青瓦台
青瓦台上发幽光
一半艳阳一半霜
二金平壤喜相拥
依依别
情长路更长
景福宫
景福宫前蝉声歇
大王临窗望汉天
破窗去
遍地韩文框与圈
注:此杂俳写于2000年。
去杜甫草堂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浣花溪畔的一群孩童
抱了几根茅草
嬉戏中消失于唐朝
等他们回来
足足等了1200多年
这帮让诗圣怄气的孩子
已经长大成虎背熊腰的地产商人
杜甫还住在为秋风所破的茅屋
他的神韵固定在一座青铜雕像
2006年9月17日我和老七
接待北京来的琳达和傅敏
当我们说起
草堂茶园嘎吱嘎吱的竹椅
越过头顶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盖碗茶
还有编了号的参天楠木
不用编号的茂林修竹
加上她们的嘴馋死成都小吃
她们的脸爱死成都生锈的天空
她们吵着一定要去草堂喝茶
虽然残酷的秋风
将她们完整背诵的杜诗
吹得七零八落
虽然我们四人只有二人会
三个人玩的“斗地主”
她们吵着一定要去草堂喝茶
去就去呗
从青羊宫过陈麻婆豆腐店
不到苏坡桥就到了
事情恰恰不是这样简单
走到清江东路
我们就迷失在地产商开发的一个个楼盘
问了无数个保安
像是故意走错路一样
我们的车始终围着草堂兜圈
一丛丛钢筋混凝土的花朵
围着一间茅屋盛大开盘
一辆辆五颜六色的汽车
绕着老杜的诗歌旋转
来到草堂大门我们一起决定
将所见楼盘告诉诗圣
说我们见到了
他在公元761年秋天
在那个凄风苦雨的秋夜
祈望的“广厦”与“欢颜”
浣花苑
浣花新城
春天花园
紫藤花园
天邑花园
龙景花园
清江雅居
流水山庄
康河郦景
水木光华
天合·凯旋城
杜甫花园
没有桃花的春天是一句谎言
《诗经》里的灼灼其华
一直灿烂到龙泉
片片桃花在枝头
点燃古人的忧伤
没有桃花的春天
等于一句谎言
没有芳香的春天
是一场诈骗
从成都赶来赏花的人
有福了
他们被桃花照亮
生活在春天里
南非行(组诗)
开普敦
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就有了光
在开普敦
我说要有彩虹
于是就有了彩虹
罗本岛
如你所说
你将长矛与仇恨
抛进了大海
从开普敦看卓湾中的罗本岛
看曾经囚禁你27年的地方
阳光镶嵌的轮廓
一闪一闪的
像极了一条项链
曼德拉铜像前
“嘭嘭
嘭嘭”
这是南非的鼓点
还有带羽毛的歌声
祖鲁族少女的赤脚
踩在激昂的节奏上
我想象这是一条小木船
你被供在船头
“嘭嘭
嘭嘭”
整齐的舞步
左一脚右一脚
右一脚左一脚
非洲大陆摇晃起来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
事有不巧
去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当天
一头大象
因偷猎而负伤的大象
在一条小溪旁死了
它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来死
导游说
我们的眼睛
已经集齐了非洲五兽
(狮子
豹子
水牛
犀牛
大象)
也不缺这一只
但是这一次我想
是大象不想再看到人类
约堡
上锁的铁栏
荷枪实弹的保镖
阿明带我去看
一家钻石加工厂
设计切割打磨
璀璨梦幻
我对疯狂的世界
常常感到无语
人们对哺育他们的
阳光大地熟视无睹
对虚荣的事物
却如痴如醉
好望角
一边听导游解说
一边我心里将暖流与寒流
置换成女人与男人
好望角
是美好希望之角
又是风暴角
印度洋的暖流
大西洋的寒流
在此交汇
海面像煮开了锅一样
用暴风骤雨这些词都软了
咆哮狰狞凶悍横不讲理
大海在这里发脾气
吞没过往的船只
是件小事情
我一边听
一边绝望
还好好望角上空
及时出现了彩虹
我想它应该是
人类相信的爱情
诗歌之核
——北京机场遇娜夜
人群里
有人偷偷爱你的诗歌
与年龄无关与性别无关
潮与不潮好看或者丑
喧哗抑或矜持
雾霾退去后的阳光
缓缓滑向跑道的飞机
这些多么像事物的壳
那个核人们都知道的
人群里
有人偷偷爱你的诗歌
泸沽湖(三首)
献诗
天空将白云开放成花朵
大地将群峰开放成花朵
阳光将树叶开放成花朵
泸沽湖将摩梭女儿开放成花朵
秋天来到泸沽湖
我死死搂着心中的比喻
这可是诗人开放出的花朵
夜马
这不是诗歌里的意象
泸沽湖畔一匹马
从黑夜里向我走来
惊艳无语
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我按捺住问当地人
“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个傻问题
我只记得泸沽湖畔
静谧的夜晚一匹马
和我擦肩而过
车过盐源
历史上喧嚣的铁
和津津有味的盐
不见了只剩下
蓝天白云骄阳
车过盐源我给一个
在北京的盐源女孩拨电话
“去泸沽湖呀盐源印象如何”
“天空富有大地贫瘠”
“哪里哟盐源很多好吃的东西
下次一定到家里做客”
巴西掠影(组诗)
圣保罗美女
“为什么旅行”
“去看世界上的美女”
在圣保罗
我看见一个大眼睛美女
她眼球的转动
不只是白昼与黑夜的转动
不只是500年来白与黑的
转动
我像孤注一掷的赌徒
双眼盯着转动的轮盘
将停未停的瞬间
我几乎窒息
而她转动眼球时
眨都没眨一眼
里约
在耶稣山留影
我发现照片一片空白
朋友说白雾太厚太快
由此我原谅了上帝
不怪他看不见眼皮下
肮脏的贫民窟
不怪他只看见
美丽的科帕卡巴纳海滩
伊瓜苏大瀑布
一幅环形窗帘
牵得太夸张了
从阿根廷牵到巴西
从巴西牵到阿根廷
来到伊瓜苏
我还未掀开窗帘
一万只老虎扑出来
注:“伊瓜苏”印第安语意为大水。
玛瑙斯
1.蝴蝶效应
要么坐船要么飞
水上的玛瑙斯
鱼腥味的玛瑙斯
365天穿拖鞋的玛瑙斯
女人多过男人的玛瑙斯
跳板一样的玛瑙斯
经过你去亚马孙丛林
不为印第安人不为帝王莲
不为食人鱼不为蛇虫蚂蚁
我想目睹一只蝴蝶
一只扇动翅膀的蝴蝶
最好是洛伦兹举例的那只
如果凑巧得克萨斯
两周后遭遇龙卷风
我会莞尔一笑
像是掌握了世界的秘密
2.流泪的树
谁在亚马孙的丛林里
哭那是橡胶树
谁在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后
哭那是印第安人
谁在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上
哭那是非洲黑奴
谁在陪他们一起使劲地
哭呀那是玛瑙斯
自从1873年一个英国人
在马来西亚
成功移植橡胶树
注:“蝴蝶效应”由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提出。
印第安语称橡胶树为流泪的树。
橡胶树原产地在亚马孙丛林。
尼亚加拉大瀑布
河床太滑一块翡翠
沿着尼亚加拉河道
跌落悬崖摔碎为
浪花激流漩涡
雨雾和彩虹
水里滚出的巨雷
停在空中
以及木桶漂流
探险者的传说
我惊诧的是
沿着尼亚加拉河道
在注入安大略湖之前
汹涌澎湃的水
撕裂后的融合
一块翡翠
好像途中不曾摔碎
台湾纪事
今年打算去福建寻根
《李氏族谱》说
始祖所在汀州武平
没想年初随阿来去台湾
像是一次暖身
台北过元宵
介绍主人时有两个名字
让我暗暗吃惊
一个是我走了43年的爷爷
一个是我走了19年的父亲
记不住谁说过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酒过三巡陈春发
用拇指掐着无名指对我说
“台北叫春发的大哥多得很
我是其中最小的那一个”
我两次向他敬酒
他不知道他与我爷爷同名
台中足浴
上演的是另一种剧情
邻座的李晓平
亮出他的瞎眼趾甲说
“谁是古槐底下人
双足小趾验甲型”
父亲说过小脚趾瞎眼的
自家人搞不懂啦
我千里迢迢从成都到台中
是来对趾型
东文兄高雄为我们饯行
88岁的余光中
请大家不敬酒
省去不断起身
我知道他是福建永春人
他站立讲话的形神
成了乡愁的化身
风中的乡愁
老去的乡愁
我明明到的是台湾
感觉是到了武平
海胆
在一座海滨城市
服务员热情介绍菜品
刺身龙虾清蒸东星斑
三文鱼北极贝象拔蚌
凉拌海蜇清炒虾球
蛋羹海星生吃海胆
邻座说海胆壮阳要吃
我从未吃过心里有障碍
坚硬球形刺猬状
海胆的长相不想给人吃
加之我把蛋羹海星
听成了蛋羹海心
感觉异样
像是在吃大海的五脏六腑
当时我的心里长出
另外的句子
“大海将陆地上的河流
面条一样吮吸了
人类在精致地吃大海的内脏”
“与大海相比
人类的吃法有些小气
有些忘恩负义”
在虎牙大峡谷看见鸽子树
1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莱布尼茨说
“虎牙大峡谷没有多余的一片树叶”
我说
植物的竞争不亚于动物
阳光水分土壤空间角度
加上风媒雨媒蜂媒鸟媒
植物之美背后有生死之争
你是植物学者还是诗人
好吧让我端出冗长的比喻
从峡谷口到雪宝顶的每一棵树
都是诗人
树叶是它们
发布在季节里的诗篇
斑斓的色彩
隐秘的意象
仿佛只为献给造物主
2
“我想和鸽子树合影”
它的花白到荒诞
说是开了一千万年
一种比爱更持久的时间
“照下来就不美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平武诗人何波说
白马藏族达娃的话
更让人伤感
“你只带得走照片
带不走鸽子树的美”
四姑娘山(二首)
天上的石头
和太阳月亮星辰
一样镶嵌在天空
蓝天白云是你的家园
你照耀万物
藏语说斯古拉
汉语说四姑娘
英语中的stone
汉语中的石头
斯古拉
你是供在天上的石头
待嫁的新娘
心情不悦
你浓雾当布
遮住自己
心情向好
你掬一捧阳光
抹在脸上
那是金灿灿的笑容
想要出嫁
你抓一把白雪
涂在身上
那是身披婚纱的新娘
扭动一下腰肢
摆动裙摆的图案
熊猫雪豹羚牛金丝猴
还有沙棘树和雪松
你扭得太快了
裙裾上的花朵撒落一地
杜鹃百合雪莲绿绒蒿
还有蒲公英和报春花
四姑娘
圣洁的新娘
待嫁的新娘
九寨神仙池(二首)
九寨神仙池
我曾读过
一本关于地球起源的书
科学家吵了半天
也不知道
地球上的水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科学家们
充满敬意
他们讨论的事
总比哲学家讨论
“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
要好
虽然人类
不知道地球上的水
来自哪里
关于水
我想告诉你
我仅知道
地球上最柔美的水
在九寨神仙池
五月的红桦树
你是
树林里的行为艺术家
故意和破洞牛仔裤撞衫
不修边幅
不好好穿衣服
巾巾片片挂在身上
像是绯闻
你是油画家
其他树木深深浅浅
画着绿色
神仙池用水
画米黄的涟漪
松鼠画轻盈的跳跃
林间的雨滴和风
画安静的栈道
蓝天白云
画深邃的背景
甚至有人躺在地上
用相机画憨态的杓兰花开
而你
只画褚红
你是一个使苦肉计的恋人
让身上的皮肉
在风雨中炸裂
传说用红桦树皮写情书
一写一个准
甩石头打天的人
小时候从教科书
知道的印第安人
今天在雨季
在亚马孙丛林
在一条木船上
算是见到了
此时你跟我说
她的祖先跨过白令海峡
迁徙而来
我是信的
你说她的祖先
乘独木舟漂洋过海而来
我是信的
甚至你说他们
是候鸟叼了炎黄子孙的骨头
丢在美洲大陆上长出来的
我信
黄皮肤黑眼睛四十多岁
一个卖手工艺品的妇人
她的眼里
有石头一样的安静
有亿万年的光阴
曾经作为公务员
我去大娄山高山访贫问苦
要打开米柜看
要揭开锅盖看
在一家农户的灶房
也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
她看我用的就是今天
这种眼神
她的眼里
有石头一样的安静
有亿万年的光阴
谁人说的
我们是一堆呼啸而过的钢铁
他们是一群甩石头打天的人
神把一切看在眼里
只是神一直缄默无声
2018平昌见闻(组诗)
赞武大靖
大陆本来就是漂移的
不要太使劲
把对手滑在身后就行了
破纪录是好事
我担心
你再使劲
你会把江陵体育馆
蹬裂
再滑出一片陆地
平昌欢迎您
没有什么鞭炮
第二天一早
我看清楚了是
这座海边酒店的道旗
60厘米宽
1.8米长
绷得太紧了
海风一吹整夜
噼里啪啦地响
竖排的
平昌欢迎您
拼音字母
里面
像灌有炸药
柳时光
不用想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想起
“书贵硬瘦能通神”的柳公权
一个韩国司机
在餐巾纸上写下他的名字
我称赞他书法好时
这个魁梧的男人
羞涩起来
一直羞涩到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海浪
沿着江陵的沙滩走
这片海
地图上叫日本海
半岛的人叫朝鲜东海
中国古书上叫鲸海
沿着江陵的沙滩走
这个民族
崇尚白色把长白山当作圣山
这个民族
崇尚冰雪竞技
将全世界冰雪健儿邀至平昌郡
沿着江陵的沙滩走
大海
将她蓝色长裙的
白色里衬
反复
翻给我看
陶法托富阿
陶法托富阿
穿人字拖
穿红黑相间的裙子
赤裸上身
作为旗手
代表赤道附近
汤加王国
参加奥运
他一登场
全世界都笑了
在零下10摄氏度的平昌
我必须佩服
这个旗手
他随身携带着他的祖国
肯尼亚行(三首)
脏辫
毫不吝惜时间
毫不吝惜金钱
每个非洲女子
都醉心于她的发型
大小不一的辫子
编织不同的造型
紧爬在头皮
纠结在脑勺
披垂在耳畔
五彩缤纷
美轮美奂
我不在乎
她们头发的真假
不追溯
脏辫是否起源于
航海中的水手
以及摇滚歌手
在脏辫里
灌入了怎样的歌声与节奏
在非洲
除了金合欢的树冠
雨后的彩虹
我爱看
女人的脏辫
有两句话
必须替她们说出来
“梳妆打扮
莫如梳头好看”
“美是自由的象征”
马赛马拉草原
十月雨季到来之前
我看到的
马赛马拉大草原
是不动的
没有角马的狂奔
没有血腥的捕食
云不动
山不动
树不动
草不动
大象
水牛
狮子
长颈鹿
树枝上的秃鹫
也不动
飞禽走兽不过是些
摆放在草原上的雕塑
十月雨季到来之前
我看到的
马赛马拉大草原
是不动的
它像挂在墙壁上的
一幅油画
小鸟
离开马赛马拉的早晨
一个年轻的马赛人
右手握住一只小鸟
举在胸前递给我
黑亮的肌肤
羞怯的眼神
我注意到小鸟
绒毛中张开的脚趾
很久没有看到
这种粉嫩的趾爪了
我随口问
“How much money?”
他摇摇头
口中吐出
“fly”一词
短暂的僵持
他放飞了手中的小鸟
小鸟飞向
洒满阳光的树林
马赛人也消失在树林
我恍惚了一下
好想抽自己两个耳光
丑陋的“How much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