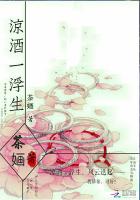任伯中被眼前景象吓疯了,死死攥着司庭,“我不想死啊,我再也不说自己无聊了,我从此以后就想过太平富贵日子,拜什么师学什么艺啊,我要被这种东西吃了,估计在世人眼中我就是个失踪,谁能想到我被妖怪吃了。说出去,都以为是无稽之谈。”
“你哪那么多废话,还有力气抓我。”
司庭翻身踩着怪物肩膀,抓了把木炭灰戳进他眼睛里戳,那东西发出凄叫,手挥到任伯中身上,直接打到吐血,那血喷到司庭眼睛里,像是一下烧了起来,他捂着眼睛在地上打滚,疼的要命。
任伯中趴在地上,五脏六腑都移了位,却抬头惊诧,那怪物和司庭竟然动作如出一辙,都是捂着眼睛痛的扭曲大叫,一瞬间在微弱的火把下,仿佛重叠在一起,最后模糊成一片。
一阵冷风吹过,昏迷之前看到师父那张难得不是宿醉慵懒的脸,瞪着眼手里拿着长剑上面穿着个黄符,风一样的飘来,而远远的看着崔阑有些懵逼的在远处打着灯笼,晕过去之前,任伯中就一个想法,这究竟是梦,还是现实?
中间司庭醒了两次,一次全身疼醒的,动不了,手脚都被绑在木板床上,头上贴了符咒,第二次是身体不疼了,但轻飘飘的,抬头看任伯中在一边以泪洗面,他当时真想骂娘,老子还没死呢,你一个大男人哭什么。
同时叹息,阿妈说过,这辈子遇到一个为自己哭的人不容易,何况这都是他第二次为自己哭了。当下做了个决定,以后好好陪任伯中炼剑,再也不诓他占小便宜了。
想想自己就是心软,以前救过小红一次,小红当时哭了,他就觉得这姑娘真不错,现在看伯中哭的智障一样,心更软了,以后不能总编故事骗他了,人总挨骗,假的也成真的了,慢慢的会觉得江湖是好地方,司庭虽没经历过大起大浪的江湖,可他在狼群待过,知道这世上有一便有二,哪是任伯中书里看到的那样。
以后一定要和伯中说清楚了,以免这实心孩子上当。
身体轻飘飘的感觉,他又有些熟悉,仿佛很小的时候自己就有过这种轻飘飘的时候,想说话说不了,动也动不了,就和死了一样。
等再醒来的时候,这一次,实实在在的胳膊腿都能动了,却浑身酸涩,任伯中趴在床边睡着了,低头看到这厮大概是没洗头,一股子麻油味。
司庭起来正好看到铜镜中的自己,脸色苍白仿佛受了多大罪似的。
面前是熟睡的任伯中和崔阑,他晃晃脑袋,走出房门,山间清凉。师父难得这个时候没有醉酒,在悬崖边炼剑,花月零空,横扫千秋,回眸间一脸正气,让人看得呆了。
收了剑锋,盯着司庭,“你生来自带一股怨气。专门招揽祸事,好在年幼便被修仙之人封印,到如今已经消减大半。”
司庭回头看看确定在和自己说话,可却没怎么听懂。
师父也不在意,“听说你有个阿妈?”
司庭点头,他挣了不少钱都送去给阿妈,可自从进来任府,阿妈就说她年岁大了,有自己的人生要走。
也许别人觉得不舍,可司庭在狼群中长大的,小狼都会在长大后被母狼赶出家门,自立门户,这是稀松平常的事。
师父叹气摸着他的头,“苦命的孩子。”
满眼怜悯。
“阿妈说人要好好活着,坦坦荡荡,就不觉得辛苦。”
“话虽如此,可谁能保证自己一生坦坦荡荡。为师教不了你什么,不过一些花拳绣腿,将来你若觉得苦,便想想你阿妈说的话吧。”
司庭似懂非懂,“师父我们那天遇到的是什么?”
“你那天当真看到了东西。”
“伯中也看见了。”
“按理来说,伯中看不见的,可你的血和他的血不小心融了。”
“什么意思?”
“你俩的血可以相融。”
“为什么?我们又不是亲兄弟?”司庭瞪着眼睛。
后者哈哈大笑,“这世间最蠢的事,就是不少人觉得血相融便是父子,血不融便不是,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家庭。你俩都受伤了,血滴在一起融在一处,这是你二人的缘分。那东西外人看不到,崔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他看不过是一阵风。这结界阻拦的是凡人,你们是和我一起才进的来,其他人是看不到这山的。”
“那修真岂不是很厉害?”
司庭露出向往之色。
“可人更愿意选择看不清这个世界,司庭。”
师父第一次叫他的名字,语气柔了下来。
“你阿妈给你的那种药丸还有吗?”
“都用完了。”
“那以后就不要轻易用你阿妈留给你的东西了,也不用总帮伯中找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以后的他,你是管不了的,你二人并蒂。”
说道这,看到司庭的眼睛,咽下了后半句话。
师父不知从哪里拿出一壶酒来,剑扔给他,司庭吓了一跳用手一握,就见师父脚下生风,气势逼人朝他一掌过来,司庭直往后退,手中剑竟然挥着过起招来。惊奇的发现,身体竟比之前轻盈许多,如有神助。
听到声音屋里人跑出来,任伯中惊讶的,“司庭你醒了。”
司庭捂着手里的剑,像是参透了什么把剑扔给任伯中,后者接过来却还是老样子。
正玩乐着,突然远处传来钟响,那种沉闷深远,在山头都听得清晰。
崔阑惊慌跑到崖边,太阳还未完全升起,那钟响一声接一声,“这,这。”
说完又不敢相信一样的听着,可就在这时,城里城外接连带着大大小小的钟响,循声而起,连续不断,仿佛瞬间京城都沉浸在钟声里,崔阑手抖着跪在地上,朝着京城方向磕下头去。
师父眼神缥缈如云,拍着肩膀抖动的崔阑,“该回去了。”
后者抬头满眼泪痕,“师父,你早知道?为什么还要把我带出来?你明知道,四皇子那边。”
“你父亲求我带你出来,京城乱了,崔太傅自己也没把握全胜,你是崔家唯一的血脉了。我得对的起他。”
师父叹息着没说下去,司庭皱眉问着,“这是?”
任伯中也是心中惊惧,“皇上,驾崩了。”
丧钟传出来,便是朝局尘埃落定,皇上可不是钟响了才驾崩的,历代都这样。
崔阑骑马一路狂奔,这种气氛干扰到任伯中也火急火燎的往任家跑,可跑到大门处,看到上面挂着国丧灵布,门口小厮一水的丧服,跑进院子直奔着父亲书房,还没到近前,就看阴着脸的任天意,“跑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父亲。”
他惊叫着。
“国丧期间还穿这身衣服,下人们一个个不经心,来人啊,给二公子换衣服。”
下人低垂着脸七手八脚的上来给他和司庭换衣服,任伯中张大着眼睛,“父亲?”
后者盯着自己的儿子看了半晌,叹了口气,“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崔太傅拍着自己儿子肩膀说道。
崔阑不可思议,父亲推推他,“进宫吧。”
他转身上马,宫门口的人没变,他一路顺畅,只下马扑到正殿之上,看到四皇子一身丧服坐在大殿中间咳嗽。
“你骗我?”
后者脸色苍白拉起嘴角。
“你还笑,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寒冰草,是你和师父联合起来骗我的。”
“你那么精明的人,好像什么都在掌控之中,我有时候就想看看你被骗的样子,咳咳咳。”
崔阑攥着拳头,“因为这世上我只信你一个人的话,你知不知道,你在拿你的命赌。”
“我现在不是好好活着。”
“可是为什么?”
崔阑知道这个结果是好的,却始料未及,所有人都知道,其实连四皇子自己也知道皇上驾崩,便是国舅爷和汝南王下手的最好时机,聚集在一起的矛盾一触即发,只要杀了四皇子,他们便名正言顺,所以他支走崔阑,想保崔阑一条命。
可为什么,可怎么会?
四皇子咳嗽着眼神看着虚无,“崔阑,对你这件事情上,我终究是输给他了。”
任伯中坐在父亲的书房里。
任天意叹息着,“兵戎相见,城外对峙。”所有人都猜中经过,可谁想得到结局?
最后雷声大雨点小结束这场战役的,是一个谁都想不到的人。
国舅爷的御林军,汝南王府无论明里的兵力还是背地里的高手,早就把皇城围的水泄不通,即便崔太傅,任天意乃至无数要抛头颅洒热血的重臣,也只能拼死一搏。
其实不用那么难,四皇子常年病重,只要杀了他,烈豪上位是理所当然。
可烈豪把冲到最前面的猎鹰杀了,杀了宠妃杀了国舅,守着四皇子,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他自己放弃皇位,杀了退而求其次的烈鹰,断了汝南王的后路,如果再打下去,便名不正言不顺,是反贼。
如果是这个名头,那么全天下都可杀之后快。
国丧的钟还没敲完,便已尘埃落定。
烈豪离开京城起身去北边的时候,天还没亮,他没告诉任何人,就自己牵了一匹马挂个简单的包袱上路。
自古英雄不问出处,他曾在京城翻天覆地,最后也不过是身后落下的一片秋叶。
直走出北城门,马道上萧索一片,一抬头竟早有人等在路上。
崔阑红着眼站在那,想骂他的话终究没说出来。烈豪身手拍拍他的背,往常一样呵斥,“娘们唧唧的。”
“你就这样走了?”
“不然呢?留下来讨人嫌,我父亲已多日不肯见我,全族上下恨不得扒了我的皮,可惜啊,我父亲就我一个儿子,杀了,他舍不得。”
烈豪竟还有心思调笑。
崔阑肩膀颤抖,说不出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