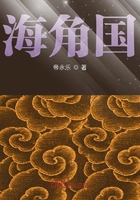痛疼蔓延着,我踉踉跄跄倒退几步,尽管我从不担心这种痛,毕竟遭遇外物入侵人体,不舒服的反应始终会有一个过程。而春仁这贱人,一脸阴戾,她得意地笑着,尖利的笑声像磨石,销蚀了我对其仅存的一点饶恕之心。。
一之谓甚,岂可在乎?果然留不得她的性命,此人怕生了反心呢。永生的岁月,最大好处是历史的教训丰富,从我最开始获得永生就见识过什么叫人性的诡谲。
就是那双不甘的眼睛盯着天空,鼻翼一动也不动,两颊肌肉紧张,表情狰狞——这样躺在地上的人配合深幽的夜空和周围各种努力压抑的呻吟声,交织出一副教人难以忘怀的画面,在当时刚获得永生的我看来,印象深刻。耳边听到几句汉地关中的方音,伴着呜咽的调子。哦,原来有个穿着鱼鳞甲衣的家伙亲手替地上的人合上双眼。人,死就必须瞑目啊!
在一刹那间,我有种奇特的抽离感,仿佛我从来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分子。可是曾经十几个时辰的行军、共同战斗,又怎么能磨灭!难以想象十几个时辰前,地上的那具尸体还活生生地被人尊为“明公”、“傅君”——他作为天子敕封的护羌校尉,傅育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如果我详细道明他如何上奏朝廷,凭一己之力,说服天子同意拨出陇西、张掖、酒泉三地的兵马,供他驱使,这就足够证明他身上的自信来源。
然而这一切的转折点要倒推回大半个月前,我们的军队在临羌附近驻扎,准备和其他三队人马汇合,每个人的心里盘算着怎么样缴获羌人养殖的肥美牛羊、娇娃美女。而我挂着傅君为我发明的人皮面具,在帐下装模作样地站岗,心里对同伙的想法不以为然,牛羊是有的,美女嘛,大家大可放心,羌人中的绝色佳丽哪个不是早被豪酋大人们掠去,剩下的普通货色,还不如洛阳里寻常闺秀的三分之一。怔忡之间,傅君的帷幕下出现了一个人,由于他戴着厚厚的斗篷,我没法看清楚他的样貌,但凭直觉,这人肯定是我认识的人。于是竖起耳朵听账内的动静:
——“傅君过虑,羌人的牛羊,正是母兽怀胎期间,必不肯大肆反攻。何况我探听到为首的归义……啊,不,应该是羌贼迷吾,背疮好像难以愈合,而且身在我们前方吊着的那支羌军中,此时不进攻,更待何时?”
尽管他背对着帷幕帐门,然而嗓音毕竟改不了。我哼了一声,原来是阿菀的异母兄长,那厮蛰伏汉地和羌人营寨交界的村落已久,做着各种见不得光的人奴交易。前不久,傅君收留了毁容的我,同时却发现,他也在傅君手下办事。他不过靠口甜舌滑博得军里上上下下的欢心罢了,能有什么好事儿!
面对着帐门的傅君,摸摸唇边的胡须:“甘公固然有理!那于其上三郡的府君看来,仆直抵羌人中心,他们啥功都没有,那岂不等于抢功劳。这叫以后其他兄弟如何肯听命?”姓甘的摇摇头:“此言差矣,旁人还以为傅君做乡愿呢!羌人这次集合的寨子又不止迷吾一处,南边、西边不也有大把的人头可以攫取?傅君大可追击羌人主力,然后再把剩下两翼的人头送给其余三郡首长。我军迅速行动,而且其余的友军又不知情;消息又是你第一个知道的,你立功了,谁敢说话?至于朝廷那儿,你一有首功、二得人缘,马上封侯的荣耀那是指日可待的!”接着两人哈哈大笑,姓甘的还举杯祝寿,口呼“愿君得进万石”的谀辞。
我虽然感到姓甘的,肉麻过甚,但又觉得甚是有利,岂止对傅君日后平步青云有利,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本万利。等到羌寨彻底攻陷那刻,或许另外一枚簪子就可以落入我手上。这样一想,我对姓甘的反感,减去了许多。
可是,十几个时辰的战斗,历历在目,迷吾庐帐的撤去只为了在谷地里埋伏。但我们涌进三兜谷时,突然高处掉下许多石头,前面的黄土呼啦啦地掀起,下面大变活人似的冲来一伙拿着刀斧的羌人。我一看情形,暗叫糟糕,但事已至此,不得不持剑格杀,傅君甚至下马战斗……
凌乱中,我若隐若现看到对方军队后方站着一个酋长般的人,而他的身边,竟然是个毕恭毕敬的熟人——除了姓甘的还能有谁。呸!叛徒,之前我还以为身为汉儿的他,始终忠心朝廷,谁知,“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殷鉴不远啊,所以我现在敏感扑捉身体内部的细微变化。春仁也许自认为万无一失,她选择刺入的口子非常准确,刀尖所过处全是大动脉,不枉我辛勤教导。可惜,她没有再补上几刀,区区一个伤口,阻止不了我快速愈合。等到痛疼完全停止下来时,短刀就整儿个弹出我的胸膛,为了迷惑春仁,我却依然用手持着短刃,装作受伤的姿态。可笑那春仁在翻包找寻绳索处理我的“尸首”。
好嘛,这是比“抢红包”手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当我悄悄接近春仁,手起刀落,以那柄还沾着我的血的短刀反捅入她的心脏,但不提防她指甲一个刮蹭,我的人皮面具,噗的一声,如同枯叶般落下。
“啊,你——”
春仁的眼珠子睁得可圆呢,似乎随时要跳出眼眶。她的嘴巴只看到黑漆漆的喉咙入口。而我忍不住摸着失去“保护衣”的尊容,从春仁的瞳孔里,我读懂了惊骇、厌恶,各种难以言喻的感受。这些体验,我也从前也有过,那时我拆开缠在头上布带后,特意上街逛逛的情形。每个经过我身边的人,但凡瞥见我的尊容,马上嘴角流露出鄙夷,甚至有孩子吓得大哭;正要掏钱给肉肆的屠夫,那厮从鼻底哼出一句,“你到别处乞讨吧”……
我感觉自己的青筋突突地冒出,太阳穴生生地扯痛,她绝对不能活着见明天的太阳!绝对不能!
我果断抽出腰间藏着的簪子,拔出怀里另外一特制小管的机关,滴了一点红色液体到簪子上。那红色的液体,毫无疑问,是戈兰的鲜血;簪子受了鲜血的催动,不自觉颤动起来,我口里念诵着咒语。簪子“嗤”的一声,悬空到春仁身体上方,从簪尾发放出绿色的光束,颜色越来越浓,打在春仁的口鼻部位,幻化成一方帕子。春仁起先小脚还蹬几下,慢慢地,手脚下垂,她咽气了!
之后,我轻车熟路打开车尾箱,那里备着络酸洗液,加上我从阿奴那学来的秘方倒下去,很快,地上看不到春仁了,只有几滩黑水,空气飘着奇怪的味道。我稍加收拾就施施然离开,天明后,这里所有一切依旧!
“一道急行冷锋正快速扫过本身北部地区,预计8小时内,气温下降,届时可能会下雪。请各位驾驶的朋友,小心路滑。”电台里的天气预报响起,我边开车边微微地笑了,池水明早又再次结满了冰……谁会注意那一滩黑乎乎的东西呢!我现在终于能腾出手,好好料理戈兰这小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