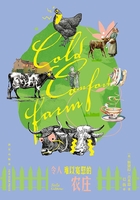对于女孩子的所作所为,江玉成觉得这不真实,他坐在她的床上时还在怀疑她的微笑、她的这种超常的行为。面对她那得体的话语、多情的诱导、激动的声音、任性的脾气、娇羞的暗示,他显得无情无绪,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她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呢?是刘元新的一个色情侦探吧?传说刘元新当年能够扳倒他的前任就是利用色相设了一个圈套,他才如鱼得水的。莫非她受刘元新之命,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困了你就睡。你怎么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放心,我不会谋害你。”曹玉芹不以为然地说。
“哦,我不困,你在哪儿睡?”江玉成问她。
“一张床睡不下我们俩?你休息,我去洗个澡。”
江玉成觉得她就像一个很有经验的成熟女人一样自然、大方。她还是一个未婚的女子呀,就如此放荡。虽然江玉成一度幻想与期待过,但是,当她勇敢地出现,他又因心里的担心而畏缩了。色是杀人的钢刀,杀人不流血的魔棒。
江玉成无言以对,去了一趟洗手间,等他回来后,发现曹玉芹已经脱得只剩三点式。她见他走近了她,立马弹起来,江玉成无情绪地抱住她,她就像一块雪白的冻肉挂在了他的胸前。吻了一会儿,曹玉芹推开江玉成。
江玉成躺在床上,困倦疲惫一扫而光,他不但没有累的感觉反而兴奋起来,浑身传导着一阵阵骚热,产生了强烈的情欲冲动。他扒光衣服悄悄地去冲凉。他发现淋浴下飘荡着薄薄一层水雾,曹玉芹朦朦胧胧挺神秘的 ,他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陷阱。
“想什么呢?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呀?”曹玉芹两眼放光地盯着他问道。
江玉成自言自语道:“多美的人儿呀,我一身如炭似的漆黑,不能玷污了她呀。她应该有个更风流更富有朝气的小伙子爱着,我不能毁了她,她就像一件珍贵的玉雕,洁白无瑕。她几乎和我女儿一样大,我太没有良知了吧。”江玉成出了一身汗,只听她喊他,他像贼一样逃走了。
曹玉芹披着浴巾走出来,发现江玉成穿好了衣服,惊讶地问:“怎么你想走?我哪儿做得不妥了?我让你不高兴了?你真的不想做了?”
“不是的。我做不到。求你饶了我吧。”江玉成几乎是乞求她了。
“说什么呀?你就在床上睡,我不会要求你,我知道你没情绪。你别把我跟刘行长联系起来想,我绝对不是他派来监视你的人。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时间会帮助你调整好心态。你并没有伤害我,我不怕任何人,你懂我的心思吗?”
“不,你是美丽的女孩子,就像一块宝玉,应该珍惜,供大家欣赏。”
“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大家都来珍惜那块宝玉,不去打碎她,不重新塑造她,那她还有什么价值?那么宝玉就不能再生,岂不是宝玉的悲哀?”
没想到曹玉芹竟然有一副伶牙俐齿,让他无话可说。他必须以一个男人的形象面对一个激情荡漾的青春少女。
夜怎么这么静啊。他们睡了一小觉,东方就蒙蒙亮了。城市的嘈杂声把他们从甜美的梦中惊醒了。
“刘元新对待你比我好吧?”
“什么意思?”她像蜂蜇了似地一跃而起,支着身子盯着他。
“我是说他一定也在倾心你的美貌,贪婪你的姿色,想尽千方百计占有你。”
“他像个真正的父亲,不瞒你说,我想跟他睡一个房间,他怎么也不肯。他说我是你的父亲,你不要这样做,我要求你守身如玉,将来嫁个好丈夫,好好过日子。不管我怎么求他,他就是不肯,我想……”
“你想怎么样?”江玉成问道。
“我想报答他的抚养之恩。那天我哭了,他一直陪着我,等天亮了我发现他坐在我的床前,一直慈祥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他抚摸着我的头发,默默地垂泪。嘴里还不断地呼唤着:‘你真是我的好女儿呀’。”
“他在折磨你,还是他真的是你父亲?”
“我感觉像,又不像。后来,我才知道,他真的是在保护我,他对我的爱就像一个名副其实的父亲。我对他既敬重又有点恐惧,生怕哪儿做错了让他伤心。他曾经跟我说过,‘孩子,你从小吃过很多苦,有了我这个父亲,我不会再让你吃任何一点儿苦了,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没错,他一定说的是真心话。”
“那么他?”
“做个检验啊。”
“你帮助我?”曹玉芹说。
“我会的。”说完,他就沉默了,然后他又在沉默中后悔了,“做个需要很多费用的吧?”
“想什么呢?”
“我这不是作孽吗?你这么年轻,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做了,我有罪呀!”
“不,我是心甘情愿的,我又没怪你。我早晚得嫁人,可我不想找一个同龄人,我觉得中年人更适合我。”
“没有别的?”
“没有。如果非要寻找理由,那就是我对你的报答。那时候你就看见了,我如果被那伙流氓糟蹋了,我的命运也就改变了,真不敢想象啊!真的感谢你,不管怎么样,你碰上了,说明我们有缘。”
“好了,别说了,我们从此两清了,你还是尽早嫁人吧,我对你是负不起责任的。一个黄晓依就够我受的了。”
“除了爱你,我并没有要求你做别的,我会一直这样默默走下去。家还是家,情人还是情人,我觉得这样最好,彼此没有什么拖累。你以为呢?”
“那样对你更残酷了。我不同意。”
“我知道你跟黄晓依不错,可是,她也有比你更好的朋友!”
“你说刘元新?你不要乱说。他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见得有血缘关系呀!她是个养女。她母亲生他们兄妹九人,她排行老八,最后一个才是男孩。因为刘元新的大哥无儿无女就抱养了她。后来刘元新的哥哥和嫂子病死了,刘元新继续抚养她,直到她结了婚,他们都没有分开过。为了掩人耳目才把她弄到了土城银行。她丈夫死了,孩子又残疾,她就不上班了。”
“原来是这样?”
“你们在一起她没说过吗?”
“没有?”
“你也打听她?”
“我怎么好意思打听?”
“你让我嫁人就能保证我寻找到真正的幸福吗?”
江玉成无话可说,只好沉默了。
太阳悄悄在空中灿烂起来,江玉成辞别了曹玉芹,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耳边一直回想着曹玉芹的话语。他要弄清楚,刘元新在别的女孩子面前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为什么他对待曹玉芹那么爱护,甚至可以用生命去保护她呢?那么,只有一个条件,他们是真正的父女。这一切曹玉芹并不知道吧,那么刘元新心里一定十分清楚。只有这个答案才能让他信服,不然,曹玉芹不会在这种肮脏的地方保持得那么纯洁吧。
江玉成计划破译这个谜团,也许破译成功就有了向刘元新进攻的资格,也是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不卑鄙吗?他这样问自己,又一次把自己推向了进退维谷的边缘。
爱与被爱
江玉成感到彻底失望了。快下班了,仍然没有黄晓依的消息,起初,他甚是气恼,后来就觉得痛心。她怎么不辞而别了呢?她非要这样逃避我吗?她毕竟不是青春少女了。我们彼此相爱,再说爱得又是那么艰难,干吗要逃跑呢?她是不是怪我了?他突然想起关于她发起的残疾人自救会需要他的帮助,他一直没有付出行动。于是他找来了李秘书,让她把10万元今天给黄晓依汇过去。
“老板,就用这个账户?”秘书惊奇地问。当知道是给黄晓依汇款时,她就不敢说什么了。
“别啰唆了,快去吧。”江玉成厉声说道。
江玉成把李秘书赶走了。他埋头工作,需要忘却一切,他想只能如此了。到中午江玉成的脾气开始暴躁起来,看哪个员工都不顺眼,他简直就像个魔鬼。可他自个儿心里清楚这是为什么。他甚至没有腾出时间去吃午饭。但这是无济于事的,痛苦依然不停地折磨他。江玉成再也无法忍受。她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其实,他与曹玉芹做爱时已经把她幻想成黄晓依了。他不说,曹玉芹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毕竟还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她的确是一个把自己保存得很完整的处女。
秘书回来了,她笑容可掬地说:“老板,按照你的吩咐我汇走了那笔款子。悠着点呀,小心上当受骗。”
“什么上当受骗,你笑什么?”江玉成抬起头望着她。
“没笑什么,笑笑也不行吗?这钱别打了水漂!”
“本来就是打水漂的。没笑什么你笑什么?”江玉成幽默地说。
“我怎么啦?这不是你平时吩咐的吗?要用自然的微笑面对所有的人,养成习惯,难道我按照公司的规定笑一笑你也反对吗?”李秘书侧着脸调皮地说。
“反对,你那是幸灾乐祸,期望我被人骗了。”
“干吗呀,江总?黄晓依暂时不来见你,你就见了谁拿谁出气呀?真没劲。”
“你说什么?”江玉成一阵惊愕。
“明知故问。”李秘书说完甩头走了。
江玉成把她叫住,并告诉她,不要让人来打扰他。是的,他心神游移,见不到黄晓依无法安抚他那颗骚动的心灵。李秘书点点头就退了出去,她发现他一脸的怒火,这情绪也传染了她。
这时,焦虑不安的江玉成打开一瓶水城大曲,倒了满满一杯。他每次遇到无法排解的痛苦时,就想喝点儿酒解救自己。几分钟后,江玉成感觉脑袋开始发涨,隐隐有点儿疼痛,只好作罢。
这时,江玉成的专用外线红色电话响了。他在电话面前坐了好一会儿,听着电话铃响,不想接电话。桂玉是唯一用这个号码同他通话的人。此时此刻他无法同她说什么,但是电话响个不停。江玉成最终还是站起身,拿起了话筒。
“是江玉成吗?”原来是黄晓依。
“是你?”当江玉成听出那声音时,兴奋得不知所措了,“你在哪儿?”江玉成吼道。
“我叔叔家。”她说。
“是吗?”江玉成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他还以为她想从他身边逃走呢。但是听她说在刘元新那儿,他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是这样。我在帮你!”她回答得很干脆。
“哦,”江玉成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太阳穴的疼痛犹如一把钳子紧紧地夹着他的脑袋。“你为什么呀?”他焦急地问她,本想责备她,可是一旦对上话,他什么勇气也没有了。
“你并非属于我,江玉成。现在我意识到了,特别是昨晚跟你分手以后。”黄晓依的声音轻得让江玉成几乎听不见。
“我父亲就是那样,这你不了解他,你听我说。”江玉成急忙解释着。
“我太了解了,你听我说呀,我真希望自己没那么做。我真不知道我怎么鬼使神差地同你交往起来,而且越陷越深,我太轻率了。”
“黄晓依。”江玉成只感到全身像针扎一般疼痛。
“也许,因为我感到孤独,或许因为我很长时间没跟男人一起过性生活了,我太思念我的男人了。”她这样说道。
“这不是真的,黄晓依,你也明白这一点,我需要你。捐款,我已经给你汇过去了。”江玉成乞求地说。
“谢谢,我代表所有残疾人家属向你致敬。”
“跟我这么客气,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江玉成有点迫不及待了。
黄晓依的声音听起来很疲乏:“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这也无所谓。我只知道你并非属于我。现在我们最好及早分开,免得到时陷入难以自拔的地步,你说呢?你我都应该更理智些。”
“可我爱你,黄晓依,我非常爱你。我觉得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有点儿神不守舍的感觉。昨天晚上我没能在宾馆里找到你,我已经完全失望了。对我来说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你更重要。”江玉成嚷嚷着。他恨不能立刻把她抓在手里。
“没有用的,江玉成,我们不可能天长地久。我们没能力与世俗抗争。”
“黄晓依,你不能离开我!”江玉成的话震得电话机都在颤抖。
“我不离开你,可以后就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一样。我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交往。你明白吗?”
江玉成内心顿时生出一股难言的苦涩,吼道:“也许你可以,但我不行。我或许可以假装自己从来就没有爱过你,可是我能做到吗?我不能,相信你也不能。我们谁也不肯离开谁,对不对?”
黄晓依的声音表面上听起来显得格外平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玉成,看来也就这么回事儿,你并不优秀。真的,你只是一个有点自负的建筑工人而已。你有一股子粗野的蛮横劲儿,别的你还拥有什么?”
江玉成没有做声,他也无从回答。不管怎么说,她的话犹如一把利刃直刺他的心脏。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打击,一个风流寡妇对他的轻视。明明她和他在一起,她怎么瞪着两眼说谎呢!
“如果刘元新能挤出时间的话,他可能会去你的办公室找你。再说你有些办法,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去面对他呢?我觉得你呀,哦,算了,再见江玉成。”
电话挂断了,只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江玉成无可奈何地放下话筒,一下子瘫进沙发里,两眼盯着办公室的墙壁发呆。他的心凉透了,不再有梦,不再有狂喜,一切都结束了。良久,他捶了一下沙发,伸手拿过酒瓶子,举起来就汹涌地往嘴里倒。
另一部白色电话响了。江玉成拿着酒瓶,随手抄起电话:“江总,刘行长想见你。”秘书说。
江玉成放下酒瓶,并没有丝毫醉意。这酒像是兑了水一样寡淡无味儿。他木然地坐着。“我不能接待他,你带他去见高良吧!”江玉成恨恨地说。
“可是江总?”她的声音似乎很惊讶。
“别废话,请你带他去见高良,我已经说过了。”江玉成大声吼叫着,然后把电话一下子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