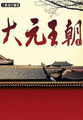四月的风已经很暖和了,轻轻拂过脸庞,应该是热的,可是拂过南慕白的脸庞时,却比刀子割还难受。如果吹来的是冬天凛冽的风,南慕白就会向人说,他脸上的泪水是因为眼睛受不了寒风的捶打才流下来的。其实他又会真的向谁说呢,这个村子里,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真正坐下来听他说呢?
妻子已经走了,带着满心的遗愿走了。在那一个世界,她会瞑目吗?她还会一个多月说不了几句话一个人默默承受一切吗?不会的,不会的,如果在另一个世界还会活的那么痛苦,她干嘛急着要走,急着要离开这个有她的丈夫,有她的儿女的世界?那一定是一个快乐的世界,至少要比这个世界快乐。是的,一定是个快乐的世界,是的,一定是!南慕白一遍遍地在自己的心里说着,他抹着一把又一把的眼泪,望着远处的山,那儿披挂着层层的绿衣。
南慕白已经用这种自言自语在妻子的坟头徘徊了一年,只是,到现在他还没有说服自己,那个世界真的会比这个世界美好。活着的人怎么能知道死了的人的世界呢?
妻子的两年祭日过后,打发走了四个孩子,南慕白才一个人拖着沉重的身子,迈着疲惫的步子再次来到妻子的坟头。南慕白需要单独和妻子呆一会儿,就这样一个人静静的,没有纸火,没有香蜡,只有他们两个人,多好啊!捧着一杯清茶,南慕白喝一口,往坟头倒一口,这样的生活才像夫妻的生活嘛。每当南慕白孤单了,他就到坟头和妻子喝一杯淡淡的清茶。妻子前几年还不喝茶,只有这几年来才开始喝上了,现在却永远喝不上了,所以南慕白隔三差五就到坟头走一趟。南慕白想,妻子也老了,也和自己一样怕孤单。农村的妇女四十多岁,就已经被岁月的风霜摧残的很老很老了……
这会儿,南慕白正坐在坟头,高高的山梁上晚风习习,对面山头一片残红,红的天空,红的云,红的山,红的草,红的庄稼,红的树,夕阳西下是一种多么自然的现象,它的沉落代表着次日的重新升起,可是,妻子的中年早逝,只能是永远的沉落,再也不复归来。他改变不了这一切,他默默看着夕阳下的这片血红,看着看着,这血红竟然就像妻子出事故那天倒下去的血泊一样,深深刺伤了南慕白的心。南慕白闭上了眼睛,滴滴眼泪就从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流了下来。他赶紧一把擦去了那些湿湿的液体,不自觉地向四周张望了一眼,粗造的一双大手竟然也变得湿漉漉的了。
南慕白想着要给妻子说点什么,其实平时他已经向妻子叨叨太多了,但此时此刻,他就是想和妻子说点什么,或许是新鲜的事儿,也可能还是平时的那些絮絮叨叨。本来应该在妻子祭日的那天说的,那天是哪天?那天不就是昨天吗?南慕白无奈地摇摇头,自己的记性是一天不比一天了,尤其是妻子去世后,他的记忆力明显下降很多,这样下去,南慕白真害怕有一天他连妻子的祭日都会忘记。南慕白总觉得祭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就像出生日一样,生死之际,展现的都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样子。南慕白喝了一口茶,给妻子又倒上一口,他放佛看到了妻子最后闭上眼的一刹,望向自己的深情的目光,那目光里面,包含了他们二十多年夫妻生活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那种不舍和无能为力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那种眼神,南慕白知道这一辈子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南慕白已经和妻子喝光了他带来的一杯茶水了,可他还是没想好该对妻子说点什么。他觉得,祭日应该说点特别的,看,我们的南慕白一眨眼功夫,又把今天错当成了妻子的祭日,罢了罢了,去年的今天,他不也是一个人端着杯茶水和妻子喝来着,一直喝到月上高头,繁星满天。南慕白皱着眉头努力回想着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好给妻子絮叨絮叨,那严谨的态度就好像他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稍有不慎,就会亵渎了自己的信仰。看到了这儿,谁还会再去责怪一个老人,就因为他早早地记错了妻子的祭日。老人?他不是刚过五十吗?可是你看他两鬓花白,佝偻着脊背,两颊凹陷,满脸皱纹,分明就是一个老人嘛!
西边山头的残红只剩一丝一丝的了,四月的晚风也悄悄地变凉了,它本不想去打扰这位可怜的老人,可南慕白还是不自觉地颤了一下,单薄的外衣还是保护不了他那瘦弱的身躯,南慕白叹了一口气,两眼久久地望着那个小小的坟冢,动了动嘴,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来,他实在是想不起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想着要不说点窝心话吧,可他转眼一想,有些话太窝心了,说出来了,就会将他的心也扯出来。他捧着一个空杯子,伸出手抓了一把黄土,往妻子的坟头慢慢撒去,然后拍了拍坟头,那样子,仿佛他是拍了拍妻子的肩旁。然后,站起身,拍拍屁股上面的土,依依不舍地准备离去。
蹒跚着脚步,南慕白慢慢朝路口走出,没走多远,他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折返了回来。“芬芳啊,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南慕白抬头瞅着西边的残阳,大声咳嗽了一声,“我本来寻思着,就不给你说了,可想着你们从小一起长大,觉着还是应该告诉你一声。芬芳啊,听了你也别伤心,就是你那个堂哥田文学,听说他进监狱里去了。唉,这人的命啊,真不好说!上回你住院的时候,他隔三差五地跑来看你,给你又是塞钱又是拿东西的,我这心里还记挂着人家的好呢。可谁知遭了这变故,哎,世事难料啊!那时候的田文学是风风光光的,记得当时你还央求着人家,以后要照顾着咱们的娃。可是,谁会想到,你这才离开几年,他田文学就锒铛入狱了呢?”南慕白掏出一个烟盒,抽出张纸,卷了根烟卷,划了根火柴,点燃了,他一口一口抽着烟卷,眯缝着眼睛,唉,你说这人啊,就连田文学那样的人,都吃上了官司,入了班房,他可是你们老田家的骄傲,也是咱们县里数一数二的名人哪!唉,你们老田家的风光这回也到头了喽!”南慕白又点了一根旱烟卷,吧嗒吧嗒地抽起来,“芬芳啊,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大半辈子想着让咱们的娃上大学,你活着的时候,动不动就拿你的堂哥田文学教育咱们的娃,现在你走了,我给你说这个事儿,你在下面听见了,可千万别难过啊!其实,我想这样也好,倒也断了咱想给娃娃们找条后门的念想了。娃们都还没有成人,以后他们自己的路就由他们自己去走好了。芬芳啊,你就在下面好好睡着,咱们的娃有我看着呢,你活着的时候,动不动就说,离了你,我连娃们都拉扯不大,现在离了你,只要娃们争气,我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会供他们上个大学的。芬芳啊,你活着的时候,心没有闲下来的一刻,现在你走了,你就在下面好好睡吧,娃们的心你再也不用操了。俗话说得好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何为着儿孙做马牛呢?”南慕白吸了一口烟,没有吸出味来,才发现烟卷上的火星子早就被风吹灭了。“芬芳啊,你堂哥的事,你就不要难过了啊,那都是命,俗话说得好,唉,他命里就该如此!芬芳啊,你就在下面好好地睡着吧,什么心也别操了,你都已经操了大半辈子的心了,终于到闲下来的时候了。芬芳啊,那我就先回去了,改天再来看你,再来陪你说说话。”天已经暗了下来,南慕白一步一步地从山梁上走下来,一步一回头。那片曾经充溢着张扬的绿色的洋芋地,曾经遭人妒忌的希望地,曾经默默地忍受着偷盗者践踏的土地,正在夜色中慢慢变得模糊不清,现在妻子田芬芳正安静地躺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守护着它不再被人踩踏……
南慕白回到家里时,天已经很黑了。猪娃子在圈里早已嗷嗷开叫了,只有那只上了年纪的老猪婆闷头闷脑地一动不动地呆在它的窝里,安安静静地等着它的主人来给它倒上那从来也不会变样的食物。然后,再朝主人哼哼唧唧几声,这一天最后一顿的吃食也就结束了。南慕白看着它吞吞咽咽吃食的样子,心里想着:它也老了,等下完这窝猪娃子,也该卖了它了。优胜劣汰,在南慕白家的猪的世界中从来都是如此。现在,南慕白来钱的地方就是靠着一只老母猪生猪崽子。他太需要钱了,没办法给它养老送终,它的使命完成了,就只能被淘汰。忙完猪圈里的事,南慕白又一头扎进了驴圈里,两只毛驴偎在他的身旁,推也推不开,又叫又挤的,南慕白只感觉脸上被它俩呼出的热气弄得痒痒的。南慕白伸出巴掌,“啪”的一声打在正在龇牙咧嘴的骟驴的身上,它不情愿地挪走了靠在他脸旁的头,撞到了他手中的背篓,里面的麦秆节子撒出来了一些,他弓下腰,一撮一撮地抓到了背篓里,又仔细地把混在麦秆节子里的杂物捡了出来,抬起胳膊,扔到了圈墙外,大声吆喝一声,两头毛驴乖乖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南慕白扬手就把驴草料倒在了槽里。传来一阵一阵“唰唰”拨动草料的声音,两只毛驴用力地咀嚼着,咀嚼得回味无穷。南慕白一手操起钝钝的旧铁锨,一手拎着小巧的扫帚,开始了驴圈大扫除。顷刻间,两只毛驴瘦骨嶙峋的影子就映在了光滑干净的圈地上,弧度好像天上若隐若现的上弦月。是啊!驴子真瘦,就像南慕白一样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南慕白拎着一桶水,挨个让毛驴喝了,然后拍了它们一巴掌,关上了门,南慕白想着,过几天要给驴子加点豌豆料补补了。南慕白是个勤快的人,他家的猪圈、驴圈、院子、大门口总是保持着绝对的整洁和干净。路过的人对此总是赞不绝口,说他真是一个会持家的好男人。没事要是在老南家的猪圈驴圈旁溜达一圈,你会惊叹原来牲畜住的地方也可以收拾得这般干净,看那叠得整整齐齐的防寒帐篷,看那堆得高高的新鲜的粪堆,应该很快就要被担到庄稼地里去了吧!看那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牲口棚,尿液很好的被引出了排水沟,牲口们有的懒洋洋地哼哼唧唧,有的晒着太阳悠闲地闭目养神,仿佛在告诉你做南慕白家的牲口是一件多么幸福而又荣耀的事情。是的,别人家的牲口们绝对享受不到南慕白家的这种五星级的待遇。
关上驴圈的门,南慕白拖拉着步子回了屋,屋子里一片漆黑,如果不是一直围在脚下活蹦乱跳“喵喵”叫唤的毛蛋(南慕白前几年收养的一只猫的名字)提醒他该开灯了,他就打算这样黑灯瞎火地呆着。以前一个人的时候,老是不开灯是害怕费电,是省钱,现在南慕白一个人不想开灯,是因为他害怕看到灯光下自己孤单的影子,长长的,歪歪扭扭的,映满整个屋子,心里怪难受的。他摸索着找到了灯绳,开了灯,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孤单的影子,触目惊心,是的,以后他真的是永远的孤单了。毛蛋抬起小脑袋,两只圆圆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瞅着那只二十五瓦的灯泡,它可能怎么也理解不了,就那个比自己脑袋小不了多少的东西怎么会突然发出光这种东西,其实什么是光它也理解不了,它只看到了南慕白,看到了南慕白那双无数次对自己笑的眼睛像两只黑洞,一动也不动,幽深得什么也看不见。“喵喵,喵喵……”它抓着南慕白的裤腿,发出被冷落了的叫声。南慕白低下了头,它也饿了吧!碟子里的花卷被撕下了一圈丢在了饭桌上,南慕白放到嘴里嚼了嚼,喂给了它,再给它的碗里倒了点水。“毛蛋啊,你慢慢喝吧,我先睡了啊!”现在家里所有有生命的动物们,都得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只剩南慕白了。但是南慕白拉开被子,一头钻了进去,灯灭了。平日里的晚上,南慕白喂完所有的牲口,忙完所有的家务,才开始给自己弄吃的,和小瘦猫毛蛋一起相互做伴,只是今晚他困了,再一次从妻子的坟头回来以后,南慕白又想起了妻子离世的那个痛苦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