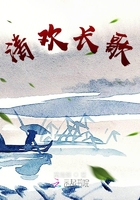槊和枪,本都是马上厮杀便当之器,在这武斗台上周旋起来,枪花槊影占得满满当当。
槊很像枪,它的头部介于枪和矛之间,却又多了一截带棱刺的部分。为了便于步兵作战,槊从马槊衍化出了步槊,槊杆从一丈八尺长缩短为一臂,一根衍化为两只,9公斤左右的重量也平分在两只上面。所以能使得起槊的人一定是力大无穷。
枪是四大名器之首,百兵之王,讲求轻快灵动,枪重一般只有1公斤左右,便于扎、搕、挑、崩、滚、砸、抖、缠、架、挫、挡。枪虽流传古远,使得好的却寥寥,花枪也只公孙一家,所以乐闲能够猜到。
一长一短、一轻一重、一单一双,两件兵器各有所长,而胜负却并不在两件兵器上面,而在两个使器的人。
悟性高超的人,能够在各种条件下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知道怎么扬长避短。敏锐的观察力,精准的判断力,随机应变和处变不惊,以及关键时刻的决断,这些能力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在将门世家中也并不多见。
所有左右战局的成败都源于那关键的一刹那,而那一刹那的决断,并不只是那一时做下,而是过往功课的考验。
一枪见红,那枪尖戳在了乐闲的大腿上。
不论将领兵士,为行动方便铠甲只穿上半身,小腿绑有护腿,跨部会有一圈如裙摆的围甲。燕国地处东北,生猛野兽很多,冶炼技术却不如中原发达,他们的铠甲并非金属制成,而是皮甲。一块块皮切割成小长方形编串起来,能抵御箭矢且穿着轻便耐用,后来碾压六国的秦军所穿皮甲还是跟他们学的。
枪尖难以刺破皮甲,若被卡住反而有枪被步槊砸断之险,所以他引着乐闲步槊护面,冷不防找到机会,一枪避过围甲的缝隙,戳中了乐闲的大腿。
乐闲大腿吃疼后退一步,眉头也没皱一下,反而大笑:“好!再来!”
说着双槊脱手,向安儒飞去。
原来乐闲的槊与手臂间有铁链相连,槊竟多了流星锤的功能。
本来步槊短对长枪长的短处因这飞矢流星而消失,局势便又有了变化,安儒被逼的步步后退,完全被乐闲压制了下来。
一槊险些将安儒的枪尖砸断,那槊与枪缠绕之际,另一槊已砸到了他的头顶。
安儒一把,抓住了乐闲的槊头。
槊头的尖刺早已扎进了安儒手心。
安儒的血顺着槊尖缓缓流下,滴在平台靛蓝的石板地上。
在乐闲杀气腾腾的气势之下,安儒也是一个眉头都没皱,一张儒雅风俊的脸上竟是视死如归的凛然。
两人僵持了三息,周遭忽然有了风声,将血滴石板的声音掩了过去。他们盯视对方,手上还在暗暗运力,像两头远古异兽,头角架在一起,却仍在用鼻息比拼气势。
天地之间,风起云涌般的只这两个生灵,在为两个族群而战。
此时,乐闲的眼底有了一丝触动,随着他眼光中攻势的松动,他的脚下也向后退了一步。几乎同时,安儒放下了乐闲的槊头。
乐闲上下看一眼安儒,嘴角微微上扬,屏住的呼吸回复了往常的频率。
他自顾自转身走到一边,拿起了酒葫芦,喝了一口,然后将它扔给安儒。
乐闲本就无意于这个赌局,他只是想看看他的身手,和他比试比试。
这个决定,还是从看到那个枪花后才做的。
乐氏在燕国是大将之家,父亲善于兵法,他也是自小习武,论体格论技术,燕国从来没人和他打过平手,更别说赢过他。
所以他有很久没有,或者说从来没有和谁厮杀得这样痛快,他满心喜欢,这面前的楚国校尉,这个同龄人。甚至还能刺中他一抢。
安儒接过酒葫芦,喝一大口,咳了两声:
“我不好酒,也不嗜杀。却不想在此时此地,做了平生最不喜的两件事。”
乐闲走到他身边坐下,拿过酒葫芦咕咚咚灌下数口,不再递给他:
“不好酒便不喝,不嗜杀便不杀。大丈夫顶天立地,总要做自己愿意之事,何必为难自己!”话说得轻巧,安儒却无法苟同:
“你说的何尝不是,只我祖上为将,便注定世代为将。将在军中,又如何由己。”
乐闲大笑三声。
“好个祖上为将,世代为将。将在军中,如何由己!”乐闲笑得豪迈,似有同感。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我自以为守着道家的清静无为,便能找到万事万物本来的归宿,各得其所。没想这一世却辗转漂泊,终是个为君王开疆辟土,私怨公仇,累得百姓妻离子散,马革裹尸的大逆不道之人。”安儒也没想到,自己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好个私怨公仇,马革裹尸!好个大逆不道,响屁不臭!哈哈哈哈!”乐闲从哪里顺来了一句缀在后面,听上去非常之讽刺。
如今国与国间交战是常态,没有借口也要寻个借口,燕相弑杀燕惠王自然是送给别国再好不过的一个理由。
说起这件事,其内情乐闲心里非常清楚,却也无可奈何。
武成王不是燕惠王的儿子,最多算是王室里一个旁系的公子。公孙操与圉人串通弑君杀世子,将那旁系公子顶替世子立为新君,他也便可一手遮天,再无人可与之匹敌。
话说回来,燕国内部祸起萧墙,就算公孙操一人身兼将相,但乐家还是掌握着实质上的兵权,若是起来主持公义,将公孙操掀翻不是不可能。
乐闲就有过这样的想法。
可是乐毅执意不肯。
燕惠王与乐家有怨有恩,乐毅曾被燕惠王逼走投赵,还写下了被后世称颂的《报燕惠王书》,按说他更有推翻燕惠王的理由。
所以乐闲一直以为乐毅的听之任之是对公孙操弑君的一种默许,这个想法让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接受。
君毕竟是君。更何况他只是被齐国的计谋蒙蔽逼走的父亲,乐毅在赵期间,燕惠王对他们乐家一直都恩遇有加,从未动过杀念。而后诚意请乐毅归国,提拔乐家后人。
就算没有这样的恩典,君也毕竟是君。
现在的燕国都不知道是谁的燕国了。
可是乐毅不睬。
他甚至还劝住了和燕昭王、燕惠王关系最铁的赵王放弃为之报仇,怪就怪在赵王非但不再提报仇之事,还将女儿嫁给武成王为后。
乐闲不懂乐毅对于燕国王室的绝望,比他要深得多。
国事就是国事,战争就是战争。每个人都是国君、国家的子民,都有为国而战的使命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