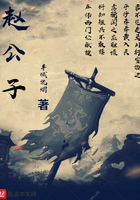梦深难觉止步缘无我迷津已渡拈花笑何为
余君惠这一夜,因藏着心事,翻来覆去的,何曾睡一个饱觉?次日到了学堂里头,对了教员室一面穿衣镜子一望,只见两只眼睛,竟是通红,身上一件浆洗得发了白的中山装,一列纽子,全系错了,领头这里兀自矮下去一截,底下又如生出一块赘疣似的,十分的滑稽。余君惠望了镜中的自己,全然不像个样子,不觉皱了眉头,向那身影叹了两回气,自言自语道,“这可不像话!不像话!”他说这话时,黄秋水恰由他身旁经过,对了他便是一个微笑。余君惠对于这个微笑,似有些心虚,脸上先就红了一片,忙掩了神色,对了镜子将仪容整理了一通,夹了讲义出门去了。偏生第一堂课便是那白玫英班上的,余君惠踏进课堂,便觉有些不自在,目光不知往何处安放,只得低了头,看讲义簿子。他向来是个洒脱之人,讲起课来,是谈笑自如,最能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谁知这一堂课,却拘谨得很,说话的声浪也十分的低沉,简直是对了书默念,十分的无趣。那些同学们见余先生忽然像变了个人似的,都不免交头接耳起来,白玫英最是个活泼的学生,这番议论,她自然也在其列,未免对他更添了几分注意。余君惠见了这样的目光,越发脸上发烫,站在讲台之上,竟如站在钉板上头似的,散课铃还不曾打,他便宣布下课,匆匆走了。
玫英见余君惠今日有些魂不守舍,便猜是自己那封情信,起了效用了,心里头一番高兴,自不用说。又想爱情这事,虽是十分的神秘,可到了这个时候,似乎应该打铁趁热,将他尽早俘虏了,自己才算安心。于是中午休息的时候,便想寻个由头,到教员室里去找那余君惠。不想才走到教员室门外,却由后头伸出一双手来,将她一拖。玫英回头一看,见是秋华,便向她笑道,“怎么?你也来找你那位黄先生么?我们果真是好朋友,想到一处去了。”秋华叹了一声道,“你今后不要说这样话,我同他,已宣告终结了。”玫英听了这话,倒有些吃惊,忙问道,“这是怎么说的?好好的,怎么变了卦了?可是他那头反悔了?”秋华将头摇了两摇道,“如今的情形,是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既是都不愿意,也就散了。”玫英向她脸上望了几望道,“你别同我打麻胡,是不是为了他旧家庭的事,你不乐意,他那头见你不乐意,只好罢了?要真是这样,我可要说你一句,你太没出息!”秋华道,“这怎好算没出息呢?我就不信,难道你看见余先生一家子和乐的样子,你心里不犯嘀咕么?”玫英道,“为什么要犯嘀咕?你要想着,你是救黄先生出苦海啦!旧家庭的枷锁,在他身上压了这些年,想来也够沉重的了,要是摆脱开去,前头就是光明。摆脱不了,他一辈子都要在炼狱之中煎熬,难道你也忍心么?”秋华皱了眉道,“这话似乎有些不对罢?”玫英道,“怎么不对?我心里便是这样想的。如今看起来,我们似乎是无理的那一边,拆散人家的家庭,是个破坏者。往后瞧,根本上他们的旧婚姻,就是一个错误,我们做的事,是叫那个错误终止,将他们引向正途,这也就算做了错事么?既不算错,你为什么犹犹豫豫的?依我看,你嘴里说着一个爱字,却不肯为爱人牺牲,这不是没出息,又是什么?”秋华听了这话,心里又是一动,静默了半晌才道,“你的理论,似乎有几分正确性,可我心里乱得很,再叫我思量思量罢!”玫英却拍了秋华的肩笑道,“还思量什么?你这头只管思量,那位黄先生的心可就要碎了,你想做一个负心人么?”秋华红了脸,将她一推道,“我瞧你今天,真有些兴奋呢!你又得着什么好消息了?”玫英也不急着答复她,只抿着嘴笑,停了一歇才道,“你没瞧他今天的样子,有些不寻常么?”秋华笑道,“八字还没写一撇呢,就他呀他的,你也不害臊!”说时,伸出手来,将食指在她脸上扒了两扒,又是摇头两摇头。玫英脸颊之上,立时便飞起两圈红晕来,却仍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握着秋华的手,摇撼了几下道,“秋华,我们是好朋友,有什么事我也不必瞒着你。今天,我是快活极了!我常和你说,他是爱我的,其实我心里,真有些打鼓呢!昨日我那一封信去了,只觉心里头七上八下。今天见了他,我先还不敢看他,可如今,我已经领会了,他心里,也的确爱我。我这一程子的心结,算是完全解开了,你说我能不快活么?”秋华笑道,“你不用说,光是瞧,我就知道,你是真快活了。你瞧这张脸上,用眉飞色舞四个字来形容,真也就不为过。”玫英经她一说破,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将头侧了,在秋华肩上抵着,两边的短头发,纷纷披向脸上,将半张脸遮了,不让她瞧。秋华摸了她的脸笑道,“怎么?我说了这话,让你不好意思了么?为什么躲着不让人瞧?”玫英笑道,“秋华,你不是好朋友,我有了这样的好成绩,你不替我高兴,还说风凉话呢!”秋华笑道,“好罢,不说笑话了。你在高兴头上,我送你两句吉利话罢,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你那一头的情形,原要比我难上十倍,不想却有了这样的好成绩,我真该佩服你才是。”说这话时,又有些怅怅的,脸上的笑容,便有些挂不住了。玫英知道她又在心里犯难,忙拉了她的手道,“你既说佩服我,我说一句话。什么事,都是开头难,你这时候,可不能打退堂鼓!”秋华听了这话,却是叹了一口气,正有一句话要说,忽见教员室里头,出来两个人,忙将话头止住。
那出来的两个人,正是余君惠和那黄秋水,见玫英与秋华两个在那边站着,不约而同,都是一愣。黄秋水与秋华两个,为了昨日的约定,此时都正了颜色,余君惠是十分之尴尬,也将脸孔板着,偏是玫英一个人,见了余君惠,她是万分的欢喜,望了她那位意中人,便是一笑。玫英这一个笑容,虽扮作洒脱,却带了三分娇羞,正是十分富有青春美,任谁看见了,也要动心,余君惠此时见了,难免又有些发愣,正在迷惘之际,忽想起昨日妻子那一句醍醐灌顶的佛音来,不觉在心里叫了一声“不好”,忙正了神色,同黄秋水匆匆走了。玫英一直目送他的身影出了学堂,才握了秋华的手笑道,“如何?你瞧他的神色,是不是有些为我颠倒?”秋华道,“我瞧不出来,我看余先生,倒有几分尴尬。”玫英道,“所以我说你是个呆子,上海人说话,要叫你阿木林!他越是尴尬,越发说明他心里头动摇,他若是对我没意思,早就恼了。”秋华又有一句话要说,转念一想,她是个直爽的性子,此时又是一团高兴,旁人劝什么,她也未必肯听。且那位余先生,绝不是个胡来的人,我又何必过分地担忧,扫了她的兴致。于是只向她笑道,“兴许你说得对罢,你算是得了个成功的开头了,接下来预备如何呢?”玫英笑道,“不是你的话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预备乘胜追击呢!秋华,你就等我的好消息罢!”说罢这话,向秋华挥一挥手,满面春风地走了。
她这一腔子高兴,哪里还有心思念书?这日下半天的课,人虽在课堂之上,神思却飘到那余君惠身旁去了,好容易下了课,坐了汽车回家,本想径直回屋去,写她的第二封情信,忽又一想,阿姐今天早上说身上不适宜,连学也不曾上,我倒该瞧瞧她才是。何况明日是礼拜,学堂不上学,我纵是将这信赶着写了,也不好交给他,我又何必心急得这个样子!于是转了步伐,去看望她姐姐。才走到瑞芝门口,便听见里头有男子的声音,细听之下,便知是她们那位魏表哥来了。玫英对于这位表哥,是不大喜欢的,于是在门外先就叫道,“真是稀客,今天是什么风,吹动了魏表哥的大驾?”一面说,一面踏进屋子里,只见瑞芝穿了一身睡袍,在临窗一个西式的古董沙发上坐着,魏润良坐在床沿边上,正满面堆笑地,同她谈话。此时见玫英进来了,便向她笑道,“我正和瑞芝说呢,这样大喇喇的话,不是别人,一定是玫英表妹。表妹,你这性子,该收一收才是,要不然,将来哪个少爷,敢把你这样一位女将军似的人物娶进门?”玫英闷哼了一声道,“我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本来嘛,你就是稀客,阿姐打电话,三催四请的,也见不到你人,这句话,我说错了么?你说我大喇喇,可表哥自己,一来便往人家床上坐,似乎也有些不客气罢?”
魏润良听了,转头便向瑞芝笑道,“你瞧,我一不小心,倒叫她捉着错处了。仔细一考量,我确实有些喧宾夺主。不过,我们两个的关系,到底比别人密切一些,不必在这些繁文缛节上头计较罢?”瑞芝笑道,“我们之间显着亲密么?怕是不能够罢?玫英的话,很有几分道理,表哥这一程子,常是躲个不见面,也就同我们生疏得很了。”魏润良道,“这是没有的话,好比说今日,我一听说你病了,放下电话,我就跑了来,这就算够交情了罢?”瑞芝向他睨了一眼道,“你真当我是小孩子,拿这样话来哄我。我知道,是姑母强押了你来探我的病,要不然,你这样一个盲人,哪里有工夫到我这里来呢?”魏润良笑道,“你说这话,是骂我了,我是回来度假的人,最是闲不过,算什么忙人呢?”瑞芝道,“又是那句话了,你既不忙,为什么总不见你的人影?”魏润良道,“我是难得回来一趟,自然有许多朋友要会,只好算是无事忙罢!”瑞芝点了一点头,又是闷哼一声,才道,“是了,我猜也是会朋友的缘故,只是这朋友,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呢?”魏润良听了这话,不免将眉头一皱,正有一句话要说,回思一番,还是忍住了,因向瑞芝望了一眼,笑道,“朋友就是朋友,为什么还要分男女?瑞芝,你这样追根究底,是对我不肯信任了。”瑞芝将头摇了一摇,笑道,“我哪里敢追根究底?根本上,我就不敢管表哥的事,我没有那个资格呀!”说罢这话,望了魏润良,只是微笑。
魏润良见她今天的态度,与往常全然不同,说起话来,常是话中有话,未免也有些疑心。转念一想,我和春容的事,并不曾公开,我又收买了这里的下人,我同春容出去,常是避开瑞芝的行踪,故而一次也不曾叫她撞见过。要说有人向她告密,知道这事的人,除了春容那一个妹子,便是露露了。春容的妹子,是她一母同胞的姊妹,想来不会做这样的恶事,倒是露露,她恨我是恨到骨子里去的,怕是她泄露的消息,也未可知。我虽不喜欢瑞芝,可这一桩婚姻,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与她结婚得。往常她是肯为我倾倒的,我待她冷落一些,倒也无妨,如今她的态度,有些转变了,倒是不能不敷衍敷衍她。他心里虽是动了几个念头,脸上却是一丝不露,仍是带了笑容,向春容道,“瑞芝,你说这话,可有些冤枉我,我们是至亲,你来管我的事,也是天经地义呀!你对于我,似乎有些不满意,我这一程子确实疏远了你,你若是怪我,我向你认错。今后,我一定抽出些工夫,多陪一陪你,你就不要同我怄气了罢!”瑞芝听了这话,将眉毛一挑,抿了嘴便是一笑,向他道,“表哥这样子客气,我可真有些受宠若惊。既是这样说,明日金都看电影,表哥是一定肯赏脸的了?”魏润良忙道,“一定来,一定来。”瑞芝笑道,“那便好极了,我还邀了密斯孟姊妹两个,看完电影,还要扰表哥一顿饭呢!”魏润良听了「密斯孟」三个字,却是一皱眉,只装作不在意的样子,问道,“是哪个密斯孟姊妹呢?”瑞芝道,“自然是密斯孟春容和孟秋华呀,表哥同她们两个,也算会过几次面了,怎么倒不认得了?”魏润良只摇了手笑道,“我如今记心太差,叫表妹看笑话了。”瑞芝听了这话,又是一笑,向他望了一眼道,“不在女子一边留心,这是好事呀,证明表哥是个正人君子呢!”魏润良对于这一句话,却也有些不好答复,只笑了一声,并不回答。又坐了一会,便去了。
玫英在他二人谈话之际,本闪在一旁,对了书架子上一本小说书,在那里翻看。这时见魏润良走了,才走过来,在瑞芝身旁坐下,先向她脸上望了一望,才道,“阿姐的脸色不好,该躺着才是,为什么倒坐起来了?又陪他说了这许多话,依我看,明天看电影,还是不要去了罢?电影院里头,空气不好,反添了病了。”瑞芝此时将茶几上一套英国骨瓷茶杯碟,捧在手里头,慢慢呷着红茶,听了玫英这话,却是出了一会神,半晌才道,“我不过精神有些疲倦,不碍事的。明天这一场电影,怕是一出精彩好戏呢,错过了,倒是可惜,还是去罢!要是不上演,我再回来。”玫英听这话说得奇怪,便问道,“电影不过是放片子,又不要凑班子,怎么还有不上演的说法?”瑞芝笑道,“你不懂,我要演一出鸿门宴呢!只怕他们那两个角儿不肯来!”停了一歇,又冷笑一声道,“真正是那句话,男子都是贱骨头,你待他好,也是没用。你瞧不上他,他倒急了!走着瞧罢,我也要叫他吃一吃蛤头呢!”她说这话时,两颊之上,是一片潮红,眼睛里仿佛也冒着血丝。玫英只道她发着烧,在那里说胡话,忙扶了她上床歇息去了。
到了翌日,瑞芝的病并不见好,反添了几分热度,连中饭也不曾吃,只是沉沉地睡着。到了晚上吃夜饭的时候,玫英便嘱咐厨房做几个清淡的小菜,端到瑞芝房间里,陪她一处吃。瑞芝此时发了一天的汗,热度虽是退了,却是十分的虚弱,好容易爬起身来,叠了几个枕头,倚靠在床头,一个小丫头在床头跪着,伺候她喝绿豆百合汤,因见玫英来了,便叫小丫头下去了。玫英笑道,“你真是好福气,一点子病,闹得全家人不安宁,还要小丫头子跪着服侍你。”瑞芝笑道,“这是娘非逼着我喝的,说我是热出来的病,又发了一天的汗,该吃些清爽的东西。”玫英道,“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叫厨房给阿姐开了小灶呢!”正说着话,恰是下人端了菜来,瑞芝一瞧,见是一道西芹百合,一道清炒嫩藕,一道白玉冬瓜卷,一道苋菜炒豆腐,外加一罐子酸萝卜老鸭汤,一罐子香米粥,便向玫英笑道,“你这几样菜办得好,我一日没吃东西,正是饿了,闻见你这酸萝卜的味道,馋虫在里头叫呢!”玫英这时也向床上盘了腿坐着,听见瑞芝说饿,忙就盛了一碗汤,递到瑞芝手上,笑道,“亲妹子亲自伺候你,你说你是不是好福气?人家拜年说的吉利话,有一句叫万事如意,说得正是你这样好命的人,样样事情,都叫你顺心如意。”瑞芝正呷着汤,听了这句话,却将汤碗放下了,向玫英微笑道,“傻子,这世上哪有什么人,能事事顺心呢?各人有各人的烦恼罢了。”玫英道,“这话倒不错,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可我们总是亲姊妹,阿姐有什么烦心的事,为什么不肯说给我听呢?”瑞芝笑道,“我不过是一句譬方,我并没有什么不快活的事。”玫英道,“你还嘴硬呢!我瞧你这一场病,就是由心里这个病起的。人家说心病还须心药医,你不肯把心事叫人家知道,还怎么医病呢?”瑞芝不等她说完,伸了筷子,将一个白玉冬瓜卷,夹到玫英碗里,向她笑道,“你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想来是得着甜头了,对了我也高谈阔论起来!快吃罢,如今时候可不早了,吃完饭,就该走了。”玫英忙道,“怎么?病得这个样子,还要出去么?”瑞芝微笑道,“我心里头有个疑惑,不出去这一趟,料想也不能解决。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这场病,才可望好呢!”说罢,便催玫英吃饭,饭吃毕了,又忙忙地换衣服,玫英本想阻拦,却是不能够,只得陪她去了。
二人坐了家里的车子,一刻便到了金都门口,才下了车子,便看见秋华遥遥地走了过来,一面走,一面向四处张望,玫英招呼了她几声,她竟不曾看见,直至走得近了,她方才认出二人,忙停了脚步。玫英皱了眉道,“你真是个睁眼瞎,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站着,你会瞧不见!喊得我喉咙也破了。”秋华笑道,“我方才就看到这里站了两个人,只是密斯白向来爱穿洋装的,不想今天调花样,穿了旗袍了,我有些不敢认呢!”说这话时,向瑞芝身上望了几眼,只见她梳了一个牡丹头,身上一件粉红织锦缎的旗袍,肩膀垫得高高的,正是新近时装杂志上时兴的样式,左手上提着一只金丝手袋子,右手是一柄日本扇子,脚上踏了一双绊带的高跟鞋,也是水红的颜色,除此之外,又在脖子上挂上一串珍珠项链,那样子精心装饰,真有些艳压群芳的意思,便向她笑道,“密斯白倒是甚少穿这样艳丽的衣服,实在好看。”瑞芝笑道,“不瞒你说,我是存了心思,要同春容比一比美,也不知她今天肯不肯赏光。她这一程子,可真有些神秘,连学堂也不大去了。”秋华叹了一声道,“她如今的心思,哪里还肯放在念书上头?密斯白还不知道罢,她已和校长说,要办退学了。”瑞芝听了这话,脸色便是一变,虽仍望了秋华微笑,那笑容,可有些不大自然。玫英听说便道,“好好的,怎么学也不上了?可是好事近了?”秋华道,“兴许罢,她的事,我懒怠管。”玫英道,“要我说,她不该为了婚姻,放弃学业。女子嫁了人,便不能在社会上活动,这是旧思想,早有人倡议,应该摒弃。喊了十多年的口号,偏是没人实行,真也气煞人!白念了许多年的书,丢了人格,去给男子养在家里头当玩物。她们难道不知道,给人家当玩物,总有腻烦的时候,到了那一日,又该怎么办?”瑞芝听了这话,心里倒是一动,点头道,“你的这番议论,很有些道理。一个女子,一门心思为了一个男子,他只当你是粪土,将你踩在脚底下呢!这样的婚姻,也是无味得很。”玫英笑着将手在她脸上扒了两扒道,“当了外人的面,你就嘴硬,见了你那位魏表哥,你就不这样说了。”瑞芝听了这话,却只闷哼了一声,并不说话。玫英见她的神色,有些不同寻常,正有一句话要问,忽听见人潮之中,传来一个声音,叫着“检票”,接上又有几声摇铃铛的声音。随了这一声令下,那人浪便向戏院子里涌去。瑞芝听了这几记铃铛响,将头点了一点,向秋华、玫英两个道,“瞧这样子,他两个是不肯来了。我今天本有一件事,要当了你们这些好朋友的面宣布,既是他们那一头,不肯将这事宣布,我也不忍做这个恶人。好在如今,我对这一切已是看得极淡,任他们再玩什么花样经,也是白费工夫。此刻我身子倦得很,我先走一步了。”她说这话时,两颊之上,虽泛着病态的潮红,嘴角却带了一丝微笑,那神情,很是平和,当下坐了车子,便回去了。
秋华目送那车子走得远了,才问玫英道,“密斯白方才的脸色,真有些难看。”玫英道,“病了几天了,今天才好一些,便吵着要出来。出来一趟,电影不曾开场,又回去了。分明藏着心事,闹得病了一场,问了她,她仍是不肯对人说,我也没法子了。”秋华道,“密斯白这一场病,是为了这一桩心事的缘故么?”玫英道,“她身体向来很好,那天不是还在学堂里头,同人打网球么?回来接着一个电话,脸上有些不快活,问她什么,她也不说,晚上就发起烧来,你说,这不是蹊跷的很么?”秋华听了这话,因知必是春容与那魏润良的事,叫她知道了,这才生出这一场病。然而瞧她那样子,仿佛还不愿将这事同人说破,连家里人也蒙在鼓里头,却不知是什么道理。正在心里猜想,忽听见检票员在那里发表第二次的命令,又见门前拥着的人浪,已去了一大半,便同玫英去检票子。
走到检票口,却看见几个人围了检票员,只是七嘴八舌地嚷着,似乎有什么纷争。只见一个穿西服的男人,也不知受了热,又或是生气的缘故,满面涨得通红,挥着手里的电影票子,和一沓子法币道,“向来看电影,都肯进去再补票的,偏你不放人。我已有三张票了,不过再要补一张票子,并没有说要看蹭戏!你瞧我这样子,也不像看蹭戏的人呀!”那检票的人生了一张麻脸,仿佛天生就不具备发笑的能力似的,向人瞧时,扬着一张脸,竟是拿鼻孔对着人,态度是十分的傲慢。那穿西服的男人说了这一番话,他只当不曾听见,只将那「检票」两个字重复着。玫英见那人受窘,倒有些替他难过,便走过去道,“这位先生,可是买不到票子?我包了一个包厢,只两个人坐,既有两位女眷,就请坐到我们包厢里来罢!”那人忙道,“多谢小姐的好意,看不看这场电影,我全然是无所谓,我只恨他不讲理!他们戏院分明有规定,先进场再补票,也不是不可。他偏拦了人不让进去,我知道他的意思,是问我要「康密辛」呢!如今这世道,算是完了,一个检戏票的,不过手上有这小小的权力,就想着讹诈老百姓,要让他尝着了甜头,越发胆子大了,我绝不能纵容这样的恶行!”那检票的人听他这几句话,是十分不给面子,冷笑了几声道,“我是检戏票的,你又是什么大官?跑到这里充起天王老子来了!什么世道不世道?你肯出钱,就有门道,没钱,旁边蹲着去!再在这里捣乱,一会宪兵老爷来了,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那人听了这话,也是一声冷笑,向那检票的人瞪了一眼,点了几点头道,“我知道,你们金都,向来肯讨好宪兵的,好吃好喝,当佛菩萨一样供着。你们自以为有当兵的在后头撑腰,就无法无天了么?按照民国的法令,这是治安的事,理当警察管辖,他们凭什么干涉?你叫了他来,我倒要瞧瞧,他们敢动我不敢动我!”检票的冷笑道,“放你的狗臭屁!你是什么大人物,宪兵老爷也不敢管你?你有本事,叫了警察来,宪兵老爷一杆枪,照样打得你们满地狗爬!”一面说,一面两手按了那人的肩膀,便向外推。那人一个踉跄,险些要摔倒,幸而叫他几个朋友搀扶住了。只听他在那里连连叫着“岂有此理”,又跺了几跺脚,向那检票的人冷笑着点了几点头,转身便走。玫英见那检票的人,实在有几分不讲理,一句话正要冲口而出,秋华因恐惹出事端来,忙拖了她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