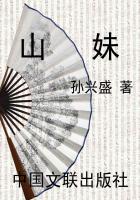看别人文章,会引起一些联想。荆歌《自己的头发自己剪》,让我有话要说。首先是这个“自己打理”,荆歌举例说到了江苏几位作家,说他们都是自己打理,譬如苏童,譬如毕飞宇,又譬如本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本人当仁不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给自己理发,要说省钱,已经省了许多。
苏童的头发绝不是自己打理,他有一位专门的师傅,所谓专门,也就是熟悉的店熟悉的人。仔细观察过苏童大脑袋的人一定知道,他脑门正中不时翘着的一小撮毛,这需要很卓绝的技巧,自己很难把握。毕飞宇的发型是最酷最炫的大光头,不过历史并不长久,是最近几年的事。我这人好较真,打电话过去求证,他太太接电话,说那大光脑袋有时候是自己打理,有时候还得太太帮忙。
江苏男作家中,荆歌的长发,毕飞宇的光头,最能凸现艺术家气质。玩艺术的张扬个性,折腾起头发来,也就这么简单两招。《孝经·开宗明义章》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大明朝亡了以后,很多男人寻死觅活,不是因为国家亡了,而是满人逼着剃头。满人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于是男人们一个个都成了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大伤脑筋。
时代在变,有一点没变,人们总是喜欢用头发做文章。满人让明遗民剃头,民国激进分子逮着了清朝遗老遗少,也要为他们剪掉猪尾巴。记得我读中学时,流里流气的男孩都留长发,父母常催孩子去剃头,赖着不肯去的,蛮横的爹妈便大打出手,像押贼一样硬把儿子领进了理发店。
现如今风气完全改变了,你怎么玩那头上的几根毛,都没人管。多年来我一直留着板寸头,母亲为此想不明白,老是问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跟囚犯似的。她不明白我是在享受自己剃头的乐趣,用一种傻瓜型电推子,定好了尺寸,很短时间里,就把自己的头发给收拾好了。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给自己理发,很多人看了觉得吃惊,光溜溜地走到了我身边,一边琢磨,一边感叹不已。
给自己理发有一种不求人的自豪感。反过来,替别人剃头,也未尝不是乐趣。还是在读中学时,学校里学雷锋,组织为人民服务小组,我有幸成了理发组的成员,成为一员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可以去买把理发的推子。记得当时是向祖父开口要,那年头,做好事很理直气壮,非常轻易地就能获得了一把推子。
用那把推子,只为一个人理过发,此人是理发小组的另一名成员。我把事情搞砸了,很快就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把哭丧着脸的同学哄到理发店,请老师傅重新